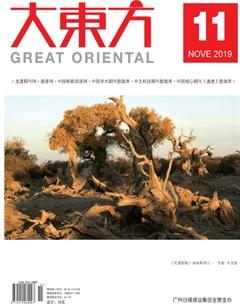比較詩學視野下關于李清照詞情心境研究的思考
摘 要:李清照是古代文學史上女性詞人中的典型代表,目前學術界對《漱玉詞》的研究多集中在前期的相思閑愁與后期的家國之愁,對于其人其作的深層次挖掘和探索并未有充分拓展,泊來的文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與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觀點一拍即合,為李清照詞情心境研究帶來新的思考。
關鍵詞:比較詩學闡發(fā)研究;知人論世;文化闡釋學;李清照
在浩如煙海的文學史長河中,李清照是一個富有代表性的女性詞人,她心思縝密,才思敏捷,有著常人無法比擬的文學抱負與詞話寄托。近年來,以王汝弼、陳祖美等人為代表的學者對李清照及其詞作的研究提出新的觀點,認為在其看似風平浪靜的創(chuàng)作氛圍背后,或許還藏著其他鮮為人知的內心秘事。他們的觀點大致分為以下兩點:一是不能小視宋代黨爭(新舊兩黨之爭、和戰(zhàn)之爭)對李清照創(chuàng)作的影響,二是李清照與趙明誠之間或存感情裂隙,因清照“無嗣”,趙明誠有“納妾”的可能,這也是影響詞人創(chuàng)作的因素之一。
以此為契機,對于李清照內心隱秘的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由于該研究方向更關注詞人的心境本身,使得原先較為粗略的研究方法在部分時候不能完全達到研究目標,對于其人其作的深層次挖掘和探索并未有充分拓展,而泊來的文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與中國傳統的“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觀點一拍即合,為李清照詞情心境研究帶來新的啟發(fā)。
比較詩學闡發(fā)研究指的是將不同民族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中的一些具有內在可比性的基本問題加以相互印證,相互發(fā)現,相互闡釋,并相互運用,以求把握文學的普遍規(guī)律。本文將試從該視角切入重新討論李清照詞情心境研究中的相關思路。
一、問題之源:前后分期造成李清照內心隱秘探究困境
對于李清照的研究,一般分為前期和后期兩部分,即“二期”說。陳祖美先生《李清照評傳》一書中對傳統的“二期說”提出質疑,認為這種大致以靖康之變和趙明誠過世為界石將李清照及其作品一分為二進行研究的方法過于粗略,不能適應更為細致的詞人思想感情與復雜心境的研究,為研究者們帶來了一些不便的困擾。例如:
1.時間線過寬致使中間年限創(chuàng)作的詩詞分期困難。“靖康之變”爆發(fā)于宋欽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冬季,而趙明誠病故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中間時間間隔接近三年,但這三年在李清照的生涯中卻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三年,三年中的經歷對詞人的影響和沖擊不亞于前十幾年,這樣大致的分期使得對具體作品的研讀難以深入,且更加不利于對創(chuàng)作年限存疑的詞作進行嚴格分期。
2.粗線條分期造成對部分詞作的內涵解讀模糊。“二期說”建立在對李清照人生軌跡的大致分界之上,認為詞人前期婚姻幸福,生活美滿,詞作中相應表達的也是相思夫君的閑愁嗔怪,而后期經歷南渡之變,家國之愁在此時上升為作品中的主要矛盾。但實際上,在“二期說”背景之下有一些作品并不能嚴格地劃入前期作品,例如《醉花陰》《鳳凰臺上憶吹簫》《臨江仙》《訴衷情》等,這些詞作中均或多或少的含有其他隱含愁緒,并非簡單的閑愁別緒。除去對部分作品的分期存疑以外,“二期說”還使得學者對一些詞作的內涵并不能正確解讀,也就使得研究者與李清照的詞情心境距離愈來愈遠,失去了進行該研究的意義。
3.“二期說”無形中淡化了對文本本身的探究。研究李清照,南渡成為了普遍認可的分界點。對于前后期的作品,研究者會自然而然地向所屬時期的作品特征靠近,從而忽視了對于作品本身內涵的解讀。由于詞人身份特殊,且詞量基數較少,又為女性,正史中的相關記載有限,所以更應該從《漱玉詞》中的意象表達中入手展開研究,才能更貼近詞人最真實的狀態(tài)和詞作原本的內涵。
從文本入手,是探索李清照詞情心境中的關鍵一環(huán),如何克服與化解當下研究中的這個困難點,拓寬更深層次的研究視野,正是本文論述問題的根源所在。
二、溯回之本:“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本土研究思路
“知人論世”出自《孟子·萬章章句下》,起初是孟子與人交談時隨口而抒的觀點。“孟子謂萬章曰:‘一鄉(xiāng)之善士,斯友一鄉(xiāng)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意為與古人交最主要的途徑是閱讀古人的作品,通過閱讀和理解古人留下的書卷和著作,來理解古人的思想境界,從前賢的身上獲取精神力量。同時,還要從古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出發(fā),以作品的內涵去理解古人背后的社會狀況。隨著時代的不斷發(fā)展,“知人論世”的觀點開始廣泛在文論中的應用起來,其與“以意逆志”一樣,都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方法。
回到李清照詞情心境的研究中,“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思想指導研究者從《漱玉詞》本身入手,透過文本理解詞人的心境,對詞作提出更貼近原意的解讀。在當下李清照的研究方法之中,“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并不是第一次提出,它是一個基本的研究手段,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和鑒賞易安詞的文本內涵。但由于“知人論世”是孟子與人交談時提出的觀點,因而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主觀性。郭英德《論“知人論世”古典范式的現代轉型》一文中講到:“孟子所說的‘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實際上是一種隨感式的評論,缺乏嚴密的內在邏輯性。”這使得讀者在閱讀和學習古人作品的過程,大多有以下兩種情況:一是起先并不了解“其人”、“其世”,在“頌其詩,讀其書”之后才“以意逆志”,逐漸清楚和明白了何為“其人”、“其世”。二是在“頌其詩,讀其書”之前,以對“其人”、“其世”有所了解,甚至比較熟悉,可以在誦讀研究文本的過程中將“人”與“世”的特征引用其中,從而幫助讀者深入理解文本內涵,目前對于李清照及其此詞作的研究大多屬于后者。
按照上文所述的“二期說”及李清照本人的性格特點來看,李清照的詞文創(chuàng)作大致分為前后兩期,前期作品除去少女時期思想單純的少量作品以外,其他均為對于閨中閑適生活的記述,抒發(fā)對丈夫趙明誠的相思之情,而南渡以后的后期作品則主要以顛沛流離的愁情寄托和家國離變后的復雜心緒。在李清照研究中,一般會根據詞作的創(chuàng)作年限,大致將其置于所處時期,并根據該時期作品一貫有之的特點進行賞析和評價。這樣的文學評論思路大致是合理的,但卻不置可否地受到了先入為主思想的影響,使得對《漱玉詞》中部分詞作的理解并不到位,僅從表面字詞和大致內涵進行了解讀,與探索內心隱秘和研究詞情心境的目標相去甚遠。例如,李清照《醉花陰》:
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jié)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
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此詞為李清照前期作品,其“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之句被歷代學者看做是抒發(fā)相思之愁的佳句。但對于詞作的具體分期學術界存有爭議,部分學者由其屬于前期作品而想當然地將該詞理解為夫妻分別后的純相思之作,認為《醉花陰》作于趙明誠起用為萊州知州,李清照閑居青州之時,表達對丈夫的相思之情。而結合“元祐黨爭”背景,再仔細研讀文本過后,我們發(fā)現致使“人比黃花瘦”的除了單純相思,或許別有寄托。以陳祖母、馬瑞芳為代表的研究者認可這個觀點,認為此詞應作于1103年朝廷下令禁止元祐黨子女住在帝京后,是李清照被迫回到祖籍居住后的愁悶宣泄,此時的清照與明誠被迫分開,對“明誠納妾”的擔憂或也在此時埋下伏筆。
我們不難發(fā)現,在李清照詞情心境的研究之中,“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它更適應細膩的貼近心理的研究需要,但在當下的研討側重點上有所偏移,仍舊停留在一個比較表層的程度,使得學者對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比較粗糙陳乏,難以推陳出新,拓寬思路。
三、西學之鑒:由文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觀點帶來的思考
西方結構主義文學認為“文學研究與具體作品的閱讀和討論不同,它應該致力于理解那些使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程式。”結構主義學家提出作家主體身份消失的觀點,他們不再關注作者在作品評論中的作用,更多聚焦于文本本身,探討文學范式,這提示我們在研究中不能過于先入為主地以“其人其世”論其作品,應該更多從文本本身出發(fā),探究其文學“程式”。
誕生于19世紀的西方文化闡釋學與接受美學從讀者的角度解釋了閱讀時“偏見”存在的合理性,這與中國傳統“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提倡重視對文本本身的研究與探討,并關注歷史和其他因素對作品內涵的影響。
闡釋學的代表人物伽達默爾提出“視域融合”的觀點,認為在重新喚起本文意義的過程中, 解釋者自己的思想總是已經參與了進去。理解者的視域與理解對象的視域互相融合, 理解者由于在理解對象時不可避免地具有前見因素,自身的前見會滲透到對理解對象的過程中, 導致對理解對象的忠實度降低, 同時解釋者的視域又是動態(tài)的, 可以在理解的過程中擴大到融入他者的視域, 形成一個比自身視域更大的視域。這與中國傳統“知人論世”的觀點不謀而合,但不同的是闡釋學的觀點更為客觀系統,是在理性分析基礎上進行地合理推斷。將文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的觀點融入對李清照詞情心境的研究中,可以更好地平衡“知人論世”中過于先入為主的情況,使對各方面因素的分析達到更為準確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作家作品的誕生都不可能離開所處的時代歷史背景,作家和讀者本就是歷史的組成部分。伽達默爾指出“歷史既不是的主觀創(chuàng)造,也不是對過去客觀事實的重新發(fā)現或復制。歷史既是理解的前提,又是理解的產物,它表現為理解的處境與界域之間相互作用的合力。”在李清照研究之中,不能忽視歷史大背景對詞人創(chuàng)作的影響因素。李清照長于鐘鳴鼎食之家,從小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是一個思想活躍,關切政治的女性。她的一生分別經歷了新舊黨爭與和戰(zhàn)之爭,其父李格非和公公趙挺之分屬新舊兩黨正營,她的生存處境可以想見,這樣的政治背景,不可能不對李清照的創(chuàng)作產生影響;除此,在中國古代傳統社會,丈夫通過納妾的方式來為家族開枝散葉的行為屢見不鮮,就連當時享譽全國的大文豪蘇軾在外做官之時,都有妾室在身邊照顧自己。且李清照又為正妻,更有為丈夫操持整個家眷的義務,如此看來,“明誠納妾”說或可成立。作者和讀者一樣,從來不是歷史的割裂部分,只有把握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才能得出更貼近事實的結論。
二十世紀后期接受美學理論從闡釋學中發(fā)展出來,代表人物姚斯借用闡釋學中“視野”的概念, 以“期待視野”為中介,以“視野融合”為途徑,將文學史轉化為一種閱讀者的積淀,在文學與社會、 美學與歷史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梁, 接通了文學與現實、過去與未來。“期待視野”是指解讀者面對本文時,調動自己的經驗并產生的思維定向及其他所希望的本文對他的滿足,“視野融合”則是指接受者的期待視野與本文或生活實踐視野的交融和相互影響。一個真正合格的研究者,應該先從作者所處的位置理解和體悟他(她),了解作者的生存背景,研讀其人的性格與精神世界,帶著一定的“期待視野”去走進他(她)的作品,而在與文章和生活實踐發(fā)生碰撞以后,應該及時調整和梳理觀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偏概全,要想真正走進作者和作品之中,則需保持一種多元的、直觀的、立體而飽滿的視野去分析文學作品。
反映在關于李清照詞情心境的研究中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單純地由“二期說”引導對詞作的研讀,而應該承認和關注面對文學作品時的“偏見”,以“期待視野”為媒,以“視野融合”為徑,實現詞人內心、作品內涵和讀者鑒賞三者之間的有機統一,這就是文化闡釋學與接受美學觀點帶給李清照研究中最直觀的思考。這樣,既平衡了“知人論世”中的隨感性與主觀性,更將《漱玉詞》研究提升至較為細膩的心理學高度。
四、創(chuàng)新之途:從比較詩學闡發(fā)研究的角度重新審度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分期
在中國早期的比較文學發(fā)展中,本土文學理論在很多時候不能完全適應研究的需要,受“西學東漸”思潮的影響,很多西方文藝理論開始傳入中國,并受到學術界的關注。面對一些需要立體剖析的文學作品,部分研究者直接將適宜的西方文學理論運用在研究之中,來對文本進行更深入的闡發(fā)與探索。這種“拿來主義”即為比較詩學中的闡發(fā)研究。王國維是比較文學中較早運用這種方法的學者,他的《人間詞話》是運用西方文藝理論和美學理論評論和賞析中國古代詞學的典范之作。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錢鐘書在《談藝錄》中運用了雙向、多項闡發(fā)法,出版于七十年代末的《管錐編》更是將其廣泛運用。
主流的李清照作品分期以靖康之變和趙明誠亡故為大致線索,將《漱玉詞》分為前后兩部分。但在易安詞隱秘心緒的探究之中,“二期說”對某些含有內心隱秘的詞作內涵分析帶來了些許困境,且并不能涵蓋詞人每首詞創(chuàng)作之時的心情狀態(tài)。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化闡釋學和接受美學中對于時間、歷史以及讀者原先存在的先見和視域融合等觀點則有力地補充了李清照研究中該方面的空白,不僅能夠更科學地進行研究探索,更使得對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分析評價更為準確全面,避免了人云亦云、模糊不清的問題。對于一些詞作的具體分析,也可以更加理性透徹,更貼近文本本身。由此,陳祖美先生對李清照研究提出了“三期說”的觀點,改前、后期為“前、中、后”三期:
前期:出生至屏居青州(1084-1107);中期:青、萊、淄、寧時期(1108-1129);后期:趙明誠去世至亡故(1130-1155)。
“二期說較適合粗線條的文藝批評的社會學方法,對于細膩的心理學等方法,它是相形見繼的。”“三期說”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二期說”存在的問題,更適用于細膩的李清照心曲研究,便于對易安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感情進行更透徹的分析。將中國傳統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研究方法和西方文藝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的觀點相結合,采用“二期說”和“三期說”補充對比的方法,更有利于對李清照詞情心境的深入探索。除此,“三期說”以趙明誠亡故為而不是靖康之變作為中期下線,這樣便于對詞作整體的把握和具體的分析與探究,在詞作賞析之外,也更適應對于李清照本人的研究。
在李清照的相關研究中,引入和運用國外的文藝理論,不僅可以與中國本土“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更有助于形成條理化、系統化的李清照審美評價體系,為今后的深入研究開拓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孟軻.孟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曹順慶.比較文學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3]郭英德.論“知人論世”古典范式的現代轉型[J].中國文化研究.1998;
[4]伽達默尓.真理與方法(上卷)[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5]周寧、金元浦.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6]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M].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陳祖美.李清照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8]伽達默爾與孟子的解釋學思想——“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與“‘偏見的合理性”之理論透析[J].饒筠筠.武漢: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1
作者信息:
藺墨逸(1997-),性別:女,籍貫:甘肅張掖,學位:本科在讀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