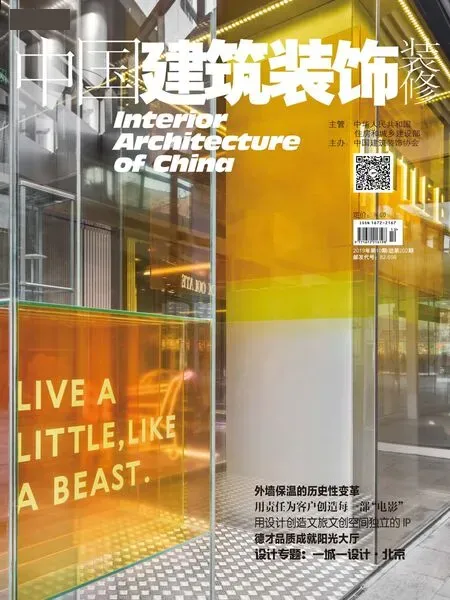舊世新題
——國子監胡同空間


大料建筑
2012 年秋,由劉陽和徐丹在北京成立。 最關心的是情感和記憶。希望用率性的方式做出“煽情”的設計。
理想中的建筑是:午后,大樹下,人們三三兩兩,聊天嬉笑,享受陽光和恬靜。 作品多次參加建筑及藝術展覽,并已獲得六項國際設計獎項。

劉陽
2006 畢業于北京建筑大學建筑系,2012 秋創立大料建筑,任主持建筑師。月亮舞臺獲得美國 Architizer A+ Awardz 文化類評委會大獎,一舍山居獲得美國 Architizer A+ Awardz 酒店類最受歡迎獎,三寶蓬藝術中心獲得美國 AAP 2017 年度最佳文化建筑獎。
地點:北京
時間:2016-2019
建筑面積:68 m2
設計團隊:大料建筑
設計人員:
建筑:劉陽、胡驀懷、劉思思、鮑蕙、楊妮、魚湉
結構:王春磊
暖通:鄭麗梅
電氣:侯延銘
攝影:孫海霆、翟博、張玉婷、劉陽
材料:磚、木、金屬

1 設計圖

2 外景
時間的累積,生活的變遷,可能性的多樣,這些東西都以直接而激烈的方式留在北京胡同的身上,似乎是歷史,在我來看,更是未來。
2019 年6 月1 日起,北京國子監街36 號,這個設計建造了2 年多的胡同小房子開始使用。一個小展覽,關于我們這幾年的設計實踐,與其說是展覽,其實更像是自己對過往的整理復習,希望能發現些好玩兒的新事情,就像再讀老書,總有新知。
而之后,這里會騰出部分空間作為我們的工作室,幸而大料小而精悍,地兒還夠。
而無論是展覽還是辦公,我們希望這里都像胡同里的空間一樣,開放而多變,不是廢舊立新,而是慢慢積累時間印記的同時,包容并融化新鮮事情,借用一句老話,“發展中調整,調整中發展”。
這房子也試著把時間上的記憶,經過重新組織后保留下來,并強烈的讓人們感知到。
我們保留了原建筑的房院關系和建筑尺度,甚至十幾年前的私搭亂建,因為那也是當時人們胡同生活狀態的縮影,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卻用下部混凝土框架和上部木框架的結構形式,調侃而夸張地表達了新老的嫁接。
還保留百年老宅拆出的青磚,十年私搭亂建拆出的紅磚,幾百年古樹留下的殘根,他們都還在原來的位置,留有原來的工藝和記憶。但建筑的構造做法卻完全不同,比如400 厚的夾壁墻體,除了保溫防潮構造外,空調新風給排水等設備也暗藏其中。

3 外景
胡同的歷史是延續的,時間是發展的,我們不希望他成為標本停留在某一刻,哪怕他足夠美好。我們覺得這個充滿符號隱喻等曖昧關系的房子,似乎更能體現目前胡同生活的狀態— —時間給這里留下的寧靜與張力。

1 設計過程
說了半天這會兒的事兒,其實原本這個設計并不是這樣的,所以我也想說說這里的過往和未來。
這就要從1988 年的冬天說起,那年我6 歲,一個出生并成長在北京胡同里的小屁孩兒。
30 年的時間,不斷苦苦求索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所居住的胡同的未來到底是什么呢?
而30 年前,我們的胡同是像圖里所看到的那樣,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大雜院的狀態。大家都在院子里邊自己蓋房子,蓋的越來越多,就把原來的院子就變成了窄道。
那時候我們幾乎每個房子里邊都放著床,住著人,我們沒有客廳了,沒有吃飯的地方了怎么辦?我們走出來,我們到胡同里邊,我們把胡同里邊當成我們的客廳,當成我們的家,然后就會出現這種老頭在胡同里下棋,小孩在胡同里玩的場景。甚至我們覺得這還不夠,我們希望我們把別人的家也變成自己的家。所以在胡同里邊,至少我小時候經常會到同學家去寫作業,或者到朋友家去吃飯,這種情況非常普遍。
這時候發現好像我們物理上的家雖然很小,但實際上我們自己覺得我們心里的家還是很大的。
設計圖的其中一張,是以前的一個公共的廁所的樣子。他跟現在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是每個蹲位之間是沒有隔板的,并且還都會離得比較近。而男女廁所之間這道墻的上方會有一個洞,這洞里邊放個燈泡,這是為了一個燈泡可以把兩個廁所都照亮。雖然這帶來的好處是我們省電了,我們燈光可以共享了,但同時,兩個廁所的聲音也共享了,同時,氣味也共享了。
而這樣的一個空間狀況就會發生很多的故事,比如說我們睡覺的生物鐘相對規律的,而我們上廁所的時間,這個生物鐘也是比較規律的。如此,我們在胡同里邊,鄰居們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出現一種情況,就是在同樣的時間,在同樣的地點,甚至在同樣的蹲位,我們兩個人無數次的相見了,而且還是非常坦誠的,相見。
那這時可能會帶來一些尷尬,就是我們不得不聊天,不得不打招呼,這就必然使得大家會變得非常相熟,整個一個胡同的人,甚至好幾個胡同的人,共用衛生間的人都會變得非常相熟。
而衛生間的這個事在整個胡同里邊,是一個比較極端的空間影響生活的縮影。但是整個胡同這樣一種比較外向的空間模式,卻是在日復一日的過程當中慢慢使得這里的人們也會性格比較外向,大家對隱私,或者說一些生活當中的細節沒有那么克制,大家會更多的交流,更多東西會共享,當然,其實是不得不交流和共享。這是空間形成人們性格的例子。這也就慢慢的形成了大家的一個印象,胡同里邊的這些叔叔阿姨大爺大媽都很能聊,甚至能侃。
電影《頑主》很好的表現了80 年代北京的的社會狀況。這三個人都是在胡同里長大的,成立了3T公司,來幫助實現別人的各種夢想。所以他們總是盡可能的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利用了各種手段,也創造了非常多的可能性。而這些我認為跟人的性格是有很大關系的,那時人們的這種普遍性格可能跟那個時代北京的空間氛圍也有很大關系。
而今天的北京,或今天的胡同成為什么樣子呢?我個人認為它是在往兩極走。一方面像左邊那張圖,胡同里停滿了車,原來胡同里邊客廳的位置被車位占領了。我們原來的公共空間沒了,大家生活的質量也會變得不如以前。
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右邊這樣。我們會把這些原來的雜院整合出一個仿明清的獨立的四合院。這樣的好處,物質條件確實是提高了,而且提高了非常多,但是它變成了一個封閉的院落,鄰里之間的關系變得陌生了,可能甚至還不如樓房小區的那種鄰里關系。
這兩種都不是我希望看到的,而我希望胡同的未來,是這里居民有更多的面積可以去住,有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時很重要的要有院子,有鄰里之間的很好的一個關系。我覺得這個才是北京胡同應該有的樣子。

2 室內一隅
而作為一個建筑師,我不僅要提出問題,還必須想方設法去解決問題。
要不把樓變高,變成好幾層的房子?雖然居住面積增大了,但是它可能會遮擋別人的陽光,而且院子就沒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房子蓋到地下去呢? 這樣面積也多了,院子也有了,但是這些房子得不到通風和采光。更重要的是鄰里的關系,也沒有在空間上的交流和互動了。
直到有一天,我在胡同里看到了這個東西,一個伸縮的停車場,我似乎一下知道胡同的未來應該是什么樣子了,也許就是一個個可以上天入地的房子吧。
它在平時的時候是這樣的,沒有什么特別的。但是比如說我在上班的時候,可以把房子沉下去,空出來院子,居民可以共享,也許可以停車,也許可以老頭下棋。晚上回家以后,院子里孩子們可以在這兒玩,是一個的不會被車撞到的地方,當然我還可以把它升起來,每個房子的話都會得到好的采光通風條件,甚至我還可以把它升更高。不僅有了更多的房間,而且還出現了一個在胡同里邊大家習以為常,但卻往往忽略的盛景,一片片屋頂和大樹交織的場面,也許還會有彭于晏裸奔出現。

1 夜景

2 光影

3 光影
那么假設胡同里的空地上出現了很多這樣上上下下的房子,是不是就會出現另外一種場面,就是鄰里之間會互動。當然也許會吵架,但同樣也許會相互協調,它至少增加了鄰里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或者說有了交流才有鄰里。
所以我認為,這也許是未來胡同空間所需要的,因為它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性。就像原來胡同空間所孕育出來的鄰里關系,孕育出來的那種有更多可能性的人們的性格一樣,這比較重要。
而在2016 年底,有了這樣一個機會,我的朋友要給自己建一個胡同的家,當我把方案拿給他的時候,他也非常興奮,他也是一北京人,也有這樣的幻想。這種貌似機器的房子所帶來的不僅是對胡同即有社會問題的改善,更是一種“無限”。時間上的,關于“生命”,就像只要是會動的事物,我們都會聯想到生命,有了生命,死亡隨之而來。我們把“會動的建筑”放置在時間的長河里,廢墟、殘垣斷壁這類的詞匯便會進入人們的腦海之中。
我們都覺得他與胡同空間在“生命力”上是契合的。
可惜最終各種原因吧,我們沒能這樣去做,但我的朋友還是希望有更多的面積,上上下下可以玩的地方等等,所以就出現了B 計劃。
一間“單室”,室內邊界模糊甚至消失,一層層向上發展著,但是每一個空間我們都試著使其靜穆和寧靜。這似乎是矛盾的,如果一個沒有墻的家,只是通過樓板簡單的錯層來分隔房間,人們確實無法得到一個完整的屬于自己的空間,人們該如何在這個家中獲得尊嚴呢?
我們覺得這樣反而會給人們帶來尊嚴,人與人的平等。它不斷地提醒著家庭成員們,雖然你身處家中,但家中的每一個人都會以一個完整的社會中人的身份再現,你會對每一個人的隱私、習慣、日常癖好給予理解,包括你自己。從危險關系轉化成日常禮節的過程是這個設計真正帶給人們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是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處理,它本身也是促進某種新的家庭情感的孵化器,也是我們對當代社會中胡同空間所出現的各種人際關系變化的回應,外向的空間,也許恰恰是相互尊重的開始。
而可惜的是,我們為了跟胡同之間互動更多,朝外開了很大的一個窗戶,而這又恰恰成了2017 年封墻打洞的針對目標,如此這個施工圖已經完成的房子又流產了。
幸而,我的朋友并沒有放棄,于是我們有了C計劃,也就是現在建成的樣子,但功能已經從住宅變成了工作室。
城市管理者希望胡同是以墻的姿態出現,那么我們就做一面墻,一面百年老磚堆砌的墻,而墻上的水平窗似乎把屋頂割裂開來,使其下部的墻體更加獨立,甚至,必不可少的門,我們讓他也成為了“墻”。
而內部,仍是一個單室,但更強調了梁柱的關系,兩根柱子,分別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這是他們共同撐起的室,男人站在室的焦點上,我希望他形式感強烈,像漢字一樣有力,而女人稍遠,半依靠在墻邊,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倒下。在我們看來它代表著“平衡”,無論多少不同的材料和構造的堆砌,最終都在梁柱的力間尋得了平衡。胡同空間的生態亦是如此,那棵柱,就是鄰居間的善意和尊重。
現在看看,雖然是一個新建的房子,但是好像已經蓋好了50 年一樣。感覺似乎見過卻又陌生,可能是來自未來的回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