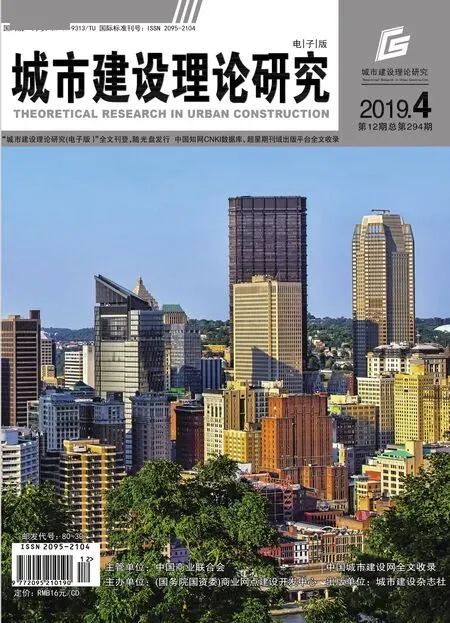淺析銅陵大通古鎮的特色民宿發展與演變
高婷婷 錢勁東 張萍萍
銅陵學院 安徽 銅陵 244061
1 、民宿溯源,時代背景和空間必要性
中國的“造城運動”一方面是朝代演替下住宅群落的演變,另一方面同樣是權力和資本主義裹挾下的產物,旋即,造成了城市發展一味地汲取單一同質的文化“養分”,使人們的生活方式漸趨機械化,市民生活飽和度低下。國內驟然一擁而起的“城市更新”弄潮,代之以模數化、標準化的建筑群體,消磨了蔚為壯觀的歷史流韻和井然多樣的城市生活,以此,發掘出民宿建筑的主旨是“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與情懷[1]。
銅陵市大通古鎮在其得天獨厚的區域定位優勢條件下(地處長江支流裹挾下的洲中小島),為游客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冷冰冰的公寓旅館的小型徽派居建風韻,入住者不僅可以感受到家的溫馨,更能盡享大通的“漁”與“娛”、“駐”與“住”的風土人情。
由于產業包圍中心戰略對我國民宿行業的影響,民宿的分布狀態呈現出以特色自然景區為中心,向周邊地區輻射的格局。由移動大數據分析得出,2016年,全國民宿房源數量為59.2萬家,19年暴增至134.1萬家,預計到2020年,民宿市場能高達300億規模[2]。日趨暴浮的數據,使良莠不齊的民宿產業日漸浮現,質量低下的劣質民宿行業也侵蝕著人們的健康,民宿空間發展的必要性愈顯強烈。
2 、大通古鎮民宿產業發展機遇與挑戰
2.1 、徽派旅游業發展趨勢與政府形勢的機遇
由于城鎮間貧富群體的差異,政府規劃扶持力度的差異,城鎮中的某些地區呈現出支離破碎的形態,如一些被文化、歷史和傳統都割裂開來的孤立的地區。民宿建筑類行業的崛起面臨著巨大的機遇。大通古鎮位于安徽銅陵縣級區域,豐富的漁牧業與地理優勢為建筑設計者帶來了獨特的構思與規劃,利用其長江流域的自然河灘,天然風貌,結合淡水豚保護區與洲中獨島的特點,重點發展風景旅游業與民宿結合的產業形式,帶動鄉村振興。
2.2 、大通民宿發展面臨的挑戰
2.2.1 、產業規模范疇拮據,帶動作用有限
大通古鎮是國家4A級景區,全年的旅客接待量和旅游總收入位于該市第二名。大通古鎮分為兩個主要組成部分,一部分位于長江支流圍繞成的江中島,其中包括和悅洲,永平村等地區,另一部分為新大通古鎮風景文化新區,全區占地面積僅70多平方千米,可供開發的特色民宿建筑少之又少,致使對周邊產業的帶動力度微弱。
2.2.2 、基礎設施不完善,產業合力微弱
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島中位于和悅洲區域的建筑因施工條件較為窘況,多為危樓或待拆遷古建筑,改建耗資大。水力、電力、電訊設備、旅游廁所、垃圾整治、醫療救治等基礎設施供不應求,在重點規劃布局區域更應著重考究古建對其周邊產業的影響。面臨著傳統的封建教條進行區域化改革難度大,區域建筑規劃難度大,地域自然風貌改進空間大等問題。
2.2.3 、文化內涵缺失,發展缺乏特色
大通古鎮已有的民宿多以旅館、農舍的形式出現,空間功能僅滿足食、宿作用,消費者希望體驗到民宿舒適的入住體驗以及與自然交融的人文情懷。隨著銅陵市的大規模城市化進程,非農業人口數量的大幅激增,歷史文化、底蘊、信條、代代相傳的歷史風韻被打破,村落人口的空心化帶來鄉土文化的匱乏,傳統民俗文化名存實亡。民宿產品的“文化”素質關系到整個城鎮的興衰榮辱。
3 、大通古鎮民宿產業發展對策建議
大通古鎮位于銅陵市郊區,古名瀾溪,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厚,境內有瀾溪街,和悅洲,野生河豚培育基地等著名景點。作為發展手工業,養殖水產業的農業強區,大通古鎮中各建筑物規劃布局井然有序,呈街區“一”字形貫通古鎮。大通古鎮的鄉村振興戰略目的,在于利用構思村鎮徽派民宿建筑藍圖,推動貧瘠產業帶動效應,促進大通古鎮民宿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自攝)大通古鎮和悅洲現址
3.1 、明確定位,建造特色徽派民宿
塑造高標準的徽派建筑產品定位是民宿得以長遠發展的承托。雖,大通古鎮的發展面臨眾多約束,然,利用大通古鎮現址的江上賞景、瀾溪古鎮、和悅洲島,等一大批傳統文化景點,采用線上線下技術宣揚大通民宿傳統文化,塑造明確的徽派文化民宿產業定位。民宿裝飾材料、裝飾色彩與地域文化聯系緊密[3],引入徽派高宅、深院、天井、木雕等傳統工藝獨創民宿新風尚。
3.2 、改善生態綠建、提升發展質量
任何建筑離不開傳統的依托與自然的承接。在大通古鎮的徽派建筑中,設計者應尋求流暢統一,規劃和諧的整體美,通過裝配式綠色建筑完成民宿產業轉型,豐富民宿產業內涵,提升消費者的消費價值觀,解決民宿產業規劃單一發展,忽視歷史底蘊難以融合新興產業而發展后勁不足的缺點,開創多元空間,實現眾創、眾籌的共享居所。將裝配式綠色建筑植根于現代建筑體系中,增加小額經濟效益,實現鄉村經濟振興和自然發展平衡。
3.3 、傳承建筑空間發展,銘刻建筑使命感
傳承歷史文化底蘊,將原始的質變建筑空間發展為以人文情懷為核心的功能空間,營造雋妙無比的建筑美學沖擊。
隨著大通古鎮景區的建設、發展、升級與完善帶動產業的連鎖效應,使原本一成不變的民宿灰色地帶轉為高強度、高收益的產業,改變徽派建筑以往群體布局的封建宗教信仰,以全新的裝配式綠色徽派建筑融入民宿設計中,使傳統文化得以大力傳承和發揚[4]不僅實現了鄉村產業結構振興,更鞭策了建筑專向生們恪守建筑營造使命感,傳承建筑營造從屬感,打造高質高標,綠色健康的民宿建筑。民宿傳承,未來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