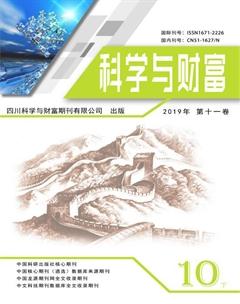書評:《娛樂至死》
摘 要:《娛樂至死》為波茲曼帶來了世界性的學術聲譽,也為媒介環境學打開了一個新紀元——正是它開啟了媒介環境學派在傳播學領域有占有一席之地的大門。”以媒介環境學派為主體的技術——控制論學派,儼然已成為和經驗-功能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成為并駕齊驅的傳播學“三大學派”。對《娛樂至死》一書的研習與解讀,自然成為理解媒介環境學不可繞行的重要把手。
一、“媒介即隱喻”:《娛樂至死》體現的媒介主體認識論
早在1953年,麥克盧漢便與卡彭特共同創辦了《探索》雜志,旨在建立文化和傳播的交叉研究平臺,成為媒介環境學創建和發展的關鍵一步。到了1968年,在麥克盧漢的建議下,波茲曼在紐約大學正式創建了媒介與文化的課程,1970年,波茨曼干脆在紐約大學創建了媒介環境學的博士點,并與特倫斯·莫蘭、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成為媒介環境學理論建構和制度規范的三架馬車,扛起媒介環境學的大旗。
作為《娛樂至死》的基本理論命題,波茲曼在全書的第一章便開宗明義地指出,媒介即隱喻:“雖然文化是語言的產物,但是每一種媒介都會對它進行再創造——從繪畫到象形符號,從字母到電視。和語言一樣,每一種媒介都為思考、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從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
在波茲曼看來,媒介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不僅是傳播方式、人類的認知習慣、審美趣味和行為方式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人類認識世界的思維模式,這對人類形成個人或群體的認知、態度和價值都起著決定作用。媒介技術發展的每一個階段與其相對應的社會文化特征都非常鮮明,可以說,媒介技術可以通過重新定義現實,對那個時代的認知模式、文學樣式和審美規范等起到了重構的作用,進而重構整個社會。
眾所周知,在傳播學研究的歷史上,在很長時期內,占統治地位的一直是美國的經驗-功能學派和歐洲文化的批判學派(結構主義符號-權力學派)。在這兩個學派的視線中,媒介往往只被視為盛裝信息的容器,學者對媒介的關注更多的是其承載的內容,以及不同的媒介實現的傳播效果。在《娛樂至死》當中,我們則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是把媒介本身作為一個獨立的事物來考察,其透視的是媒介與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構建乃至整個生存環境的關系。在波茲曼看來,媒介本身就是一種認識的方法——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實際上是用已知事物構筑未知事物的過程,這是人類無可回避的認識機制,而作為人類感知世界的中介,媒介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人們認識和辨別事物的關鍵,也正是媒介發揮作用的這種范氏,必然帶來了媒介的“隱喻化”效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波茲曼“媒介即隱喻”的論斷具有馬克思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性質,媒介,不再只是承載信息的容器,人們長久以來被內容這樣一塊“滋味鮮美的肉”所渙散的注意力,終于開始集中到媒介這樣一位“破門而入的盜賊”本身。傳播,開始被置于人類文化和思想形成過程中的首要地位。
二、“麥克盧漢不聽話的孩子”:尼爾·波茲曼媒介批判思想的理論淵源
早在20世紀50年代,波茲曼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時期,便結識了麥克盧漢,并建立了長久的友誼。波茲曼曾戲稱自己是“麥克盧漢的孩子”來描述其與麥克盧漢的學術傳承關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曾評論說:“波茲曼在麥克盧漢結束的地方開始”。
麥克盧漢看到了媒介對信息、知識等內容的反作用,提出著名的“媒介即訊息”這一論斷,認為“技術的影響不是發生在意見和觀念的層面,而是堅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變人的感覺比率和感知模式。”,從而讓媒介突破了“工具”的范疇,促使研究者開始關注傳播媒介本身可以開創的可能性,及其帶來的社會變革。
波茲曼正是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媒介即隱喻”這樣的觀點。只不過,與麥克盧漢對媒介本身的關注相比,波茲曼更關注媒介是如同通過不同的具體形式把意義傳播給大眾,并由此站在了與麥克盧漢不同的道德立場:在他看來,技術造成的后果是人性化的或反人性化的,拋開道德的立場去看待媒介是沒有意義的。他不不相信技術是中性的,因為每一種媒介都有自己所偏好的形式內容,每一種媒介都為表達思想和抒發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進而創造出獨特的話語符號環境,并最終隱喻出不同的文化內涵。
從波茲曼對于媒介偏好的表達,以及對技術的悲觀態度,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尼斯對波茲曼的影響。事實上,波茲曼對英尼斯評價極高,作為“麥克盧漢的孩子”,他甚至認為英尼斯的學術地位要高過麥克盧漢,并尊英尼斯為“現代傳播之父”。波茲曼認為,我們關于理性、批判、分析和不偏不倚的思考的觀點是與書寫文字緊密相連的,而瞬間傳遞信息的電子媒介則會助長匆忙、情緒化的判斷與回應。這恰與英尼斯“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隱藏了一個不被它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所察覺的意識形態上的偏倚或行為傾向,由此它會控制我們對周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的研究路徑一脈相承。
與此同時,我們不應該忽略的是,在波茲曼對技術理想的探討中,也可以看到芒德福的影子——波茲曼提出的工具使用時代、技術統治時代和技術壟斷時代,儼然就是芒德福前技術階段、舊技術階段和新技術階段的變體,而芒德福也早就表達了過分強調技術是導致人的異化、戰爭以及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這樣的技術悲觀態度。
因此,作為一個“不聽話的孩子”,波茲曼從麥克盧漢結束的地方開始,但在對于技術理性的認知態度上,則明確地與麥克盧漢的道德中性立場分道揚鑣,轉而從英尼斯、芒福德那里汲取了更多的理論滋養。
三、一位悲傷的教育專家:從《娛樂至死》來評析尼爾·波茲曼的媒介批判思想
作為將媒介生態引入媒介學術領域的學者,尼爾·波茲曼被北美傳播學者奉為媒介生態學真正的開山之父,其學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用技術悲觀主義來警惕我們對人類、媒介、社會之間的關系保持足夠的反思,并及時調整我們崇尚技術的危險心理及行為——在波茲曼這里,技術悲觀論者并不是不尊重技術的存在,相反,“技術悲觀主義者渾身流露著對技術的謙恭態度,他們就像古埃及的法老塔姆斯。”他對文化符號流失的以及由此而來的敘事損失的焦慮,也給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建構帶來了極具顯示意義的啟迪。但是,《娛樂至死》中,也反映出波茲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中形而上學的一面。
首先,《娛樂至死》中呈現給我們的理論視野,不是整個媒介技術的變遷史,而只是選取了印刷術和電視作為兩個關注點。結合其教育專家的學術背景以及學術轉向的經歷,我們也許可以感知,波茲曼在批判電視時,帶著一種先驗的價值觀——他不是像英尼斯、麥克盧漢、芒福德他們那樣,在梳理整個媒介技術的發展脈絡中來透視媒介技術,而是在選取具有說服力的實例來論證他對自己發現的但是所存在的社會問題的觀點。他對媒介技術的研究,是他本身便具有的人文精神與道德意識的投射,這樣的研究確實具有偉大的意義,但不能完全表征媒介演變的規律。也正因如此,波茲曼會對印刷品及電視之間做出好與壞這樣絕對的價值判斷。
但正如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所言:技術與文明作為一個整體是人類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智能活動和奮斗的結果。在人類歷史演進中,作為“人的延伸”,媒介技術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推動器前進的,正是每一種媒介本身存在的功能缺陷,激發著人們不斷創造新的媒介技術以更好地滿足人類相互交流與探索世界的需求。因此,對于任何一種媒介,采用絕對的價值判斷都是不科學的。每一種媒介都由其優勢,同樣也有劣勢,對于任何一種后繼的媒介,人類的初衷,應該都是對前一種媒介功能的完善或者彌補。比如波茲曼推崇的文字印刷,在麥克盧漢看來,是“聽覺向視覺的轉換,構建了人的心靈生活。這種心靈生活將人與外部世界分隔開來,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將人與其自身的感官分隔開來。”與其裁決一某種媒介形式的好壞,也許具有意義的是將其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長河中予以觀察、分析。
第二,《娛樂至死》中,波茲曼展示出近乎絕望的悲觀,他在序言中明確表示,“這本書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而赫胥黎的預言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結合波茲曼《童年的消失》、《技術壟斷》來看,我們不難明白,在波茲曼看來,技術便是那將毀滅我們的、深受我們熱愛的東西。他還進一步強調,“正如赫胥黎所說,我們沒有人擁有認識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是我們相信自己有這樣的才智,也沒有時間去傳播真理,或者無法找到輕信的聽眾來接受。”這些都展示出波茲曼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忽視,他將的問題歸罪于技術,并且認為人的努力都將是徒勞。
然而,在馬克思的技術認識論中,技術是人類思想的物質表現,在人與技術的關系中,人具有至上性。正如勞動創造了人一樣,技術之于人類,也絕不只是簡單的毀滅與被毀滅的關系,而是像麥克盧漢所言,是人的身體感官的延伸。技術的世界不是孤立于人類世界之外的對手一樣的存在,而是人類“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智能活動和奮斗的結果”,這一創造、革新技術的過程中,人類的各種感知能力被不斷拓展,認識與對世界的改造能力也在不斷地增加,比起絕對的悲觀主義論調,我們也許更應該把人類與技術視為相互塑造,而不是相互毀滅。我們在承認技術帶來的負面性的同時,也應該相信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波茲曼帶給我們最寶貴的財富,不應當是對媒介技術(尤其是電子媒介)的工具批判,而應當是在“上帝已死”、人類的主體性得以徹底的宣揚、實證主義站在聚光燈下并極度發展,從而使得“異化”成為可能乃至于現實的時代里,重拾人文主義關懷,重煥道德救贖之光,再次走出洞穴,走向另一個從黑暗到光明、從無知走向有知、從被遺棄走向被拯救的進步神話。
參考文獻:
[1].【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中信出版集團,2015年5月第1版
[2].【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3].【加】哈羅德·伊尼斯著,何道寬譯:《帝國與傳播》,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4].【美】尼爾·波茲曼著,何道寬譯:《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5].【美】E·M·羅杰斯著,尹曉蓉譯:《傳播學史》,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6].劉海龍:《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7].李曉云:《媒介技術的變遷及其隱喻功能的實現》(J),《新聞界》,2010年第3期
[8].李曉云:《尼爾·波茲曼的技術壟斷批判》(J),《新聞界》,2009年第10期
[9].陳力丹:《傳播學的三大學派》(J),《東南傳播》,2015年第6期
作者簡介:
譚盛,出生年月:1997.11.28,性別:男,民族:漢,籍貫(精確到市):上海,學歷: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