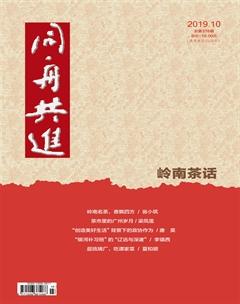德國的身份迷惑與外交轉型
孫興杰
德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它應該在歐洲和世界舞臺上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樣的問題在二戰結束后的半個世紀里并不是問題,從2009年歐債危機后,德國的身份問題變成了歐洲焦慮的問題。如果不是英國“脫歐”的話,“德國問題”會更加突出。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根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想想今天的歐洲,就像一顆尚未爆炸的炸彈一樣,引信完好無損且功能正常,炸藥依然危險。”羅伯特·卡根的比喻也是當下歐洲面臨的潛在挑戰。他曾經在《天堂與實力》中認為,歐洲在二戰后已經大轉型,朝著“永久和平”的方向發展。歐洲的和平化與德國國家身份的轉型是分不開的。戰后德國通過融人歐洲獲得了新的國家身份,德國人成為了“經濟動物”“出口機器”。卡根也感慨說,戰后歐洲在世界舞臺上的權勢是一次大崩潰。德國通過確認自己是歐洲的德國而確立了身份,德國的外交由此實現了大轉型。
歐洲的德國,還是德國的歐洲
外交是一個國家身份的“外化”,也是一個國家與外部世界溝通與交流的方式,更是自我認同確認的過程。國家身份的轉變是外交調整的根本動力,身份界定利益,當一個國家權力結構以軍事為主時,外交必然表現出比較強的進攻性色彩,擴張是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途徑。反過來,當一個國家權力結構以經濟為主,那么經濟外交就成為對外戰略的主流。
20世紀德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世紀后半期的德國與上半期的德國幾乎是兩個德國,一個是軍事化的德國,一個是和平主義的德國。回顧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可以看到,德國的國家身份一直處于顛簸之中,德意志民族雖然比較古老,但成為國家則是新近的事情,尤其是在歐洲國家中,德國是在19世紀后半期才實現統一,建立了民族國家。德國的自我定位與歐洲國際體系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開始,歐洲的均勢體系就建立在一個分裂的德意志基礎上。德國統一打破了歐洲持續數百年的平衡。
德國統一后,是不是要更進一步擴大版圖呢?要知道,19世紀后半期是帝國主義時代,擴張領土是歐洲國家競相追逐的事情。實現德國統一的首相俾斯麥深知德國擴張的限度,他要的是與歐洲和平相處,不謀求海外擴張,也不謀求在歐洲大陸的擴張。他曾說,巴爾干地區的矛盾不值得德國浪費一名士兵的生命。“鐵血宰相”在達到目標后,選擇了節制,通過令人眼花繚亂的聯盟為德國營造了一個相對緩和的發展環境,當歐洲列強瓜分世界時,德國似乎耐住了寂寞。
直到俾斯麥被趕下臺,德國的國家身份也發生了一次深刻的調整,德國從維持現狀的國家變成了修正主義國家。從1890年俾斯麥下臺直到二戰結束,德國的國家身份都沒有得到確認,兩次世界大戰也可以說是歐洲的內戰,進一步說是歐洲國際體系應對一個不斷崛起的德國的問題。“德國問題”成為歐洲的夢魘,兩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歷史中的“歐洲時代”也結束了。而德國呢?分區占領后,統一的德國又被分裂了。
聯邦德國面對的不僅是被分裂的德國,也是國家的重建。兩次世界大戰表明,德國既有的崛起之路是行不通的,德國必須解決國家身份的問題,必須重新確立自己與歐洲之間的關系。德國是歐洲的德國,還是歐洲是德國的歐洲。在分區占領以及冷戰的背景下,德國只有融人歐洲才能獲得新生。在政治學家赫爾弗里德·明克勒看來,西德的貨幣改革是聯邦德國獲得新生的開始,也因為貨幣改革,東西德在經濟上被分裂,西德融入到了美國主導的陣營中,馬歇爾計劃與貨幣改革共同促成了德國身份和自我意識的轉變,那就是要發展經濟。明克勒認為,貨幣改革就是德國的國家神話。
經濟發展成為德國人的信仰,也是德國重獲自信的最主要途徑。戰略、外交、防務不再是國家的主基調,通過北約和歐洲一體化,德國從歐洲舞臺上淡出了,客觀地說,德國成為了“幕后強國”。戰后70年,德國國家身份實現了歷史性的轉型和定型,德國是歐洲的德國,只有如此,才能解決“德國問題”。柏林墻倒塌后,德國再次統一,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間,德國依然堅持此前的國家身份和發展戰略,這是德國的成功之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論家艾利森說,“在冷戰結束時許多人預計,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將恢復昔日的霸權野心。盡管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德國注定要恢復自己在歐洲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但它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良性的。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讓他們的國家陷入泥潭后,德國領導人找到了一種新的方式來施加自己的權力和影響:領導一個統一的經濟秩序,而不是以軍事為主導”。
歐債危機后,德國的實力與歐洲的頹勢形成了鮮明對比,德國如同一頭難以掩飾實力的大象一樣。在歐元區的危機中,德國的經濟實力和金融實力轉化為外交的強制力,也因此,希臘人將默克爾視為敵人。對于德國來說,將歐洲舞臺“讓出去”70年后,不得不再次面對歐洲與德國關系的問題了。這一個問題從現代德國誕生之際就一直存在,這也是德國外交轉型的核心命題所在。
十字路口上的外交轉型
在二戰后相當長的時間,我們幾乎可以認為“德國問題”解決了。明克勒認為,歐洲鄰國經過一陣觀察和遲疑,開始逐漸認識和接受了這個新的形象:德國人又來了,不過不再是身著軍裝、頭戴鋼盔的侵略者,而是穿著泳裝、手握鈔票的度假者。外國人對德國人的新認識,印證了聯邦德國建國神話的核心和本質。德國人也由此更加相信自己的“神話”了。“神話”并不是虛假的,因為它是構建一個國家身份和認同的必備條件。現在來看,“德國問題”只是被掩蓋起來了,這里既有德國人的自我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一個約束和規制德國的多邊體系——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一體化的存在。過去運行了70年的制度似乎遇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德國不得不再次面對“德國問題”。
第一,戰后德國的經濟神話受到了越來越大的沖擊。歐債危機是非常明顯的例證,我們可以說戰后德國的信仰就是馬克,一方面新馬克讓德國解決了通脹痼疾,恰恰是通脹讓德國進入了法西斯主義的軌道,對歷史反思得越深刻,德國人對馬克越依賴。在兩德實現統一的過程中,最核心的成本或代價就是放棄了馬克而接受了歐元。當時德國總理科爾就提出,馬克是德國人的信仰。歐元是馬克的翻版,而歐洲銀行則是德國中央銀行的化身。歐債危機其實不是經濟或貨幣危機,而是財政危機,沒有實現政治整合以及必要的財政轉移,單一貨幣需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德國在歐債危機期間奉行的緊縮政策遭到了歐元區國家的抵制,日耳曼的歐洲與拉丁歐洲之間的對抗與分野出現了。
第二,德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景越來越不明朗了。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就說,德國增長模式可能走到了盡頭,雖然加上了比較含蓄的“可能”,也說明法德之間的合作模式走向了終結,在歐洲一體化的過程中,德國主要扮演經濟發動機的角色。德國人的技術創新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對穩定貨幣的執著,德國央行的唯一目標就是保持貨幣穩定)讓德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尤其是歐元區成立后,德國出口一路高歌,在歐元區形成了新的經濟結構,德國生產,南歐消費,德國賺取巨額貿易盈余,這樣的模式也是歐洲經濟乃至歐洲一體化面臨的巨大挑戰。
第三,歐洲一體化到了一個瓶頸期,隨著德國崛起,融入歐洲與歐洲擴大相伴隨,然而,英國“脫歐”代表著歐盟不可能無限擴大,相反,它到了一個轉折點上。巴納特就認為,英國“脫歐”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英國人對昔日大英帝國榮光的懷念。歐盟的離心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一種勢均力敵的態勢,德國必須直面自己在歐盟發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強勢德國總是會引發人們對德國歷史的回憶,德國在反思歷史,但并沒有接受歷史,也沒有真正與歷史和解。
第四,戰后歐洲一體化基本的安全框架遇到了挑戰,那就是大西洋共同體的裂痕空前擴大,《金融時報》就發表評論說,美國和德國到底還是不是盟友。美德之間的爭論體現在默克爾和特朗普之間糟糕的私人關系上,但這只是美德關系的一個縮影,更大的裂痕在于大西洋共同體的安全合作基石在松動。一方面美國不斷要求德國提高防務經費支出,另一方面對德國推動的歐洲防務合作又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甚至是嚴詞警告。2018年歐盟28個成員國中有25個簽署了“永久結構性合作”協議,逐步推動歐洲防務合作,但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的官員給歐盟外交代表莫蓋里尼的信中認為,這是在轉移北約的資源,并會帶來北約和歐盟之間不必要的競爭。
第五,法德軸心結構面臨著歐盟“去中心化”的挑戰。首先是馬克龍與默克爾的關系并不是很和諧,另外,英國“脫歐”后,歐盟的權力結構必然將重新調整,最近歐洲議會選舉中,民粹主義政黨的席位增加,同時西班牙的地位在提升,西班牙首相與馬克龍共進晚餐并且提出了關于歐盟發展的構想,英、法、德、意、西以及強勢的東歐國家之間形成了新的權力格局。
德國再一次到了重新認知和定位國家身份的時候了,外交不再是德國發展戰略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是引領德國實現國家身份轉型的牽引力量。
(作者系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