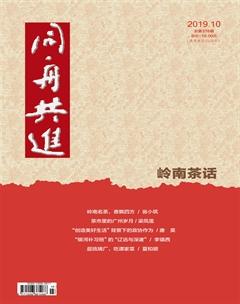英國:“脫歐”就能走出困境嗎
江東瑜
無奈的選擇
日不落帝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后,終于迎來了夕陽紅。1947年,印度宣告獨立,帝國時代正式宣告終結——其實此前已名存實亡很久了。聊以慰籍的是,帝國的殘骸塑造了“英聯邦”,仍發揮著特殊的經濟作用,比如互免簽證和關稅同盟。而“英美特殊關系”的存在也讓英國更為安心。
與此同時,歐陸一片狼藉,德國被肢解,法國和意大利名實俱損,也無法承擔世界一極的角色。老帝國頹勢難挽,新帝國氣勢如虹。蘇聯的陰影冉冉升起,唯有美國可以與之對抗。“老歐洲”不得不接受美國的庇護,場面尷尬。
與英美之間“父子情深”不同,法蘭西對美國執牛耳的局面是別有心曲。“昔與爾為鄰,今與爾為臣”的境況肯定不是驕傲的高盧雄雞所能接受的。1959年戴高樂執掌法國后,歐洲聯合的速度加快,以“抱團取暖”強化獨立于美國的立場。
最有趣的是美國的態度,美國對“英美特殊關系”有自己的底線。美國人對殖民主義的天然反感,以及尋求國際領導權的現實訴求,決定了英美之間的目標沖突。英國的戰后外交框架顯得不切實際。
按照丘吉爾著名的“三環外交”設想:以第一環英聯邦和大英帝國作為力量的基礎;利用第二環英美特殊關系,借重美國的力量重建世界大國地位;進而利用第三環聯合起來的歐洲,謀取西歐的領導權。
可惜每一環都有問題。美國無意配合英國維持“帝國形象”,尤為反對其維持在原殖民地的特殊權益。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國不惜對英國發出軍事威脅,體現了第一環和第二環之間的矛盾。而且美國人知道戴高樂是個“壞孩子”,卻視之為“有用的壞孩子”——歐洲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立,美國的防務壓力顯然也會減輕不少。英國的本意是挾美自重,成為第三環的領導者,但美國對英國的角色設定可沒有那么重要,只希望英國可以成為一個歐洲聯合體中的堅實盟友,因此敦促英國加入歐洲聯合的進程。“英美特殊關系”同床異夢,讓英國的“孤立”不怎么光榮。
更致命的是經濟。英國的走向是兩個“超主權聯合”之問的經濟競爭——英聯邦VS.歐洲聯合體,而英聯邦迅速敗下陣來。二戰后的英聯邦一度占據了有利地位,英國在聯邦范圍內實現了一半的出口,但這個不錯的開局也帶來了副作用。那就是實業界在市場保護中不思進取,設備更新和技術升級遲緩。當英聯邦成員在經濟上逐步自主時,現成的市場開始萎縮,英國企業競爭力低下的問題凸顯。國內的經濟形勢也很不樂觀,從艾德禮政府執政開始,就把經濟拖入了福利主義軌道,維持戰時的計劃經濟模式,英國經濟從此陷入泥沼。1950年到1969年的20年間,英國的經濟增長率都在2.6%左右,僅為法、意等的一半左右。這就是經濟學中的“英國病”。
外交、政治、經濟的三重逼迫下,留給英國的選擇并不多。1961年英國第一次提出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這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更可悲的是,戴高樂否決了英國的申請,并在其后的1967年再次否決。甚至在戴高樂離任后,他對英國的“詛咒”依然有效——英國必須公開放棄“英美特殊關系”才能加入歐洲俱樂部。很明顯,這是一種形式上的羞辱,沒什么實質意義。1971年英國履行了這一“效忠儀式”,才換來了兩年后的正式加入——同時宣布退出了英聯邦的關稅聯盟,這是帝國最后的葬禮。
英國加入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劇烈的痛苦和羞辱,很難想象彼此之問此后能情投意合。
即使加入了歐洲一體化進程,英國仍是異類。作為歐盟兩大支柱的歐元區和申根區,都沒有英國的影子。它在歐盟的影響力也極為有限,遠不及德、法的領導地位。而“英美特殊關系”當然不會因為一次公開宣告結束,撒切爾一里根時代、布萊爾一小布什時代體現的特殊關系遠超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水平。
可以稱為“一體化”成就的是:歐陸和英國的意識形態、政治文化的趨同。福利主義、全球主義、環保主義等歐盟標準已跨越了英吉利海峽,成為了英國社會的主流。撒切爾夫人離開唐寧街十號的背影,就是英式保守主義的最后謝幕。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套“歐洲共識”終于把歐盟的元氣也消耗殆盡,“英國病”沒好,“歐洲病”又來了。其實,從1971年英國“效忠”歐共體開始,“脫歐”的幽靈就一直徘徊在倫敦上空。
改革的可能
1974年至1975年,剛剛加入歐共體的英國就開始了與布魯塞爾的“重新談判”。工黨提出保守黨政府加入歐共體時的條件不合理——英國承擔的歐共體預算太高了。其實更深層的問題是,工黨內部在歐洲議題上的高度分裂,中左翼原則上不反對加入歐共體,左翼則把歐共體視為對抗蘇聯的“邪惡聯盟”,必去之而后快。“重新談判”并沒有獲得工黨政府所希望的結果,不過由此衍生的1975年6月6日公投意義重大——2/3的英國人選擇了“留歐”,強大的民意終結了工黨的內部分裂,保證了英、歐關系其后30年的穩定。然而,英國政壇質疑歐盟的聲音并未就此消失,而是逐步轉移到了保守黨陣營。
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她一改早先支持加入歐共體的態度,在柏林峰會上豪言“把我的錢還給我”,重提歐共體預算分攤的議題。鐵娘子的“疑歐”態度老而彌堅,1992年她在荷蘭海牙發表政治演說,全面闡述了對歐共體前途的憂慮:布魯塞爾日益集權化、官僚化;德國借助歐洲一體化增強影響力;歐洲一體化加劇了與美國脫離的趨勢,等等。20年后,撒切爾夫人的大部分預言都實現了,英國進入新一輪“脫歐”高潮。
歷史在重演,卻走向了另一個方向。2016年6月23日,時隔30年后,英國國民選擇了“脫歐”。首相卡梅倫只得吞下這個苦果,把爛攤子留給特雷莎·梅。特雷莎·梅面對木已成舟的事實,意圖爭取與歐盟“協議離婚”,愉快分手,可這一正常的思路卻遭遇了一連串的打擊。歐盟惱羞成怒,“脫歐”協議條件苛刻。保守黨內部以約翰遜·鮑里斯為首的“反歐”派也不愿對歐盟做出讓步。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科爾賓領導的工黨作為堅定的“留歐”派,其策略居然是阻撓“脫歐”協議達成,以逼迫保守黨下臺。這就形成了“留歐”派和“反歐”派兩家死對頭一起對“脫歐”協議說“不”的怪異局面,孤立無援的特雷莎·梅在心力交瘁后下臺。科爾賓和歐盟都不得不面對最糟糕的結果——主張無協議“脫歐”的保守黨強硬派約翰遜·鮑里斯上臺了,英國真的要從歐盟“下船”了。
但“下船”就能走出困境嗎?“脫歐”僅僅反映的是英國社會對現狀不滿的情緒,英國的重重問題主要出于自身因素,“歐盟的拖累”并不存在于現實。比如移民爭議,不屬于申根區的英國主要移民來源是原殖民地的印巴,近年來亞洲移民增加迅速,最后才是歐盟內部的波蘭。而難民問題對英國也沒有形成太大的沖擊。“脫歐”唯一的好處,是可以不受歐盟社會政策標準的約束,迅速推行有力的改革,但實際上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內部。混亂的“脫歐”進程中暴露出的問題——無原則的黨爭、政治投機和政治民粹化,這樣的政壇怎么推進改革?
更關鍵的問題是民意。2018年英國的稅負水平已達到50年來最高位,占GDP的34.6%。而英國國家社會研究中心的民調統計顯示,僅4%的受訪者支持政府降低稅收和減少開支,多數人已厭倦了財政緊縮,支持增稅、增大福利開支。但問題在于,“脫歐”公投之后,英國政府已沒有更多的儲備資金支持這些支出。對英國來說,經濟放緩、離開歐盟的天價費用以及借貸成本增加,都在形成財政壓力。如此民意基礎,改革沒有任何可能。
(作者系冰川思想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