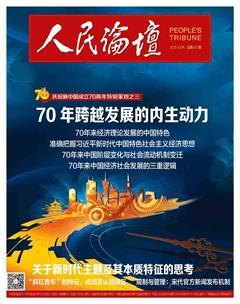多措并舉助力稅法品質優化
【摘要】優化稅法品質,應成為稅法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戰略布局上,要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建構納稅人公平負擔的稅法體系,強化保障納稅人最低生存權,加強納稅人財產權保障,多措并舉營造各方利益平衡格局,助力稅法品質優化。
【關鍵詞】稅收法定 稅法品質 最低生存權 財產權 【中圖分類號】D922.22 【文獻標識碼】A
稅法品質的優化需要法治的支撐。目前我國稅法改革已進入快車道,稅收立法已經從注重形式合法性轉向提高立法質量。下一步,優化稅法品質,應成為稅法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
稅收法定彰顯法治,是稅法的核心原則,其形式面維護法的安定性、實質面保障納稅人財產權。針對實踐中出現子法超越母法范圍,下位子法與上位母法抵觸的情況,在作為糾錯救濟的司法審查的具體案件中,應當審查稅收行政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是否有違法律優位及法律保留原則,以檢驗稅收法源的資格。在每一個公平、公正的案件中,使納稅人真切受到良法善治的感染,不斷提高納稅人權利意識,提升納稅人整體納稅遵從度,實現從被動繳稅到主動納稅的轉變,營造良好的稅收法治環境。
2015年修訂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為法院司法審查提供了規范保障,其中第53條及第64條賦予法院在訴訟中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的權利。稅收法定原則強調稅收主體等相關稅收構成要件必須由法律規定,任何稅務機關的行政行為不可與之抵觸,否則有違“法律優位”;而且法律所定的納稅義務相關事項,也不得由稅收法規或稅收規范性文件直接任意創設、變更,否則有違“法律保留”的要求。這實際上要求稅收法規尤其是稅收規范性文件不得違背法律規定,更須對“法律保留原則”進一步細化,發展出“層級化保留”體系。屬于“絕對保留”的事項,須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第6項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3條第1項的相關規定;屬于“相對保留”的事項,本質上具有法律的從屬性,可視為法律的延伸,稅務機關可在法律的明確授權下,對法律沒有規定、規定不明等情況作出補充性規定;屬于“無須法律保留”的事項,基本上是稅務機關基于行政運作需要制定的,無須法律授權即可制定頒布與稅務行政有關的細節性、技術性規范性文件,但此類稅收規范性文件不得與上位法律抵觸甚至增加法律沒有規定的事項。
適用稅收法定原則時,先通過稅收法規的法律優位前置審查以及法律保留進階審查,該審查階段旨在篩選稅收法規的“法源”,過濾不符合稅收法定原則的案件。在此審查階段外,為了進一步保障納稅義務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延伸審查稅收法定在適用時衍生的問題,規避其被架空的危險。該階段稅收法規的“適用”審查,主要從課稅要件明確性審查稅收法規的可理解性、可預見性與可司法審查性,避免不確定法律概念被濫用造成條文模糊,形成法的安定性,使納稅人可以預見,并在合理合法的限度內妥善安排經濟生活。禁止類推適用主要限制通過類推的方式不當擴大課稅要件,使納稅人承擔本不應該承擔的納稅義務。其他法律補充禁止,則是限制超越制定法文本的“可能性文義”,進行法律續造,妨害納稅人的可預見性。
建構納稅人公平負擔的稅法體系
稅法的重新分配性價值意味著,通過法治化手段調和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協調和平衡各方利益。在稅法法治的框架內,納稅人不僅通過履行納稅義務來換取個人經濟自由的形成空間,更通過稅法達到一定程度上的利益重新分配。這就要求稅法整體更具有普遍性、平等性。而體系上具有一貫性,納稅人承擔稅收分配則越公正,其要義是必須通過一致性的規則或具有普遍性的衡量標準,建構和諧統一的公平負擔稅法體系。
稅法上要求的實質公平,并未預設一個固定的實現方式或實現等級,而是要求立法者必須充分考量不同納稅義務人之間的落差并予以協調。稅法上的公平要求在納稅義務人主體之間進行公平分配,包含橫向的公平和縱向的公平,其目的是實現平等課稅、普遍課稅、量能課稅。尤其是,量能課稅作為稅法的結構性原則,是建立在納稅人可實際支配財產上的,依據納稅人經濟上的給付能力,要求稅收負擔能力高者相較稅收負擔能力低者按照比例負擔相應更多的稅收。但這并非單純要求稅收負擔能力高者理應累進地多承擔稅收義務,而是要建構納稅人公平負擔的稅法體系,解決分配結構失衡、分配差距過大、分配不均等問題,使納稅義務人均享有同等的經濟自由,負擔相對應的財務責任,從事物本質出發依其個人的給付能力衡量課稅標準。
強化保障納稅人最低生存權
最低生存權的保障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積極面,要求國家提供社會救助確保公民所需;消極面,則主要體現在稅法上,稅法防止過度侵犯納稅人財產權而形成絞殺式稅收,核心領域是建立“課稅禁區”,以保障納稅人符合“人的尊嚴”的最低生活保障。征稅對象局限于納稅人扣除保障最低生活的剩余財產,納稅人維持生活所需的再生利益是國家課稅權界限。納稅人生存必需費用,應當優先于納稅義務受到絕對保障,同時,應當禁止預先奪取納稅人生活所需,之后再通過社會救助的形式返還,因此不得制定法律規范對納稅人的最低生存需求造成侵害。
納稅人最低生存權保障與“人的尊嚴”息息相關,納稅人最低生存權保障等于強制性的立法要求。立法者有立法義務保證其所制定的法律必須足以滿足每一個納稅人維持一切生存所需,包括生理所需、人際關系協調,以及最低限度參與社會、文化與政治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各項物質條件等。立法者在其立法形成空間內,必須以正當法律程序,采用可信的數據和計算方式,實事求是地調查所有維持最低生存所需的支出,而這些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適時反映物價波動、消費提高等外在經濟環境變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4條、第5條有關個人所得稅的免稅額,即彰顯出納稅人雖有納稅的義務,但是為保障納稅人生存所必需,不將其作為課稅標的。
加強納稅人財產權保障
財產權保障在于確保納稅人通過支配財產得以自我形成、自我發展,以自主實現其具有“人的尊嚴”的生存。現代法治理論強調財產權保障,不但防止稅收侵害財產權的本質,還應該保障納稅人在納稅后,仍擁有其工作或財產所獲取的相關收益,更可以享有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質保障。縱使由于時代變遷、經濟形態改變,財產權的存續保障仍會將其保護領域擴及較新的財產累積與支配形態上,形成諸多新興保護形態。其并非考量課稅是否違反財產權保障的意旨,而在于課稅權對納稅人整體財產狀態干預到何種程度。財產權保障要求課稅必須具備正當理由,且經正當程序才得以在一定程度內限制財產權,就此課稅不應當根本性地變更或侵蝕財產權。
課稅與經濟自由之間并非處于二律背反的緊張關系,而是彼此互相補充,屬于財產權保障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私法自治保障的必要前提。由于課稅涉及限制財產權,其經濟上的負擔性質已經成為私經濟交易必須考量的條件。稅率、稅收優惠產生誘導、規制效果,可能形成或排除特定的市場活動。稅收客體依存在經濟行為的過程與結果中稅基的加、減項數額的納入或排除,形成稅收與私有用益的界限。例如,以房屋稅等為代表的財產稅,征稅范圍僅可限制在財產衍生的金錢收益上,不可觸及財產本身,否則即有絞殺財產本體的作用。
稅收本質上就是法治保障財產權及市場經濟的環節之一,稅收依存于市場經濟行為,無法獨立或與之相悖。因此,稅收立法、解釋必須在法治秩序的框架下,作為維持財產權和市場經濟的制度性前提。如果僅單純地適用實質課稅原則來解釋、調整私法概念與事實評價的結果,即有可能侵蝕財產權的核心領域,過度干預市場經濟活動。就此加強納稅人財產權保障的制度性保障思維,內含法治的時代要求,也籍以厘清稅收與市場經濟的制度性定位。
(作者為吉林大學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①黃衛:《論稅收法定原則與法律漏洞填補》,《法律方法》,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