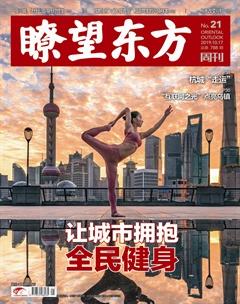人的城鎮化需尊重客觀經濟規律
陸銘

從1978年到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8%提高到了60%左右。中國用4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城鎮化進程。
經過幾十年的城市建設,我國的城鎮化取得了較大的成就。然而在過去的城鎮化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在黨的十八大確定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方向后,人們對城鎮化的方向和路徑的討論逐步深入。
過去,由于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曾走過彎路:建設用地指標被大量配置到中西部和東北那些人口流出地,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大城市)這些人口流入地,土地的供應增長速度反而慢了下來,結果出現了城市發展中土地和人口的空間錯配。
換句話說,有土地和住房需求的地方沒有得到充分供應,而有土地大量供應并建了大量工業園和新城的地方,人口卻持續流出。
出現空間錯配的原因是,一方面,各地政府希望通過城市建設來拉動GDP增長,從而實現稅收最大化和土地增值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面積擴張又受制于城市建設用地指標管制制度,建設用地的配置沒有按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來實施。
最近這些年,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上述問題逐步得到決策者越來越多的重視。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尊重城市發展的規律,城鎮化相關政策隨之出現了一系列變化。2019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調整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
首先,城市發展的導向已悄然出現變化,大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概念被加強。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與此同時,國家級中心城市,已成為區域經濟的增長極。2019年伊始,都市圈的概念又得到了強化,進一步強調了核心大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帶動作用和相互之間的一體化進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要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
其次,決策層對于推進人的城鎮化有了更為明確的決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區常住人口在100萬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已陸續取消落戶限制的基礎上,城區常住人口在100萬~300萬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在300萬~500萬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并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超大特大城市,教育水平對于積分落戶的影響將逐步削弱。
城鎮化的進程是否尊重規律,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是一個全局性的戰略選擇。
第三,為了配合人的城鎮化,決策層明確提出城市建設用地的配置,要和人口的流動方向一致。《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提出,在安排各地區城鎮新增建設用地規模時,進一步增加上年度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的權重。在前幾年已經提出不同地區之間可以進行建設用地指標的跨地區再配置的前提下,今年又提出“探索落戶城鎮的農村貧困人口在原籍宅基地復墾騰退的建設用地指標由輸入地使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土地管理靈活性,使優勢地區有更大發展空間。
城鎮化并不是為了機械地提高人口城鎮化的比重。城鎮化的進程是否尊重規律,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是一個全局性的戰略選擇。
快速的城鎮化是中國的幸運,但今天的城鎮化仍面臨諸多挑戰。中國的城鎮化要補齊短板,不僅要讓已經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接近三億外來人口能夠逐漸安居樂業,也要幫助一部分農村人口就地城市化。與此同時,更應重視人口異地城市化并向大城市集聚的客觀規律——由于大城市在現代經濟發展中強大的規模效應和引領作用,人口持續向大城市集中成為全世界范圍內的一個普遍現象。
城市應該讓在此就業、居住、納稅的人們都獲得平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權利,這是衡量一個國家現代化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也是我們對未來城鎮化的美好期許。
全國城鎮化率排名前10的城市

數據來源:全國各地區統計公報或年鑒(沈陽、大連兩市為2017年數據,其他城市均為2018年數據) 制圖/ 開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