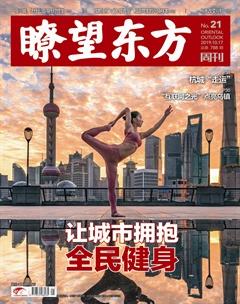去蘇州,賞花燈
李璇

2019蘇州同里中秋國慶燈會,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來賞燈游玩
每逢中秋、上元等傳統佳節,蘇州家長都會為自家小孩買一盞兔子燈,而孩子們拖著兔子燈滿巷子跑的場面,也構成了節慶時分姑蘇城里的別致景色。
兔子燈是蘇州燈彩的一種傳統樣式。蘇州燈彩史稱“蘇燈”,興于南北朝、盛于唐宋。南宋文學家周密在《乾淳歲時記》中便寫到了蘇燈的精美綺麗:“燈之品極多,每以蘇燈為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著色便面也。”
2008年,蘇州燈彩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擴展名錄。
“人們常說,燈帶來了光明,而蘇州燈彩是燈與彩、光與色的結合,它不僅為蘇州帶來了光明,更為蘇州人的生活增添了幾許美好。”蘇州燈彩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汪筱文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吳門畫派與蘇州燈彩
提起蘇州,人們第一個想到的往往是蘇州園林。蘇州燈彩之所以能夠位列四大燈彩流派(蘇燈、福燈、粵燈、京燈)之首,也與蘇州園林頗有關聯。
從外在形態上看,蘇州燈彩大都以蘇州園林的亭、臺、樓、閣為主要造型范本,體面特征上又分為四、五、六、八四種,其中四面取春夏秋冬之意,五面代表著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六面意寓“六合”和和合,八面則象征著“八面和諧”。
“就連拱、中、底的結構比例,也是符合黃金分割比的建筑美學的。”汪筱文說。
做成一盞蘇燈,需要“扎糊剪繪”四道工序,“扎”是扎架、做造型,“糊”是糊燈身,“剪”是剪紙,“繪”是畫燈面。
四道工序看上去不難,學起來卻是對耐心與悟性的考驗。“學徒三年,才能夠做出一盞燈,尤其是蘇州燈彩如今基本都用絲綢類材質制作,在絲綢上作畫是有講究的,與在宣紙上畫大不一樣,除繪畫技巧外,還要掌握綢布的暈化程度,因此即便此前學過繪畫,進入燈彩行當也還要再三摸索。”汪筱文說。
四道工序中,“繪”是最為特別的。汪筱文介紹,蘇州燈彩講求“好燈必有好畫”,燈面畫作水平的高低,往往決定了一盞蘇燈的價值,而“繪”的內容,又與蘇州的藝術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明代中期,以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等名家為代表人物的吳門畫派在蘇州一帶興起,吳門畫派的繪畫理念與文人意趣,深深影響了蘇州燈彩的制作思路。
“明代以前,人們對燈彩的定義是‘看花燈‘鬧花燈,吸收了吳門畫派的繪畫技藝后,才開始有了‘賞花燈的說法,從‘看‘鬧到‘賞,意味是非常不同的,蘇州燈彩也就此迎來了鼎盛時期。”汪筱文說。
搶救經典與適時創新
“我們要把蘇州燈彩最精細、最巔峰的技藝傳下去。”汪筱文說。
宋代的“萬眼羅燈”,是蘇州燈彩歷史上最為知名的作品,燈上共有七八千只眼孔,構思巧妙。南宋詩人范成大曾在《上元紀吳中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中以一句“萬窗花眼密”來形容萬眼羅燈的觀賞效果。
在汪筱文掌握蘇燈制燈技藝之時,萬眼羅燈早已失傳許久,復原這盞燈,成為汪筱文多年的心愿。
最初,汪筱文與女兒汪麗秋一起試著在古籍中尋找萬眼羅燈的蛛絲馬跡,不料卻只找到只言片語,根本無法發現可供參考的制作細節。他又去拜訪蘇州城中的制燈前輩,將每個人對這盞燈的理解拼湊起來,重新繪出畫稿。
經過兩年籌備并耗時四個月制作,萬眼羅燈終于在汪家父女手中復現,而這盞燈上的眼孔已達到兩萬多只,大大超越了前人的作品。
如今,萬眼羅燈被汪筱文捐獻給蘇州非物質文化遺產館,與其他蘇州非遺作品一起,留住了蘇州的城市文化記憶。
在搶救經典作品之外,汪筱文還十分注重探索蘇州燈彩的創新路徑。
傳統的蘇州燈彩要忌色,黃白兩色是喪事上用的,燈彩不可以使用;紅色與紫色不能配在一起用,因為不符合過去的審美。汪筱文則打破了傳統限制、大膽用色,以漸變、過渡等方式實現了現代審美的配色。
更為突破性的嘗試,還體現在汪筱文開創了第二代蘇州燈彩的格局。
從1984年汪筱文在蘇州拙政園燈會上成功展出“絹衣泥人”動態人物燈彩組合景開始,動態的燈彩景組日漸在國內外的燈會與展覽中受到贊譽。此后汪筱文又將蘇州燈彩與現代游樂設施相結合,為廣州東方樂園研制了一款《古燈奇觀》游樂項目。
在多番探索下,蘇州燈彩的燈會體量和游賞范圍得以大大拓展。
期待燈彩與城市互動
“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影燈戲,春前臘后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范成大以一首《燈市行》,道出了蘇州燈市昔日的盛景。
蘇州燈彩向來有“三春靠一冬”的說法,季節性明顯。農歷八月之后,燈彩市場才漸漸火熱,在元宵燈會時達到頂峰,而一旦過了元宵節,燈彩作品便又乏人問津。
近年來,西安、南京等城市都在燈會品牌的打造上頗有舉措。2019年,西安、南京兩座古都更是首次聯手舉辦“雙城燈會”。
正因如此,燈會對于蘇州燈彩行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近年來,由于蘇州減少了燈會數量,汪筱文漸漸產生了行業危機意識,擔心蘇州燈彩技藝后繼乏人。
“蘇州燈彩講究精細美巧雅,學藝太難,本就是個辛苦行當,現在年輕人都不愿意學了,更何況手藝人大部分的收入還是依靠燈會的,燈會一少,收入受到很大影響,很多人都轉行了。”汪筱文說。
汪筱文透露,如今蘇州從事蘇州燈彩制作的手藝人已不足50人:“我都20年沒有收到徒弟,甚至整個行業都沒有40歲以下的年輕人了。”
面對行業困境,汪筱文積極尋求破解之道。已年過七旬的他,還堅持到蘇州各中學去開辦蘇州燈彩公益講座,讓更多年輕人了解蘇州燈彩的歷史,近距離感受傳統技藝的魅力。
與此同時,汪筱文也呼吁蘇州能夠重新打造城市的燈會品牌。
“像蘇州燈彩這樣的傳統手工藝,只有在市場上形成了品牌影響力,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蘇州是文化底蘊深厚的城市,應該年年辦燈會,為燈彩藝人提供發展的舞臺,也為民眾的文化生活增添城市特色。”汪筱文說。
事實上,近年來,西安、南京等城市都在燈會品牌的打造上頗有舉措。2019年,西安、南京兩座古都更是首次聯手舉辦“雙城燈會”。
秦淮燈彩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顧業亮曾表示,南京打造“秦淮燈會”文旅品牌,在花燈的設計和制作上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有了市場,自然就會有藝人愿意做燈。這是一個良性循環,不僅吸引了大量游客,而且能讓燈彩花樣不斷翻新,成為南京的代表性旅游產品。
汪筱文期待,以西安、南京為參照,未來蘇州燈彩也能與蘇州城實現更多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