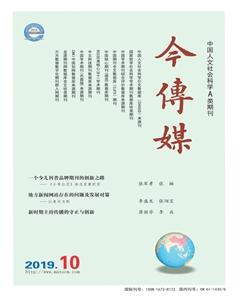從古詩詞看社會傳播各要素
張帆
摘 要:我們身處信息爆炸的時代,社會傳播無所不在,這是中國當今社會的重要時代背景和熱門時代議題。本文在傳播社會學的視角下界定“社會傳播”的概念,而后將社會傳播作為主體間性溝通行動,以中國古詩詞這一豐富的文學經典為素材,靈動地分析社會傳播各要素及其鮮明的特征,并從其中感受到了溫情的生活氣息和厚重的人文關照。
關鍵詞:古詩詞;社會傳播;要素;溝通行動;人文關照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10-0144-04
中國古代的詩詞曲賦之文學瑰寶中蘊藏了眾多鮮活的生活情景,其有意或無意中描述的“社會傳播”情景更是傳神得令人嘆為觀止!所謂博古通今,我們也正好借此加深對當今傳播活動的認識。
一、傳播社會學視角下的“傳播”概念
在從中國古詩詞中體會“傳播”的魅力之前,我們首先對“傳播”的概念作理論回顧和基本界定,這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
“Communication”,英文原詞的意義豐富而多變,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獲得“傳播”的意義,如今漢譯為“傳播”一詞。
在傳播學鼻祖、集大成者施拉姆生活的年代,大眾傳播(廣播、電視等)方興未艾,而互聯網傳媒還未普及,也無法引起他們足夠的注意。所以,在傳播學先驅們看來,傳播即意味著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s)。施拉姆在其《傳播學概論》一書中總結到,大眾傳播模式由五部分(媒介組織作為傳播者、各種類型的受眾、相同的大量的信息、推測性的反饋以及大量的信息來源)構成[1]。
而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又譯為“交往行動”)理論恰恰能將上述傳播模式零散的部分貫通起來,消弭其中還原論的缺陷。
歸根結底,傳播是一種人類的活動,人構成傳播的主體、目的并創造傳播的條件,而“溝通行動的雙方既是信息的傳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并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彼此的互動來影響對方和信息環境,實現信息的交流和共享”[2],也就是說,溝通行動的成員通過語言的交流并經由相互包容、共同合作的共識來調整一己之見,以達成互相理解的行動目的。從這個角度上說,社會傳播也可以看作是溝通行動的一種。
通過施拉姆等學者對傳播之模式和過程的詳細闡釋及溝通行動理論的銜接,“傳播”的含義已經呼之欲出了。所謂“傳播”,就是某一主體(可以是個體、組織或群體)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通過某種媒介和途徑向另一主體來表達某些意義的溝通行動。
二、古詩詞中的傳播各要素
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行動,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傳播;用以表情達意、溝通交流的傳播,體現了人際互動的種種樂趣、溫情與關懷,展現了豐富多彩的日常世界圖景。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能夠表示社會傳播的古詩詞盡可采擷,輔以上述思想家(尤其是哈貝馬斯)的傳播理論,我們將開啟傳播視野下的生活旅程。
社會傳播作為一項完整的社會行動,由以下要素——有目的之主體、實質內容、載體(或途徑)、反饋以及影響(或功效)構成,各要素因其蘊藏的人文關懷之情而緊密聯系。
首先,就社會傳播的主體和目的而言,辛勤勞作、樂天安命的農人哼唱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同我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的歌謠,傳達了自我實現的知足心意;紅葉題詩的宮娥作為渴慕愛情之心緒的傳播者,“一入深宮里,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的故事大概只能淪為專制時代的悲劇;“三人成虎”后的魏王作為有心人風傳謠言的接受者,蒙昧無察而失去股肱之力也是自然……再平常的社會傳播行為也有目的(這種目的是社會性的,而非個人性的,這也是哈貝馬斯所在乎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互動與交流,而社會傳播則是表情達意、自我滿足的重要方式。平凡如顧念家長里短,崇高如常思兼濟天下,淳良如護持禮法常情,俗惡如用盡心機權謀等,為著不同的目的,總歸得進行社會傳播。另外,現實社會也存在很多特殊的傳播現象,即傳播者無意傳達信息,而接受者卻能根據自己的長期經驗或專業知識來捕獲有用的信息(如,間諜傳信),但這樣一來,傳播就無法得到反饋,傳播的互動性和社會性就喪失了。
其次,社會傳播一定要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和具象的實質內容,即共享的意義系統。從最初的語言(包括肢體語言、口頭語言等)和標志物(如,結繩、記號、烽火或狼煙等)到成熟的文字(如,楔形文字、甲骨文等),隨著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累和抽象智慧的增長,能夠被大多數群體成員共同理解的意義系統也漸趨形成了。意義系統是長期的集體實踐和認同的結果,它是許多人共有的[3],以此為基礎,群體內部成員運用約定俗成的各種符號(意義系統的表現形式)來理解彼此的情意,就緊密關聯、共同關心的生活話題作交流。“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大家都很熟悉了,鐘子期之所以能夠體會俞伯牙的琴韻,在于他們對生活情趣與音樂審美有著相同的理解;稍顯遺憾的是,這共同理解太高雅了,以致其他不具音樂天賦的旁聽者竟無法品味曲中精妙……上述傳播情景雖然不同,但卻說明:傳播活動是以共享的意義系統作為基礎和內容的。
再者,社會傳播并非無依無憑,而是需要載體和途徑的。“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等詩句都闡明了社會傳播的載體或途徑。總結說來,在人類歷史上,信息媒介和信息傳播活動經歷了五次巨大的變革——語言的誕生、文字的誕生、印刷術的誕生、電磁波的應用、計算機技術的應用,每一次變革都推動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加速了人類文明的進程,同時也促成了傳播技術的進步。正如媒介理論家、思想家麥克盧漢所言,“媒介即人的延伸”[4]。我們通常“將身體體驗為一個異己的環境,以區別于自己的思維、心靈或精神”[5],這種身心對立觀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但在現實的身體實踐過程中,身體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絕對不存在離心之身或離身之心。不論是何種傳播途徑,都是以身體或身體的延伸作為載體的,都是人的意識與肢體相互交融后外顯化的表現,只不過就是交流工具而已。至于社會傳播的現代化方式——紙張通訊、有線通訊、無線通訊、數字通訊,任其科技含量多高,都逃不開身體的范疇。數字通訊,以互聯網為代表,傳播參與者在虛擬社區(如,Micro-blog、BBS、Tips bar等)中進行匿名交往,將互聯網傳媒代替了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種感覺官能,以求展現自我,了解他者,滿足社會性交往的需要。
還有,大多數傳播是雙向的,也就是說,受眾隨時可能對接受的信息進行反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離別之際,汪倫以踏步唱歌的方式向李白傳達濃重的離別傷情,而李白也賦詩以贈汪倫,向他表達誠摯的謝意,這算是對汪倫情誼最詩意的反饋了。從理論上來說,各類傳播形態(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在進行過程中都越來越注重受眾和傳播者之間的信息互動,受眾和傳播者的角色可以互換,受眾絕非被動的信息接受者,作為生活世界中的一個主體,他/她也在向上一級的傳播者施加影響。換言之,有反饋的傳播行動,消弭了科技理性所造成的人情疏離和人性淡漠,在人與人之間架起了理解的橋梁——這也正是溝通行動理論欲破解的社會理性化的困境。
最后,筆者將談一談社會傳播的影響和功效。“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楊貴妃親嘗了新鮮的蜀地荔枝,卻累斃了許多差官和驛馬。“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目為飛奴。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系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飛鴿傳書,方便極了。在重視禮法王道的古代,社會傳播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子也說了:“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見他早就意識到社會傳播具有啟發鼓舞人心的感染功能、考察社會現實的認識功能、受者互相感化和提高的教育功能、批評不良政治的諷喻功能。這種對傳播的社會功能的認識,是有些理想化了,但卻是“出于廣大受眾對傳播之巨大社會影響力的真實體驗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千百年來一脈相承的憂國憂民情懷”[6]。須注意的是,社會傳播也有一些娛樂功能和負功能。比如,媒體文化研究者、批評家尼爾·波茲曼就以“娛樂至死”的警語來表示他對傳播(尤其是電視)的娛樂功能的擔憂,因為廣泛的娛樂化表達方式將可能使得“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7]。
三、社會傳播的古今對照
傳播本就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傳播要實現其價值,就應該積極關照民眾的人文境況——關照人們通過怎樣的方式展開溝通行動,怎樣生活,怎樣思考,怎樣感受,怎樣行動。然而,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遷,社會傳播也因之呈現出不同的圖景。
(一)古代社會傳播的特征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比當今的社會傳播,可以總結出古代社會傳播有如下特征:
1.古代的社會傳播尤其注重傳播主體之間的交流與溝通,體現了溝通行動特有的主體間性。在消費主義文化大行其道的當今,社會傳播卻淪為滿足無意識的消費欲望的場域,溝通幾成奢望。
2.古代社會傳播涉及的范圍較狹窄,但由于十分關注可以眼見耳聞的日常事件,體現了生活化的特色。但現代技術擴大了傳播范圍后,傳播的間接性也隨之增強,使得傳播內容有可能失真和變質,甚至摻雜了宏大崇高卻遠離現實的各種“主義”,喪失了生活的原汁原味。
3.古代的社會傳播內容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達成共識,反映了社會的統一性。在當今社會,個體越發地原子化,人們已經很難就某一傳播內容形成一致的意見了,這當然是個人思想自由的體現,但在越來越缺乏共識的情況下,“社會何以可能”就值得我們深思了。
4.古代社會傳播的媒介較單一,多是口耳相傳,因此能夠直接地傳達人的情感體驗和精神狀態。而現代傳媒技術大大地增加了身體以外傳播媒介出彩的機會,我們想要通過身體官能的情感共鳴來真切地領會報刊、電視、互聯網中各類傳播主體的感受已是很難了。
5.古代社會傳播的影響較為平和,不容易虛妄地擴大那些公開事件的影響力。而現在,我們只要一翻閱報紙,打開電視,或是啟動電腦,就很可能因為“新聞巨獸”“新聞漫天”而引發過度的憂慮惶恐加空虛和過剩的同情心泛濫抑或無名火起,海量的信息已經使我們無所適從了,“復制”和“虛夸”在社會傳播過程中造成了難以預料的巨大影響。
總之,古代的社會傳播滿載著美妙象征,而現代的社會傳播則略顯蒼白無力了。
(二)當今社會傳播的反思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比對了古今的社會傳播后,我們也應該對當今的社會傳播進行一些反思。
之所以將傳播看作溝通行動,是因為傳播的各要素在現代條件下漸趨分崩離析,且溝通理念無法將之重新整合。
傳播行動要得以進行,傳播者尤其是新聞界工作者必須意識到并積極履行自身的公共責任,這是就傳播的規范和責任而言的。大眾傳播“理應是社會公器,……是公共輿論的園地”[8],而先進的現代傳媒技術也為信息的大批量復制和廣泛擴散提供了技術支持——這樣看來,大眾傳播應該能夠向廣大受眾傳遞正能量了,但真實情況卻不容樂觀。一些向來頗受信賴的“專家教授”在幕后受雇于小眾利益集團,借指導的名義向民眾散播虛假訊息;很多電視媒體將大量時間花費在形象工程、娛樂作秀、明星出鏡、大腕緋聞上,卻很少正面關注民眾現實的日常生活;個別公共知識分子對社會弊病或沉默寡言,明哲保身,蠅營狗茍,事不關己,不能發出正義的聲音;還有一部分青少年將政治時事、娛樂快訊、電子書籍、網絡游戲(甚至色情視圖)的消費當作精神食糧,卻對當下的、眼前的、自身的重要事情不大關心……傳播的主體、內容、載體、效果等各要素都或多或少地變質了,無法統一于人文精神,只有引入溝通理念,重視和踐行人文精神,才能還傳播以公器的本色。
近年來,逐漸變質的傳播活動讓大眾不知不覺地共同經歷著形式合理而實質不合理的日常生活。
以手機的普及和使用為例,手機所引發的“拇指運動”之流行,雖然為大家的溝通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但卻因為手機通信使很多用戶潛移默化地接受了“形式重于內容”的溝通觀念,彼此之間的關系并未增強,情感卷入的程度、情感交流的頻率甚至有所下降,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似乎難以跨越,真實也變得模糊不清;“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的距離,而是我就坐在你身邊,你卻在玩手機”,這句網絡流傳的調侃之言正好形容了“拇指運動”導致的親情疏冷之悲劇。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傳播技術使我們日常生活的形式變得舒適、閑逸、便利,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其變得庸俗、冷漠和無意義。反之,順暢、有效的溝通行動才能維持傳播的持續性,也才能達成相互理解。
歷史變遷不曾停息,古詩詞中充滿詩意的生活無法讓現代人親身經歷,但在常人的視角下,但愿我們平凡人能夠索引性地表達平凡事的不平凡之生命意義,社會傳播的合理價值就在這里——最真實的就是再平常不過的瑣碎生活,終極意義的追尋和體悟就藏在生活里。重拾社會傳播的初衷,我們須關注經驗世界,回歸日常生活,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與人交流,這種人文關照要比僅僅探討干澀的傳播學理論或是沉浸在轟動刺激的新聞里有意義多了!
參考文獻:
[1] (美)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何道寬譯.傳播學概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 李昕澤.傳播學視域下的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D].長春:吉林大學,2012.
[3] (法)涂爾干著.汲喆,付德根,渠東譯.亂倫禁忌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加)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5] 趙方杜.身體社會學:理解當代社會的新視閾[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27-35.
[6] 胡興榮.大眾傳播的功能與社會發展[N].中國新聞觀察中心,2009-10-16 .
[7] (美)尼爾·波茲曼著.章艷譯.娛樂至死[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8] 何滿子.聊記舊事代感慨[J].新聞記者,2000(5):44.
[責任編輯: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