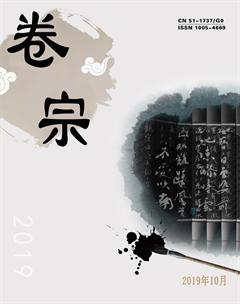論書(shū)法文化的現(xiàn)代演變
摘 要:中國(guó)書(shū)法在文字的書(shū)寫(xiě)與運(yùn)用過(guò)程中逐步形成,與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歷史及社會(huì)的變遷密切相關(guān)。從書(shū)法文化發(fā)展的歷史沿革中,分析書(shū)法的現(xiàn)代性與媒介傳播的影響,探析書(shū)法在現(xiàn)代性的影響下自身的演進(jìn)變化。
關(guān)鍵詞:書(shū)法文化;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演變
以傳播學(xué)的角度,書(shū)法的產(chǎn)生可追溯至文字傳播時(shí)代,中國(guó)書(shū)法在文字的書(shū)寫(xiě)與運(yùn)用過(guò)程中逐步形成,而文字的產(chǎn)生則與人類(lèi)社會(huì)發(fā)展歷史密切相關(guān),因此書(shū)法與社會(huì)的變遷息息相關(guān)。在漫長(zhǎng)的漢字演化過(guò)程中,中國(guó)書(shū)法文化逐漸作為一種獨(dú)特的文化而存在,在現(xiàn)代性的影響下加速著自身的演進(jìn)變化。
1 書(shū)法文化的內(nèi)涵及歷史沿革
1.1 書(shū)法文化的內(nèi)涵
有學(xué)者將書(shū)法定義為:以漢字為基礎(chǔ)、用毛筆書(shū)寫(xiě)的、具有四維特征的抽象符號(hào)藝術(shù),它體現(xiàn)了萬(wàn)事萬(wàn)物的“對(duì)立統(tǒng)一”這個(gè)基本規(guī)律,又反映了人作為主體的精神、氣質(zhì)、學(xué)識(shí)和修養(yǎng)。[1]此定義反映了書(shū)法的兩個(gè)基本屬性:書(shū)寫(xiě)屬性和文化符號(hào)屬性。書(shū)法可以作為一種書(shū)寫(xiě)工具,通過(guò)象形符號(hào)傳遞信息,也可以作為一種造型藝術(shù)來(lái)表達(dá)主體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旨趣。
學(xué)術(shù)界對(duì)于“文化”的定義歷來(lái)頗有爭(zhēng)議,這里借用“人類(lèi)學(xué)之父”英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泰勒的觀點(diǎn):文化“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總體,包括知識(shí)、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風(fēng)俗,以及人類(lèi)在社會(huì)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xí)慣”[2]。這一定義將微觀與宏觀相結(jié)合,也恰與書(shū)法的雙重屬性相契合。因此書(shū)法文化也可以從兩個(gè)層面進(jìn)行理解,一是在人類(lèi)的社會(huì)生活中,一切與書(shū)法相關(guān)的能力與習(xí)慣,二是通過(guò)書(shū)法形式而獲得的知識(shí)、藝術(shù)、道德和風(fēng)俗等。
1.2 書(shū)法文化的歷史沿革
書(shū)法作為文字傳播工具,從西周開(kāi)始履行傳播功能,書(shū)法字體多以古文與篆字為主,通常用于特定的儀式意義或者承載信息的記載功能,傳播范圍多局限于士大夫與其門(mén)客;秦漢時(shí)期,實(shí)行“書(shū)同文”,書(shū)法作為一種書(shū)寫(xiě)藝術(shù)的五種典型字體篆、隸、行、楷、草,初具形式并各有發(fā)展,書(shū)法開(kāi)始同時(shí)具備傳播符號(hào)與傳播文化信息的功能;及至魏晉時(shí)期,王羲之博采眾長(zhǎng),將人生感悟融于筆法之間,而非單純欣賞字體字型,并且開(kāi)創(chuàng)了書(shū)法的傳授教學(xué),形成了文人雅士集會(huì)分享書(shū)法賞析之風(fēng),開(kāi)始在小范圍群體中文化內(nèi)容的傳播;唐宋時(shí)期書(shū)法中法度盛行,書(shū)體的變化、規(guī)范帶有書(shū)法家強(qiáng)烈的個(gè)人風(fēng)格和思想志趣,書(shū)法家與文學(xué)家常常共生,民間書(shū)法已經(jīng)較為廣泛,且拓本的流傳使得書(shū)法傳播已經(jīng)涉足到印刷工具的傳播;明清時(shí)期,書(shū)法逐步擺脫以“官文化為主流的文化氛圍”,互相欣賞的小范圍人際傳播逐漸轉(zhuǎn)為以文本為基礎(chǔ)的傳播。
縱觀近兩千年書(shū)法的演進(jìn)歷史,作為傳播信息的文字媒介,規(guī)范性和實(shí)用性逐漸增強(qiáng)。作為一種傳統(tǒng)文化,近兩千年積累的、蘊(yùn)含在書(shū)法文化中的隱含的規(guī)則、理念、秩序和包含的信仰,融入了大多數(shù)中國(guó)人的精神氣質(zhì)中,成為我們心理層面和意識(shí)層面的一部分。[2]
2 現(xiàn)代性與媒介傳播
2.1 現(xiàn)代性帶來(lái)的社會(huì)變化
所謂現(xiàn)代性,根據(jù)吉登斯最早的一個(gè)定義是緣起于17世紀(jì)歐洲的社會(huì)生活或組織結(jié)構(gòu)模式,這一模式在世界范圍擴(kuò)散開(kāi)來(lái),并且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現(xiàn)代性從本質(zhì)上來(lái)說(shuō)對(duì)社會(huì)變遷產(chǎn)生重大影響。
1)現(xiàn)代性的“去傳統(tǒng)”的問(wèn)題。就是人類(lèi)社會(huì)從傳統(tǒng)社會(huì)發(fā)展到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西方社會(huì)經(jīng)歷了重大社會(huì)變革,宗教和傳統(tǒng)的影響不斷削弱,知識(shí)和科技得到了推崇和擴(kuò)散,工業(yè)化革命興起,市場(chǎng)機(jī)制被廣泛推行,大眾傳播媒介出現(xiàn),且其在社會(huì)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2)現(xiàn)代性的“西方化問(wèn)題”。隨著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即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擴(kuò)散,世界其他國(guó)家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廣泛影響,存在被“西方化”甚至被“美國(guó)化”這樣一個(gè)過(guò)程和現(xiàn)實(shí)。
2.2 現(xiàn)代性與媒介傳播
1)媒介傳播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位置日益重要。媒介傳播為現(xiàn)代性所建構(gòu),同時(shí)建構(gòu)了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性與媒介存在著相伴相生的關(guān)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大眾傳播媒介不斷興起并對(duì)社會(huì)生活進(jìn)行廣泛滲透。新媒體和微觀的信息傳播過(guò)程的興盛,互聯(lián)網(wǎng)等新媒體重新定義了傳播方式和人類(lèi)社會(huì)。2)在傳統(tǒng)社會(huì)向現(xiàn)代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傳統(tǒng)也變成媒介化了的傳統(tǒng),由于新的媒介的介入,許多傳統(tǒng)文化被保留下來(lái),但是,新的媒介也使部分文化傳統(tǒng)變得更加脆弱,這在中國(guó)書(shū)法文化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3 現(xiàn)代性下的書(shū)法文化演變
書(shū)法的現(xiàn)代生存狀態(tài)與發(fā)展變化歸根結(jié)底是由中國(guó)社會(huì)的變遷所決定的,20世紀(jì)初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中國(guó)書(shū)法在現(xiàn)代性影響下加速著自身的演進(jìn)變化。
3.1 書(shū)法的書(shū)寫(xiě)屬性與文化符號(hào)屬性的分離
20世紀(jì)初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因?yàn)殇摴P的效率和便攜性,國(guó)人開(kāi)始大規(guī)模換筆,鋼筆取代毛筆成為近一個(gè)世紀(jì)的主要書(shū)寫(xiě)工具,也使得書(shū)寫(xiě)的“工具性”屬性更加突出。然而書(shū)法是凝結(jié)著書(shū)寫(xiě)者的思想、情感和想象,與人的精神氣質(zhì)緊密關(guān)聯(lián),但是,鋼筆的普及使得人們更注重為了實(shí)用而書(shū)寫(xiě),書(shū)法的書(shū)寫(xiě)屬性與文化符號(hào)屬性漸漸分離。隨著社會(huì)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電腦的出現(xiàn)讓人們喪失了手寫(xiě)的日常性和普遍性。執(zhí)筆的機(jī)會(huì)越來(lái)越少,書(shū)法與日常書(shū)寫(xiě)斷裂,書(shū)法成為了純粹的藝術(shù),文字所體現(xiàn)的精神氣質(zhì)也逐漸模糊。
3.2 新媒介助推書(shū)法文化符號(hào)屬性的顯現(xiàn)
隨著大眾傳播時(shí)代的到來(lái),大批量的復(fù)制印刷使得碑帖的生產(chǎn)臨摹更加便捷,人們的感官得到延伸,書(shū)法文化的傳播也開(kāi)始借助了其他媒介的助力,雖然書(shū)法的書(shū)寫(xiě)工具屬性與文化屬性割裂,執(zhí)筆寫(xiě)字已非常態(tài),但是在大眾傳播時(shí)代下,書(shū)法不再是特定人群“書(shū)齋式”的人際和群體傳播,同樣擁有可視化特性的電視媒介使得書(shū)法藝術(shù)從文人書(shū)齋走向了大眾生活,大眾在對(duì)書(shū)法文化的感知中,文化符號(hào)屬性處于主導(dǎo)位置,書(shū)法文化也更多的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內(nèi)涵、共同精神氣質(zhì)的象征符號(hào)而被關(guān)注,呈現(xiàn)出儀式化的意義,書(shū)法的文化符號(hào)屬性愈加突出。
3.3 書(shū)法文化傳播出現(xiàn)兩極化差異
從傳播主客體的角度看,一方面,人類(lèi)的傳播手段更加豐富,多樣化的媒介讓書(shū)法文化的傳播擁有更多的渠道,大眾對(duì)書(shū)法文化的接近權(quán)不斷增長(zhǎng),提供了更多的書(shū)法文化傳播的受眾群體。但另一方面,由于知識(shí)鴻溝的存在,通過(guò)新媒體方式接受書(shū)法文化傳播的大多為經(jīng)濟(jì)水平較高、受過(guò)一定教育的中青年群體,而對(duì)書(shū)法有較高造詣的書(shū)法家往往因?yàn)槟挲g和傳授習(xí)慣的原因,并不習(xí)慣使用新媒體的方式完成書(shū)法文化的傳播,這就造成書(shū)法文化傳播兩極化的差異。
3.4 書(shū)法文化的傳播完成了由實(shí)物到數(shù)字符碼的轉(zhuǎn)變
從傳播內(nèi)容來(lái)看,由于對(duì)數(shù)字技術(shù)的借助,書(shū)法文化的傳播也完成了由實(shí)物到數(shù)字符碼的轉(zhuǎn)變,大量書(shū)法藝術(shù)通過(guò)現(xiàn)代手段進(jìn)行數(shù)字化展示和傳播。對(duì)于書(shū)法本身而言,諸如書(shū)法工具、觀念等大量的現(xiàn)代元素注入其中。數(shù)字化技術(shù)的運(yùn)用可以替代了紙張書(shū)寫(xiě),隨著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的改變,運(yùn)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替代了紙張書(shū)寫(xiě)成為可能,數(shù)字書(shū)法作品創(chuàng)作也應(yīng)運(yùn)而生,書(shū)法文化在數(shù)字化的背景下從創(chuàng)作到傳播被賦予新的形態(tài)與使命。
參考文獻(xiàn)
[1]周斌,馬琳編著.中國(guó)書(shū)法簡(jiǎn)史.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緒言.
[2]丁蘇安.愛(ài)德華·伯內(nèi)特·泰勒列傳[J].民族論壇,2012(12):11-21.
作者簡(jiǎn)介
李萍(1965-),女,山東乳山人,中共山東省煙臺(tái)市委黨校圖書(shū)館副研究館員,現(xiàn)主要從事文化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