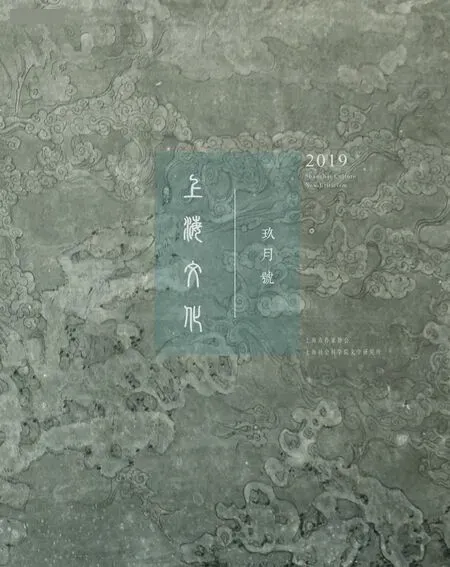波斯物種筆記
Ag
德黑蘭郊外
櫻 桃
在去向拉瓦桑的路上,司機錯過了那個不起眼的村口。
它漸漸消失在飛馳而過的后視鏡中,沒人能第一眼就尋到。一個已故電影導演的墓地就在這公路邊的某個山村高地上,根據谷歌地圖的顯示,那個墓地的紅色圖釘符號剛與我們移動著的藍點重合,此刻又在迅速遠離。我們在前方的U型指示牌處掉頭折回,減慢了車速,生怕再次錯過它。
那是個狹小的入口。沿著一條陡峭的土路,我們正接近目的地。從衛星圖上來看,墓地的精確位置應在鄉道的某個分叉路口。但我們的汽車來來回回繞了幾圈,依然沒有找見什么墓地。只有土路上的揚塵、金黃色的胡桃林和一些零落的住宅。
事實是,我們已經經過它三次,但我們渾然不知。來自德黑蘭的年邁老司機被搞糊涂了,只能以極慢的速度讓汽車徘徊,等到偶爾有人經過時,就搖下車窗問路,你知道,就像《櫻桃的滋味》里那樣,搖下車窗,輕聲地、禮貌地重復詢問同一個問題,那些本地人,非常熱情努力地為我們指路。有的說哦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墓啊,您后退,對退回去,當您看到第一個向上的坡口時,右拐,就到了,記住,右拐,就在那兒;有的說不不,不是這里,在那條您剛經過的路的左邊,左邊再上面一點點,就是了。那個本地老頭彎著腰,做了一個微微揚起的手勢,態度非常肯定。這些當然都是我揣測的詞句,從他們的肢體與語調上,不過八九不離十,有一件事兒我已經開始習慣了,伊朗人用他們溫婉的法爾西語問路,起效過程始終是漫長的,這禮儀中有著一種接近羞愧的東西,不僅是出于道德上的含蓄,還有某種更古老的孤僻情緒在其中,就像那些獨自長在荒漠中的櫻桃樹。
我們最終錨定一個奇怪的坡口,圍著它不停打轉,像瞎了一樣,最后只能決定停車。熄火下車后,我才發現這里安靜極了,風在胡桃樹樹葉上拍撫出一陣陣清晰的節奏。我漫無目的地走了幾步后,看見這個狹窄的岔路夾角上立著一扇黑色的小鐵門。墓地。就是這里,鐵門里面藏著一片從外面經過時絕不會意料到的三角形花園草坡。我們小心翼翼地跨過許多更老的墓,閱讀并尋找著。它們和鋪在地面上的石磚一樣低,有些寫滿了文字,有些印刻著肖像,我看到一塊墓碑上的遺像畫似乎是一家四口,從死亡的年份來看,應該是兩伊戰爭時期。阿巴斯的墓在幾乎盡頭處,那是一塊與其他墓碑相比過于簡單的灰色大理石,碑面一角上刻著一棵櫻桃樹剪影和阿巴斯的簽名字跡。墓碑旁,一棵年幼的櫻桃樹挨著,只有小灌木那么高。基亞羅斯塔米是這座墓園最新的一位逝者,在他的墓碑之后,是一片林間空地,我從這片空地的草坡上走下來又走上去,消磨了一些時間。臨走時,司機在墓前單腿跪地,垂下頭,默念了一些話語。
“基亞羅斯塔米躺在兩棵櫻桃樹下,一棵在石間銘刻,一棵在泥里生長,真正的基亞羅斯塔米屬于哪兒?”
在那一晚干燥難耐的熱夢中,我將這個疑問抄寫在了一張皺巴巴的、印滿了波斯數字和法爾西語的晚餐賬單上。
基亞羅斯塔米躺在兩棵櫻桃樹下,一棵在石間銘刻,一棵在泥里生長
恰克恰克山
金 瓜
司機幾乎不會說英語,這也許是他寡言的原因之一。方向盤緩慢柔和地轉動,輪胎碾過塵土覆蓋的柏油路發出沙沙響,黃色的夯土建筑和難以辨別的土堆在車窗玻璃上移動,他身上的灰色格子襯衫由于炎熱的天氣,一部分貼在肩膀和胸口上,但肘部的袖口和放在褲子外面的下擺,在他纖瘦的身體上顯得依舊有些寬大。
出了亞茲德城,是一條筆直的公路,沒開出多久,他忽然開始放慢車速,我們正漸漸靠近一輛載滿金瓜的卡車,我疑惑地望向他,發現他有著一雙孩童般的眼睛。
他將車停靠在路邊,示意讓我等一會兒。
公路上汽車經過的風聲蓋住了他本就輕生輕氣的討價還價,很快,他就抱著一只金瓜鉆回車里,將它放到座位下面。
公路兩旁的城鎮漸漸消失了,進入了一片荒漠,空氣變得更焦灼、更炙熱,周圍幾乎沒有任何建筑物,只有零星的沙堆和山包從地面上微微隆起。顛簸了一陣之后,他指著前方的一座其貌不揚的矮山說:
“看,恰克恰克。”
香 果
我們當中有誰是拜火教徒嗎?我或者他,一個來自中國的旅客,一個伊朗南部的出租車司機,誰會是隱藏的拜火教徒?我對此一點都不確定。他熄火后用簡單的英語對我說,我跟你一起去。我們一起下了車,走出幾步后,我發現他懷里抱著那只金瓜。
也許今天我們走運,也許不,他邊走邊回頭說。旅行指南上提醒,在訪問拜火教圣山恰克恰克時,神廟需要大祭司開門才能進入,然而并沒有人事先知道大祭司在或不在。我們冒昧地前來,似乎只是為了觀光荒漠的一毛不拔,以及碰碰運氣。我轉身回望山腳,那輛破敗不堪的銀色桑塔納停在沙地上,像一枚錢幣在閃閃發光。
上山的沿路有一些我不認得名的沙漠植物稀疏地生長著。司機停下來,摘了一顆那植物上的果子,然后面朝我把果子放在耳朵旁搖了搖,又放在鼻尖聞了聞,然后把果子給我,示意我也這樣做。
我把這顆圓潤的、表面不規則凹凸的褐色小果子放在耳朵旁搖了搖。嚓-嚓-嚓,內部中空的果核發出一陣輕微的聲響,然后我又像他那樣把它放在鼻尖聞了聞,是一股類似于尤加利植物的濃烈香味。他自己又摘了一顆,捏在手里,一路上時不時聞它幾下,然后扔了,再摘一顆,不久后又扔了。我則鄭重地把果子揣進衣服口袋,就像得到了一件無名的傳世珍品。
過了半山腰后,他帶我來到了一間山崖小屋。門開著,陽光灑進屋里,照亮了一塊紅黑花紋的舊地毯。他回過頭神采奕奕地說,我們可真走運啊。
蝴 蝶
從里屋走出的老頭就是拜火教神廟的大祭司,一張圓臉蛋,一只紅通通的圓鼻子。司機和大祭司輕輕擁抱了一下,并不親昵,司機顯示出一種靦腆與恭敬。大祭司邀請我們坐在那張地毯上,端來了紅茶。我環顧這個房間,它讓我想起托尼·加特列夫電影里的那些由舊木框、相片和織物搭建成的簡陋小屋。我和司機面對面坐著,他微笑著,又不知說什么,他的面容相比南部典型的雅利安長相,顯得過于黝黑而蒼老,但其中竟有些不同尋常的東西。一種優雅?或許是某種與靜默有關的東西。
大祭司又端來一個銅盤,是一盤切好的瓜,就是司機在路上買的那只,瓜瓤散發著晶瑩的白金色。大祭司說,今天很熱,你們需要喝更多的茶。相比祭司的身份,他更像是一名守門人。
待太陽稍傾斜一點后,大祭司帶我們來到一個山洞,打開了洞口的一扇金屬大門,我們脫下鞋,赤著腳進去。腳底的石頭被山泉水沖刷得滑溜、冰涼,那山泉水從洞口的崖間裂縫間滴下,落在地上時,就發出“恰克、恰克”的聲音。
山洞內部就是神廟,這里沒有太多被建造的痕跡,一種天然的喀斯特地貌的空間,唯一添置的人工物是一個花瓣形的火壇和一支三頭燭臺。大祭司點起了火壇,我們則靠著巖壁坐著,我抬頭看到巖洞頂部畫著的阿胡拉馬茲達的臉,我懷疑我曾在夢里見過這樣的屋頂。后來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在山洞里踱步,巖壁上裸露著一些洞口,透過它們,可以看見恰克恰克山形成的不同形狀。司機和大祭司走過來,我們站在一起,往同一個洞口外張望著。
一只蝴蝶從這個洞口飛進來,黑色的身體上有一些漂亮的白色斑紋。它飛過我頭頂時,我下意識地躲了一下。大祭司笑了,他伸出手,一下就捏住了蝴蝶的翅膀。他說,別害怕,然后他將那只蝴蝶輕輕地放了在我的肩膀上。蝴蝶動了幾下翅膀,便靜止了下來。我能感覺到它六只小腳微乎其微的重量,我斜目而視自己的右肩,它似乎也正瞧著我。大祭司說,和它一起待一會兒。我們三個人就望著這只蝴蝶,待著,然后又不約而同開始發笑,但我們笑得非常輕,輕得幾乎聽不見,也許只有那只蝴蝶才能感覺我身體的微弱抖動。
大約過了兩分鐘后,它扇動了幾下翅膀,離開了我的肩膀,在神廟里兜了一圈,從另一個洞口飛走了。
大祭司說,和它一起待一會兒。我們三個人就望著這只蝴蝶,待著,然后又不約而同開始發笑
阿拉斯河
石 榴
在離邊境還有三十公里的地方,出現了一座荒原。阿里決定在這里停車休息,他絮絮叨叨地打開后備箱車蓋,擺出幾只玻璃茶杯,檢查了一下熱水瓶里的水是否還冒著煙。阿里的妻子則不緊不慢地挽起袖子和袍子,蹲在水渠邊,摘了一把薄荷草。紅茶泡開后,阿里掰碎了幾片薄荷草扔進杯子里。不遠處又出現了一片金黃色的胡桃林,身后是荒原中一座廢棄的屋宅。我們幾個人朝著不同方向站著,牙齒和嘴唇間都發出了呼呼的吸茶聲。兩杯無與倫比的紅茶下肚后,我們又繼續上路。那是一條漫長的向北駛去的公路,盡頭那片海市蜃樓般的山石屏障就是伊朗的邊境。十幾分鐘后,阿里大把轉動方向盤,朝右拐上了一條窄路。
對面就是阿塞拜疆,阿里說完這句后,哼起了一些斷斷續續的曲調,唱的不再是法爾西語,而是土耳其語。
耳側傳來了潺潺水聲,阿拉斯河,綿長的邊境河,之前只有在地圖上看見過它細幼蜿蜒的身軀,現在它是全息的了。水流聲吸引著我們看向對岸。
阿塞拜疆堡壘狀的山體拔地而起,在它的腳下,有一些蒙著同一種灰土色的車站建筑物,狹長、整齊,遠距離下的窗格呈細密的古舊活頁孔排列。很多年前,列車會穿過這些廢棄的火車站,再穿過前方的亞美尼亞,一直通向寒冷的莫斯科。
伊朗亞美尼亞的諾杜茲口岸前停著一些裝卸貨物的卡車,在等待的閑暇時刻,卡車司機們斜靠在車門上,看著新駛近的車,打量著下車的人。阿里的妻子整了整袍子,給了我一個深情的擁抱,隨后便鉆進了車子。剛告別完,我又被阿里叫住,一個陌生的卡車司機跟了過來,他塞給了我一只石榴,阿里說,這位先生說他們這里產全世界最好的石榴,希望你能品嘗。
進入亞美尼亞關口的通道是一座長橋,橋兩邊的護欄被漆上了不同的顏色,阿拉斯河從橋下流過,它比先前從車上眺望時顯得更為豐沛寬闊了。河水在邊境區的中央沖擊出了一塊茂密的綠洲島,很難看出它是否和兩岸哪一邊有著明確的接壤。
土地漂浮著,在公開的中間地帶,沒有哪兒被誰屬于。
手上的這只石榴,忽然就變得像寶石一樣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