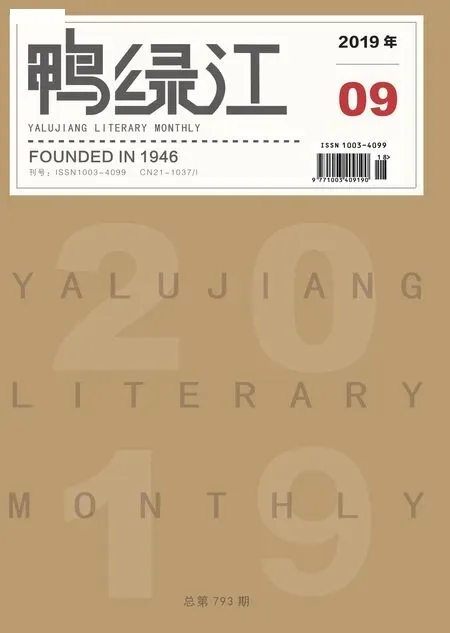我在深圳當醫生
冰 凌
哭泣的嬰兒
2006年2月9日清晨6點左右,一陣刺耳的電話鈴聲響起。我打了一個激靈,從睡夢中醒來。我習慣性地一把抓起電話。“王醫生,我是導診臺。剛才派出所緊急來電,讓新生兒科醫生出診。”我立即穿好衣服飛跑出宿舍。
天剛剛露出魚肚白,我隨救護車來到離醫院不遠的一座居民區樓前。這時樓的門前己圍滿了看熱鬧的人。正在向樓上觀望著,議論著。只見一位年輕警察懷里抱著一個僅僅包著單薄的床單的嬰兒從大門走出來。他見我身穿白大褂,知道是醫生來了便對我說:“今晨接到報警,說在六樓的平臺上發現了棄嬰。我們便趕來了。”春節剛過,雖然是深圳,天氣仍然很涼。新生兒從母體子宮內三十六度,出生后下降到十五六度。這是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我急忙用帶來的小棉被將嬰兒包裹好保暖。這是個男嬰,體重約四公斤。胖嘟嘟的小臉凍得有些發紫,全身及手腳冰涼。臍帶留了很長,尚未處理。心肺聽診無異常。看來除了寒冷引起的未梢循環不好外,其余均正常。我松了一口氣。
救護車風馳電掣般一路嗚著刺耳的笛聲奔向龍崗區中心醫院。后面的警車緊隨其后,也響著震耳的警笛。路人見狀紛紛讓路。到了醫院大門口,因為還未到上班時間,大廳內空空如也。我抱著嬰兒一邊跑一邊喊人。一名值班護士迎上來。我簡單地交待了病情,便囑咐她:“快些抱孩子去產房,處理臍帶,注射破傷風血清,送保溫箱保溫,找兒科醫生。”她一邊答應一邊接過孩子向產房跑去。隨來的警察辦了手續,我也在上面簽了字。因為這個嬰兒屬于三無人員必須要送到指定的醫療機構才可處理。后來聽警察們說事發后整個樓都搜了一遍,也沒有發現產婦。看來這個樓不是案發第一現場。說不定是這個產婦的親戚或者朋友將孩子抱來這座樓,然后報的案。
兩個月后又一起棄嬰事件讓我驚恐不已。這是一個血腥的場面,只見垃圾桶旁有一個全身裸露的女嬰,呼吸心跳全無,有人看到是從樓上拋下的。這時警察己用警戒帶將現場圍住。有一位警察正在詢問一名五十多歲的清潔工阿姨。原來這位阿姨正在倒垃圾時,突然發現了桶旁有一個赤裸裸的死嬰,她驚恐地大叫一聲,不知該怎么辦。冷靜下來后她知道要保護好現場,所以她站在那里不讓任何人靠近,同時用顫抖的聲音打了110。
這次警察迅速包圍了整座樓,不許任何人出入。約十五分鐘后便在四樓搜出了一位產婦。我緊隨其后。只見產婦的床上滿是血跡,胎盤自動娩出。這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孩,她那蒼白的臉上一雙大大的眼睛流露出怨恨,無奈的神情。讓人即可憐又可恨。救護人員用擔架從四樓將她抬下送到救護車中,覆蓋的床單下身處浸滿了鮮紅的血跡。我沒有接到嬰兒只能護送產婦到我院住院治療。
聽說這位產婦的男朋友知道她懷孕后便再也沒有露面,直到分娩,讓她傷心欲絕。自己又不愿求助家里,怕父母耽心。她恨這個不負責任的男人,她曾經按男朋友說的地址找過,根本就沒這個人,地址是假的。而且電話也換了號碼。當她生下孩子后一想到自已將要獨吞這顆苦果,要獨自撫養嬰兒,便痛不欲生。一沖動,便用此殘忍的舉動來報復那位負心人。我問站在一旁的警官,這種情況應該如何處理。他苦笑了一下說:“不管有多少種理由都不能免以起訴。雖然孩子是她親生的,但法律是無情的。等她身體恢復后是要判刑的。”警察的話說得對,無論如何孩子是無辜的。然而,這場悲劇確真實地發生了……
一年后我在早會交接班時聽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原來頭一天晚上,產科醫生出120時在途中發現,有一個挺著大肚子的產婦站在路旁向他們招手,身邊沒有一個人陪伴。大家很奇怪,便將產婦一并接到我院。當晚順產一名男嬰。原來是個多發畸形兒,頭部異常,嚴重的唇腭裂,不能吸吮。按著產婦提供的電話,我們多次聯系孩子的父親無果。產婦身無分文。可我們是救死扶傷的醫院,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娘倆挨餓啊。于是,醫護人員打飯送水,動員病房產婦捐贈奶粉喂孩子……可是,第二天中午產婦還是扔下寶寶偷偷地溜走了。護士們只有輪番喂孩子整整一周,家屬仍然不露面,無奈只有報案,將孩子送到了福利院。我想他們夫婦是想好了,早知是畸形兒,但還抱有希望。一旦生下真的是畸形兒就準備遺棄到醫院,這是他們計劃好的。他們故意躲起來,所以找不到這對夫婦很正常。可是他們想沒想到,自己的親生骨肉今后該如何面對這個世界?
21世紀初期的深圳,各系統的管理尚處于起步階段,全國的精英及農民工云集深圳。人口數由不到百萬突飛猛進增至千萬以上,年齡在二十歲左右,這是對未來充滿幻想的年齡,是一生中最美麗的年華。有些女孩受夠了那整天枯燥無味的流水線工作,為了找到慰籍,年紀輕輕就找了男朋友。還不知男方的真實底細便草草同居。當她們發現有了身孕后便不知所以,驚慌失措。這些男孩子還沒有做爸爸的思想準備,不想承擔責任就選擇逃之夭夭,而造成了棄嬰現象。經過深圳婦幼系統的全方位管理,取消了開介紹信才能做流產這一規定,棄嬰現象就很少發生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