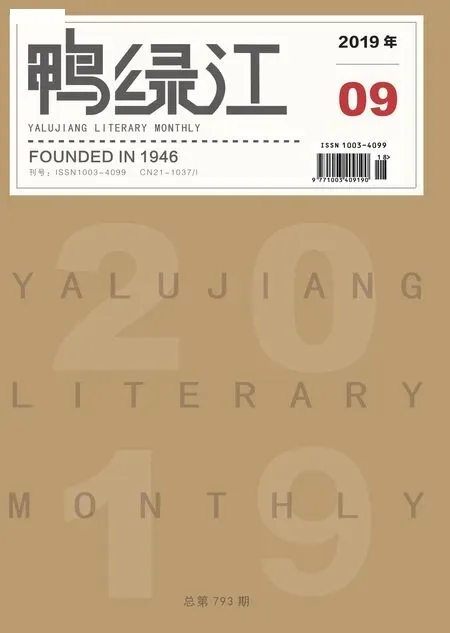讀《音樂人類學的視界》
陳 斌
音樂人類學概念的出現和界定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爭論局面。G·阿德勒最早提出“比較音樂”的定義(1885),但此定義很快就在歷史熒幕上逐漸暗淡,盡管如此,它對于之后的音樂學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孔斯特在1950年提出“民族音樂學”概念,并主張用它來代替“比較音樂學”。1956年起,內特爾將“音樂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當作同義詞混用,“音樂民族學”這個新術語很快被廣泛接受。對其研究范圍,主要出現了“非歐洲”(孔斯特、內特爾等)、“口傳傳播”(拉赫曼、李斯特)和“排我”(瓦克斯曼)三種觀點。20世紀70年代開始,對此概念的爭論才漸漸降溫。
音樂人類學是研究“文化中的音樂”,這一定義來源于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即用文化人類學的基本方法研究音樂事象。《視界》又重在突出其中的“整體觀念”,筆者認為,這種“整體觀念”具有兩層內涵。一是“全球視野”,將民族間的文化看作一個多元而又統一的整體,將音樂現象放到世界文化的語境中去考察,看到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系,從而打破以“非西方”為主的研究局限,打破西方與非西方、“純的”和“混合”、靜態與動態、高文化與低文化、傳統與現代的分野。二層內涵是音樂形態分析與文化背景闡釋的有機結合。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既要充分利用音樂學的研究方法,對音樂本體進行形態學等方面的具體分析,又要利用人類學和文化學的方法,看到音樂本體的廣大外延,做到二者的結合。《視界》中“現代音樂研究”這一部分對后現代音樂文化的種種分析,主要建立在對音樂形態的分析上。在《現代音樂的痛苦》一文中,作者介紹了歐洲音樂技術資源枯竭所導致的種種發展危機,而與此同時,美國的流行音樂卻迅猛發展,“像強大的潮流”,其音樂中即興的旋律,在作者看來是音樂根本屬性的回歸。
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文化變遷研究成為人類學研究的焦點。而對于這樣的課題每個音樂人類學家的視角和觀點各不相同。內特爾的研究習慣地將整個世界的文化整體分為兩個聯系密切的部分——西方與非西方,并著重探討前者對后者的影響以及后者對前者的反應。美國音樂人類學家J.吉爾鮑特雖然也將整個世界的文化分為兩個部分——“世界音樂”與“本土性”,并探討二者關系,但將其與內特爾的劃分相比不難看出,兩者在劃分思維上存在很大差異,內特爾的劃分是縱向的,因此看到的是跨文化的影響機制;而后者明顯是橫向的,看到的則是立體的圈層關系。
人類學(anthropology)從詞源上看,是“anthropos”( 人或與人有關的)和“logys”(學科或研究)的結合,因此是“與人有關的學問”或“研究人的學問”。這樣的學科定位意味著研究和討論它的時候,要樹立“以人為本”的觀念,著力探尋人在改造客觀世界方面的能力。無論是在音樂產生這個問題上,還是在音樂發展的進程中,人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甚至決定音樂作品的命運。
比較音樂學曾一度把“口傳傳統”的音樂納入自己的研究范疇,這一點,拉赫曼強調過,海登和孔斯特討論過,甚至李斯特也說:“音樂民族學是最大范圍涉及非書寫傳統的音樂傳播(1962)”,這種主觀性很強的口傳的音樂在各民族的傳統音樂中占很大比重,越南學者Tran Van Khe在《亞洲傳統音樂的表演性及創造性》一文中,討論了亞洲傳統音樂中表演者和音樂創造者身份重疊的情況,以及兩者之間一步步剝離的現狀,伴隨著即興創造和表演的這種行為習慣的消失。布萊金則直接從生物學和文化進化角度,強調以生物學方法作為文化變遷的研究方法之一,去探尋個體在音樂文化創造中的行為及背后動機,早期音樂人類學理論“不認為個體活動發生的行為或動機的偶然事件和有預期的結果之間有差別,但這對區別不是標榜為音樂家或標榜為音樂家的專門作品或表演的變化是特別重要的”。
中國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建設肇始與20世紀80年代,標志是1980年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研討會的召開。經過幾十年發展,如今各大高校、藝術科研機構里,音樂人類學學科體制已相當龐大,關于它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研究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城市音樂學也應運而生。《視界》涉及面廣,論文選擇恰當,其觀點和方法可以為現在及將來的音樂學研究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