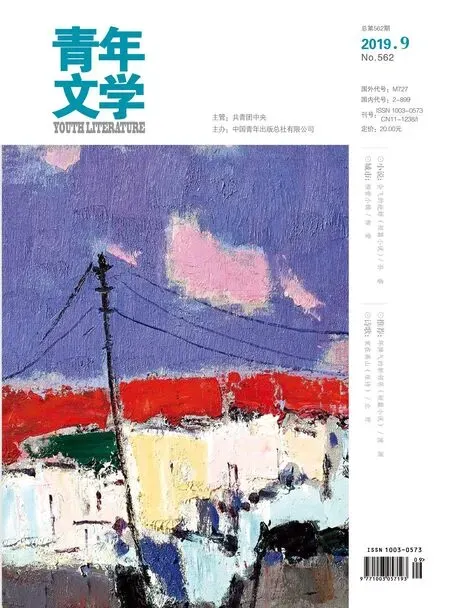馬累的詩
文/馬 累
我的詩歌(之六十一)
燕子在低處飛行,烏鴉
在高處散步。經過了一個
冬天,依然有桐籽落向
地面。那過程也是一個我
叫醒另一個我的過程。
一個自我,在燕子與烏鴉
的中間,密謀一個
幼年的真理。另一個自我
在大地上看一條大河
鋪滿春汛。看春汛中的
天性、人性。
看頓悟,
如輕微而迅疾的電流,
梳理我青絲般的迷亂。
秋天
終于可以更理智地看待
自我的痛苦了。因為
看見了這個時代的痛苦。
在這個秋天,午后短暫的風暴里。
這個時代的人有著共同的
秉性,庸俗而漠然。
這個時代的詩人有著共同的
秉性,傾心于偷窺
和紙上的王冠,忽略了
生活的恥辱。
在秋天,凝重總是晨露般
到來,經久不息。
敏銳總是晨光般轉瞬即逝。
孤傲
整個上午,我努力
保持不動。像祖母貼在老屋
東墻上的剪紙。一層
又一層。四十九公里
之外,黃河正
穿過私人的濃霧。
阻止它發出聲音的,
是萬籟俱寂的命運。
阻止我望遠的,
是現實的瞌睡。
一本永遠也讀不完的書,
其實合上才是真理。
整個秋天,
我們一起用來生病。
用整個時代都拋棄的孤傲。
臘月
我喜歡這個農歷的詞:
臘月。
如同一個詩人喜歡
汨羅江深深的
痛苦和一間草堂的孤傲。
這大雪,
只一袋煙工夫,
來時的腳印就消失不見。
難道通往真理的路
都是絕路?
我站在大堤上,
遠望河心洲一燈如豆。
這么晚了,
不會有人關注這些了。
這農歷的原野多么靜寂。
這臘月的黃河多么孤傲。
當我離開,大雪之上的云層
透著微弱的亮光。
烏鴉之九
總想起多年以前,
大約七八歲的樣子,在故鄉
我喜歡在寧靜的黃昏
鉆進樹林,并總能看見
那么多烏鴉
站在枯枝上拍打翅膀。
那即將消逝的稀粥一樣的晚霞,
映照它們發亮的羽毛。
那些不祥的神,
帶來那么多想象的寓言。
如黃昏烏黑的鴉巢,
密集、壓抑,
注滿我年幼的靈魂。
一直到現在,
那計算的前程,依然覆蓋著
不曾言明的幻象與深邃。
仿若今晚,
月光幽幽,朗照天下
其中包含我的愛恨
與忠誠。
烏鴉之二十
烏鴉三三兩兩地飛回來。
緊接著是暮色。
我向遠處望去,看到的
場景就是:
一大塊黯淡的幕布上,
點綴著不規則的濃黑的點。
像傳說中難得一見的
真理的密碼。
會的,一定會的。
當你佇立在天荒地野中,
一條大河像一條暗黃的綢帶,
維系著星光與大地無限脆弱的關系。
你一定會接收到來自秘密
深處的信息。
關于正確的生活,關于
世界的節律
和悲傷的自我認知。
這夜
這夜,我再讀魯迅。
這夜色之靜美,讓我
重回母親的懷抱,
含著那乳頭,再走一遍
家園,從人之初
性本善開始。
這夜,我的罪與惡,
請你肆意地猜,別留情面。
我微小如當下的
江山與家園,
我膨脹如世人的心。
這夜,我聆聽先生
曠古的哀愁。我注視
黑暗中那一明一滅的煙頭。
痛苦不是最大的敵人,
真理才是,人性
才是。
敘事詩
有一次,我想起小時候,
在暗暗的秋夜曠野,
我將手電筒對著星空
不停地晃動。
那根無限深邃的光柱,
那銀子一樣清冷的光。
不遠處,那深藏著
人生秘密的水洼里,
有更靜的蟲鳴與自由。
還有一次,在深冬的
華北平原,我開車
穿過一個陌生的村莊。
一些人抄著手
走過暮色中寂靜的田埂。
一些人停下來,
哈著白氣。
他們觀察這個世界的
姿勢遠勝于對自身的留戀。
所有樸素的心,
都在不緊不慢地跳著,
背向這個世界的急躁與不安。
“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簡單的理想,如今
還會被幾個傻傻的人
再次傻傻地憶起?
當我目送月光上樹梢,
像我的哀愁,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會突然純凈起來,
像小時候,
像那些卑微,卻
暗暗支撐世界的人。
自我的詩
我曾經妄自揣測過那些
偉大的古人面對命運時的
本真與無邪。
我也曾在夏日漫漫長夜
緊盯住夜空中秘密的星群,
千年的長河中,
只有它們是固執、清醒的。
只有它們,
能讓我日益松散的心
漸漸收緊。
那天傍晚,我開車經過一座
又一座破敗、寂靜的村莊。
夜色中,我看見并記住了
那些房子上恬靜的裂痕。
傍晚
傍晚,一個人驅車
來到黃河邊。
一個人,在大堤上散步。
在斜坡的石階上
坐下,看水和石縫間的草。
當我并不知曉更多
命運的秘密,生活就是這些
短暫的安靜,隨我
而來,隨我而去。
當我想到有一首詩被壓在
秘密的水底,像我們
經年的愧疚與恥辱。
我感受到了。那些
寂靜的石子,鋪滿了
我內心
秘密的信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