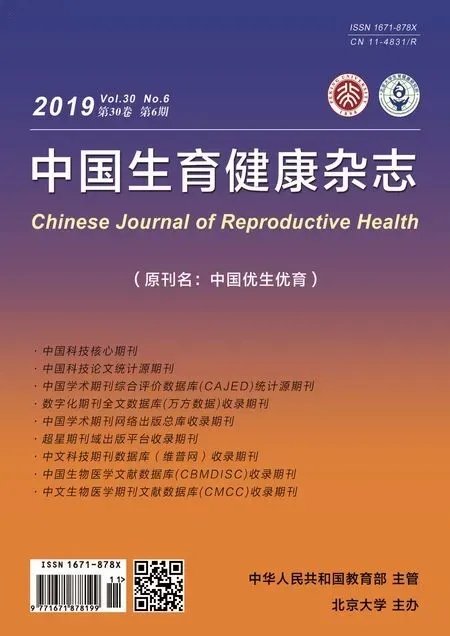早期綜合發展干預對嬰幼兒神經心理發育影響的效果分析
劉曉莉 王颎 師曉紅 白增華 郭虹 米素蘭
0~3歲是兒童早期智能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人類大腦發育最快、可塑性最強的時期。在這個階段給予適當、有效的刺激, 將使人類大腦神經元突觸的數量大幅度增加, 如再配以適當方法,兒童的智力潛能將得到極大的發揮[1-2]。研究報道,對正常嬰幼兒進行適當的早期發育指導,能夠促進其早期神經運動發育,促進嬰幼兒的精神運動發育和智能發育,為其早期全面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3]。研究和關注嬰幼兒的早期生長發育情況是中國婦幼保健工作者的重要職責之一。本研究通過對研究對象采用社區保健機構與家庭相結合的早期綜合發展干預模式,探討早期綜合發展促進對嬰幼兒智能發育及社會適應能力的影響。
對象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選取在社區兒童保健門診接受系統保健管理的健康新生兒,隨機分為研究組與對照組,每組各60名,隨訪至1歲。入選標準:母親妊娠時無重要疾病史,出生體重>2 500 g,無產時窒息史、無嚴重先天性疾病和傳染病的足月新生兒。到研究結束剔除失訪對象,最終對照組53例,研究組52例,兩組新生兒家長文化程度、家庭經濟條件、分娩方式、出生胎齡、性別、出生體格數據等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有可比性。所有研究對象調查前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二、方法
1.干預策略:研究組采用保健機構與家庭相結合的干預模式,有計劃地指導家長對其嬰兒生后實施早期發展綜合性干預措施,由專人負責定期與家長保持聯系并隨訪,干預形式采用門診預約、育兒熱線咨詢答疑、發放家長讀物、每月科學育兒小教堂、小型父母沙龍等方式進行,動態掌握并及時給予個性化的指導,在嬰幼兒、家長、保健人員之間形成指導、發展、監測和評估的互動循環。對照組給予常規門診指導。
2.干預內容:研究組采取了綜合干預的方法,包括(1)向研究組父母宣傳早期發展綜合干預的意義與方法,使家長知曉育兒的責任、知識、技能,建立起良好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模式;(2)營養與喂養指導。講解兒童生長發育的規律、如何成功母乳喂養、奶源的選擇、輔食添加和方法、喂養技術、食品安全等;(3)疾病預防。營養性疾病的防治、降低呼吸道疾病和腸道病的發生等;(4)家庭養育環境和養育方法指導。和諧的家庭氛圍、合理的教養方式、培養睡眠習慣等;(5)智能促進。主要根據嬰兒生長發育和神經心理發育規律,進行感知覺、視聽反應、語言發展、大運動、精細動作等訓練,開展親子游戲等。
不同月齡有不同的側重干預內容,包括(1)新生兒期。短暫俯臥抬頭,做嬰兒被動操和撫觸;讓嬰兒看人臉或鮮艷玩具,搖鈴訓練聽覺;進行注視、微笑、懷抱、說話等。(2)1~3月。俯臥抬頭、豎抱、被動操、3個月練習翻身;觸摸、抓握、搖響玩具;目光交流,吸引嬰兒注視和跟蹤;聽音樂,不同聲響刺激,鼓勵積極發音并回應嬰兒;照鏡子、手偶等逗引嬰兒反應。(3)4~6月。俯臥手支撐、拉坐、翻身,5個月練習靠坐,扶著腋下站立;主動抓放物品、對敲。用圖片、生活用品等訓練視覺;觸摸不同質地、形狀物品;呼喚名字尋找聲源,和嬰兒多多說話;藏貓貓、蓋布找玩具等。(4)7~9月。獨坐、爬行、扶腋下站立能蹦跳、扶欄桿站;雙手傳遞玩具、撕紙、容器中拿出、放入物品,用杯子喝水等;訓練有意識發“ma ma、ba ba”,按指令做動作和表情,識別家人和常見物品,與外界環境接觸,讀繪本,韻律游戲。(5)10~12月。手-膝爬行,拉欄站起和坐下,獨站和扶走;在積木、球等玩具中練習精細和大運動;認識五官,講故事,配合穿衣服,幫助嬰兒識別他人的不同表情,學習分享、與他人互動等。
3.干預頻率:新生兒期2次家訪,親子活動指導為1~3月每月1次,3~12月每兩周1次。同時每月1次電話隨訪、門診體檢評估、發放家長讀物、科學育兒小教堂、隨時育兒熱線咨詢答疑。
4.效果評估:(1)采用Gesell(蓋瑟爾)嬰幼兒發育量表對小兒的智力發展水平進行評估。兩組嬰兒均于生后3個月、6個月、9個月、12個月進行大運動、精細動作、適應性、語言、個人社會交往各能區的發育商(DQ)測定。(2)記錄嬰幼兒大動作發育出現的具體月齡。選擇獨坐、手膝爬、獨站和獨走這4項易于客觀判斷的發育進程作為大動作發育評估指標,大動作發育按2006年WHO標準定義[4],即“獨坐”為嬰兒穩坐于較硬平面(如床上、桌面),不用手或其他物體支撐獨坐至少10秒;“手膝爬”為用手腳或手膝動作,軀干抬高、腹部抬離床面,手膝向前或向后爬行至少3步;“獨站”指無任何依靠能獨自站立至少10秒;“獨走”指能獨自行走5步及以上。嬰幼兒的各項動作發育均由經統一培訓且具有豐富臨床經驗的兒童保健醫生在現場進行測查,如嬰幼兒能按上述標準完成大動作,則記錄為“是”,如無法按要求完成則記錄為“否”。(3)采用《嬰兒-初中生社會生活能力量表》[5](日本S-M社會生活能力檢查修訂版)對小兒社會生活能力進行測試,評分者根據年齡范圍和得分范圍換算成標準分后即可得出結果。得分越高,對應的能力越強。(4)家庭一般情況調查。
5.統計學處理:采用SPSS16.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組間比較用χ2檢驗。影響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歸,以嬰兒隨訪到12月齡時的發育商作因變量,參加多因素分析的自變量有是否給予早期綜合發展干預(賦值:不干預=0,干預=1)、性別(賦值:男=1,女=2)、是否斷母乳(賦值:否=0,是=1)、父母文化程度(賦值:小學及以下=1,初中=2,高中=3,大學及以上=4)、母親年齡、父親年齡、肉類首次添加月齡,在顯著性水平α=0.05時,進行逐步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兩組嬰兒智能發育各項評分比較
研究組嬰兒在3月齡時社交行為發展優于對照組,在9、12月齡時語言能力評分優于對照組,隨訪至6、9、12月齡時,大運動、精細動作、適應能力及社交行為各能區評分及總發育商評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二、兩組嬰兒大動作出現的月齡比較
研究組嬰兒大運動獨走出現的平均月齡要早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余大動作出現的月齡,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三、兩組嬰兒S-M社會生活能力檢查量表得分比較
兩組嬰兒在3月齡、6月齡時,社會生活能力得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成長至9月齡、12月齡時,研究組嬰兒社會生活能力得分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四、嬰兒發育商的影響因素分析
早期發展綜合干預、肉類首次添加月齡和母親文化程度是影響嬰幼兒發育商的因素,實施早期干預、母親文化程度越高將有助于嬰幼兒發育商的提高,添加肉類食物月齡越晚越影響嬰兒的發育商評分。回歸方程經F檢驗,有統計學意義(F=6.310,P=0.001)。見表4。

表1 兩組嬰兒智能發育各能區及發育商比較(得分,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and developmental quotients of intants′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表2 兩組嬰兒大運動發育年齡比較[月齡,M(95%CI)]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al age of motor between the two groups[months, M(95%CI)]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表3 兩組嬰兒社會生活能力比較(得分,Table 3 Comparison of social living ability by month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ot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表4 嬰兒12月齡時發育商影響因素的多元逐步回歸分析Table 4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of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of the infants at 12 months
討 論
國務院于2011年印發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中明確指出[6]:兒童時期是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為兒童提供必要的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的機會和條件,最大限度地滿足兒童的發展需要,發揮兒童潛能,將為兒童一生的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兒童早期綜合發展項目是一項有關于兒童權益的重要策略,其主要是依據嬰幼兒的身心發育特點,針對性開展科學的綜合性干預活動的方式,以此讓其在社會適應性、心理、認知等多個方面達到健康或完美狀態的目的[7]。本研究從新生兒開始對研究組嬰幼兒進行一系列的有針對性的早期發展綜合促進干預,結果顯示,嬰兒在3月齡時表現出社交行為能區發展優于對照組,說明早期發展干預服務不僅指導家長注重嬰兒個體化的干預,還要注意親子園的多家庭活動,嬰兒與嬰兒之間,家長與嬰兒之間的游戲互動活動,在嬰兒較小時就能表現出社會交往能力的較好發展。研究組嬰兒在9、12月齡時語言能力的發展優于對照組,隨訪至6、9、12月齡時,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嬰兒的大運動、精細動作、適應能力及社交行為各能區得分及總發育商得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也獲得影響嬰兒智能發育的因素包括了早期綜合發展干預,提示早期綜合發展服務對嬰兒的智能發育有明顯促進作用,這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8-10]。另外,進入回歸方程的因素還有添加肉類食物的月齡和母親文化程度,嬰兒的生長發育離不開營養,國內外研究證實,合理喂養行為對嬰幼兒生長發育的正面作用[11-12],如果嬰兒輔食添加構成比不合理,動物性食物添加過晚或者食用頻率低,將導致嬰兒缺鐵甚至貧血,本研究結果說明添加肉類食物的月齡越晚越影響智能的發展;早期綜合發展能夠系統指導父母正確合理的喂養,能明顯地改善父母養育知識和行為的積累,為嬰幼兒營造良好的生長發育環境和條件;母親文化程度越高,接受知識的能力越好,對嬰兒智能的發展越有好處。
嬰幼兒大動作發育作為兒童健康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不僅是運動、感知覺、認知、記憶、社會交往等能力發展的基礎,也是早期發現或識別發育障礙、神經系統疾病等的重要篩查指標,因此大動作發育一直是兒科臨床及兒童保健工作的常用評估內容之一[13]。2015年中國九城市嬰幼兒大動作發育的調查研究報道[14]顯示,獨坐、手膝爬、獨站、獨走出現的中位月齡依次為5.9、7.8、10.8、13.0月齡,4項大動作中獨走更容易受到營養狀況的影響,營養不良(低體重、生長遲緩)可能增加獨走年齡延遲風險。本研究發現,研究組獨坐、手膝爬、獨站出現時間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研究組獨走出現的中位月齡是11.8月齡,對照組獨走出現的中位月齡是13.2月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嬰幼兒社會生活能力是指獨立處理日常生活與承擔社會責任達到其年齡和所處社會文化條件所期望的程度,是嬰幼兒心理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15]。本研究通過實施早期發展綜合干預,兩組嬰兒在3月齡、6月齡時,社會生活能力得分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隨訪至嬰兒9月齡、12月齡時,研究組嬰兒社會生活能力得分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與劉貴敏等的研究一致[16],說明早期綜合干預可有效地提高嬰幼兒的社會生活能力水平。
早期綜合發展干預模式從單一的被動接受保健到主動參與保健,能動態監測嬰幼兒的生長發育情況,早期發現發育偏離,做到早期干預,加強了父母對嬰幼兒發育的認知和關注,提高了監測的有效性和實時性,促進了嬰幼兒的發展[17]。本研究基于社區,建立了健全嬰幼兒保健干預措施和相應的管理制度,從營養、預防疾病、提高父母科學育兒的態度、知識和行為,提高嬰幼兒的感知覺、運動、語言和社會交往能力等多角度進行早期綜合發展干預,達到了促進智力發展和社會生活能力的效果。腦的發育和外界環境、教育密切相關,持續給予家長定期的科學個體化指導,使家庭養育環境有著持久的影響,對于全面促進嬰幼兒神經心理的發育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