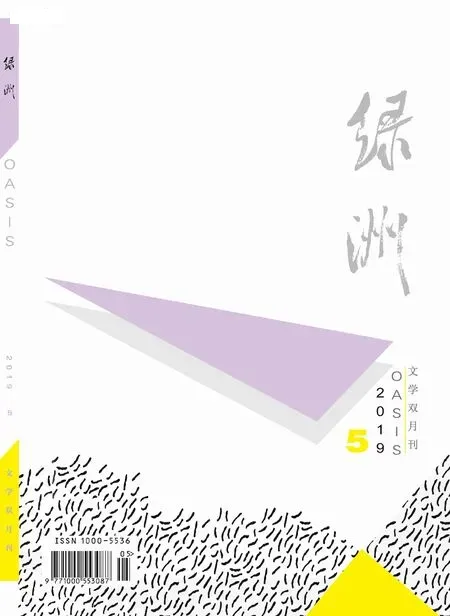從絲路沙海走來
2019-11-13 01:23:06趙天益
綠洲
2019年5期
關鍵詞:兵團
趙天益
一
晨霧淡淡地、淡淡地在古爾班通古特大漠邊緣上空裊裊升騰。
縷縷情思隨著漫漫晨霧,伴我回到魂牽夢繞的石河子——我久違了的第二故鄉,我曾經生活和戰斗過的地方。故鄉農場里的黑土地上,有刺破我手臂的鈴鐺刺,有扎爛我腿腳的葦茬錐,有我朝夕與共的親密伙伴和戰友,有我依依眷戀的田野牛羊,有我揮灑的汗水,有我掩埋的淚珠,有我的激情歡樂,也有我的悲苦和憂傷……
忘不了,這片熱土上的太陽曬得我的臉龐和黑土地一樣黑;忘不了,每塊條田里我寒來暑往走過的一串串腳印;忘不了,理想的胚胎在這里萌發時撞擊出的絢麗憧憬;忘不了,希望的種子在這里生根開花結出的馨香果實;忘不了,用香甜乳汁哺育我成長的瑪納斯河;忘不了,當年賴以安身立命的蘆葦棚和地窩子;忘不了,瘋狂的沙暴和冰雹留給我的顫栗和驚慌……忘不了啊,這一切的一切,就像魚兒忘不了水,孩子忘不了娘,禾苗忘不了土壤和太陽。
二
綠洲新城石河子游憩廣場上的標志性雕像《軍墾第一犁》,是凝固的火焰,是凝固的力量,是凝固的意志,是凝固的精神。
那位拉犁的戰友,那位掌犁的班長,那緊繃的套繩,那锃亮的犁鏵,切割得亙古荒原咯嘣嘣響。我聽慣了那種聲音,它與我們墾荒時哼唷的號子聲無比合拍,它與野天萬籟絲絲諧鳴。有了這種聲音,千古一調的荒漠協奏曲奏出了新的旋律,新的樂章。
在《戈壁灘上蓋花園》的雄壯歌聲中,石河子的莽莽荒原退卻了,白花花的鹽堿退卻了,沙丘壕溝退卻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綠洲(2022年4期)2023-01-14 08:23:30
綠洲(2022年5期)2023-01-09 12:51:08
綠洲(2022年6期)2023-01-09 10:46:38
綠洲(2022年3期)2022-06-06 08:17:22
幽默大師(2017年12期)2017-10-30 01:54:50
幽默大師(2017年11期)2017-10-27 06:17:02
幽默大師(2017年9期)2017-10-27 06:15:06
新疆職業教育研究(2016年2期)2016-04-11 09:12:26
新疆農墾經濟(2015年10期)2015-12-20 12:26:22
中國火炬(2014年12期)2014-07-25 10: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