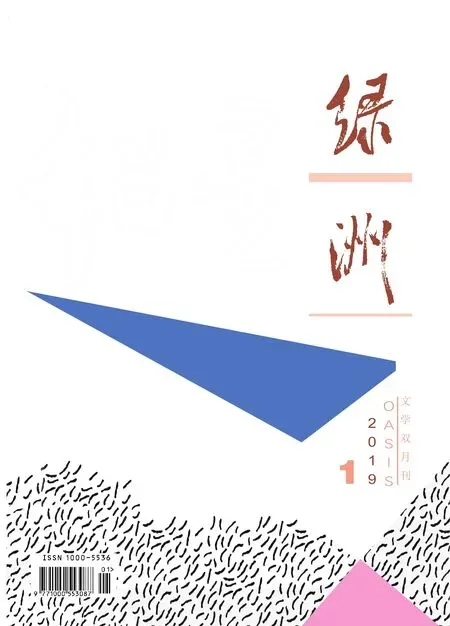沈葦:一個人的靈魂自治區
2019-11-13 02:02:20霍俊明
綠洲
2019年1期
霍俊明
當說到沈葦的詩歌和散文,人們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新疆”(包括他的《新疆盛宴》《新疆詞典》《新疆詩章》)、“西部”(西域)、“邊地”(邊界)、“異域”“民族”(族群)。那么,這種地理、文化和心理上的慣性印象(“尷尬的地域性”)對于理解一個寫作者來說意味著什么?如果一個人的寫作并不能為以上印象和關鍵詞所完全涵括,那么被“中心”位置遺漏和忽略的那部分又意味著什么?這該由誰來評價呢?“每一條路都是來由和去蹤”,正印證了道不自器。或者說詩歌寫作必須、必然要有一個所謂的“中心”和“整體”嗎?尤其是在一個感受力空前匱乏而媒體現實吞噬一切的今天,一個個碎片式的詩人和同樣漶散的詩歌文本有所謂的“中心”嗎?在時光的刀斧和人性的淵藪那里我看到一個詩人正在為自己設置一個言說的中心與內核,那低低的雷聲正在耳畔響起,偶爾炸開。在我看來,沈葦一直在抒寫自己的靈魂自治區。
沈葦這本詩集中的“少即多集”一輯收入的都是八行之內的極短詩作,在數行之內完成一首詩作也許并不難,但是處理一定數量的如此短詩(沈葦已寫有此類詩一百余首)其難度和危險系數就大大提升了。詩行越短,對詩人的要求就越高——正如一個人過橋時木頭被抽換成了幾根鋼絲。這樣的詩是字數上做減法但是在精神內里上卻要做乘法,即少即是多。而對于沈葦來說他每每能履險如夷,這就是詩人的特殊能力——修辭和精神的雙重能力。讀這樣的短詩甚至不需要去揣測什么微言大義、字字珠璣,你只要在某一個瞬間被一個詞語一個句子像閃電一樣地照徹就足夠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