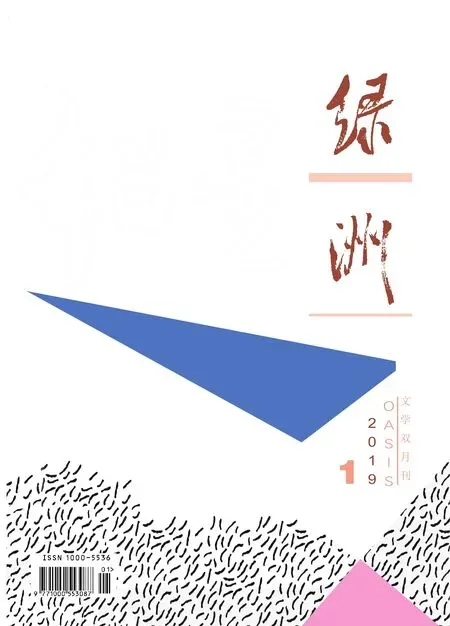我不是來(lái)參加葬禮的
方曉
下周馬麥要去首爾做半年的交換生,他一個(gè)月前就告訴了馬尚,但一直沒(méi)有得到答復(fù)。周五夜里,他問(wèn),錢準(zhǔn)備好了嗎,這次再浪費(fèi)名額我就沒(méi)機(jī)會(huì)了。馬尚已拒絕過(guò)他兩次;學(xué)校不會(huì)總把機(jī)會(huì)給不珍惜的人,下午,馬麥的班主任在電話里說(shuō),有點(diǎn)類似最后通牒。他不反對(duì)馬麥去,可是錢的問(wèn)題無(wú)法解決。昨天,他找到廠里工頭,剛露出想預(yù)支工資的意思,矮壯的工頭用兇巴巴的一句話就打發(fā)了他:眼下經(jīng)濟(jì)形勢(shì)這么糟,正打算裁員,你要想走人我倒能馬上批準(zhǔn)。他也找過(guò)偶有來(lái)往的幾個(gè)人,結(jié)果在開口之前就知道了,他也不覺(jué)得別人有理由借給他兩萬(wàn)塊。他沒(méi)打算告訴馬麥這些,難題仍舊沒(méi)能解決,馬麥反而會(huì)覺(jué)得他在自我開脫。在相顧無(wú)言很久之后,他沒(méi)料到馬麥竟然說(shuō)出這樣的話來(lái):這輩子我只求你這一件事了。而他才十一歲。
第二天清晨,馬尚起床做好早飯,叫醒馬麥。我要出趟遠(yuǎn)門,他說(shuō)。他看見(jiàn)馬麥眼里有光閃了一下又熄滅了。他等著馬麥詢問(wèn),但沒(méi)有等到,他也就沒(méi)有再說(shuō)下去。何況他對(duì)此行能否成功一點(diǎn)也不確定。去客車站的路上,他想起昨夜模糊的夢(mèng)境,在城市背后的原野上,他和林谷拉著馬麥的手隨風(fēng)奔跑。他能感覺(jué)到李潔就站在角落里看著,在夢(mèng)里,他也許想尋找她,但終究沒(méi)有找到。
馬尚還是第一次去往林谷的城市,浙江西南部一個(gè)叫云和的小縣城。客車啟動(dòng)時(shí),馬尚又捏了捏口袋里的那張紙,上面是林谷寫下的地址。林谷八年沒(méi)出現(xiàn)了,他不知道如果她更換了地址該如何是好,但現(xiàn)在好像只剩下這一條路好走了。車窗外,春天的朝陽(yáng)在城市樓宇間浮浮沉沉。十九年前,他在青蟬酒店里當(dāng)傳菜工,也是一個(gè)春天的上午,他注意到一個(gè)穿著火紅風(fēng)衣的女人,在透窗進(jìn)來(lái)的陽(yáng)光里,她微側(cè)的臉看上去嬌羞動(dòng)人。她在接聽電話。她突然向馬尚招手讓他過(guò)去,捂住話筒說(shuō),現(xiàn)在,我是在成都。她又告訴電話那邊的人,如果非不信,我證明給你看。馬尚幫她圓了謊,沒(méi)有問(wèn)為什么。幾天后,馬尚又對(duì)電話里的同一個(gè)男人說(shuō),這里是重慶。他感覺(jué)對(duì)方并不相信,但林谷說(shuō),無(wú)所謂,這只是一種需要。
客車在村莊小道上穿行,不時(shí)停上片刻。這讓馬尚擔(dān)心今天無(wú)法回程,李潔去世以后,他還從未讓馬麥獨(dú)自一人過(guò)夜。或許林谷留下地址時(shí),就設(shè)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出現(xiàn)在門前,要如何向家人介紹他,他無(wú)須考慮。兩次電話事件過(guò)去很久,他都快把她忘了,但夏天過(guò)半時(shí),她又出現(xiàn)了。她送給他一個(gè)公文包:這是回報(bào),請(qǐng)務(wù)必收下。他看不懂英文但知道價(jià)格不菲。不過(guò)我有個(gè)要求,她又說(shuō),我想去你常去的地方玩玩。他們?nèi)サ牡胤讲粌H迎合了她的好奇,還贏得了她的驚嘆。原始山洞,地下拳擊場(chǎng),廢棄的村落,干枯的河床,這些地方他也是第一次去,但她的快樂(lè)證明他的猜想是正確的。看來(lái)你了解我,她興奮地說(shuō)。在青蟬酒店門口道別時(shí),她指著不遠(yuǎn)處山邊露出的屋尖——是棟別墅,打電話的人就住在那,她說(shuō),我父親,他想讓我繼承他的事業(yè),在全國(guó)開連鎖酒店。那天夜里,林谷向前走去,又突然回過(guò)頭來(lái),在路燈下,她眼里有種夢(mèng)幻般的亮彩,她說(shuō),我喜歡今天每一秒的感覺(jué)。此后十一年,馬尚在附近干過(guò)四份工作,但一次也沒(méi)去過(guò)那里。
十一點(diǎn),客車到達(dá)云和縣城,比預(yù)想要遲一個(gè)小時(shí)。“在南邊,有點(diǎn)遠(yuǎn),富人區(qū)。”出租車司機(jī)回答馬尚的詢問(wèn)。馬尚緊盯著馬路邊閃退的風(fēng)物,盡力不去想將要到來(lái)的遭遇。玉蘭花和紅葉李正在盛開,垂柳倒映在污濁的河水上。他記得林谷說(shuō),玉蘭花期很短,像古代青樓中的花魁,無(wú)子,很快殞敗。
“來(lái)談生意?”他聽到司機(jī)在問(wèn)。
“借錢,”他如實(shí)回答。
“那關(guān)系不一般。”
“我不知道,”他想了想,才說(shuō)。
“我是說(shuō),這年頭還愿意借錢的。”
“我們有幾年沒(méi)見(jiàn)了。”
“也不事先打個(gè)電話,讓他來(lái)車站接你,那里住的都不止一輛車,還有人雇了專職司機(jī)。”
“沒(méi)有。”馬尚說(shuō),他感覺(jué)有種并不新鮮的挫敗感在逼他坦白,“我沒(méi)她的號(hào)碼。”
司機(jī)從后視鏡看了他一眼,咬住了即將出口的話。車停在一幢藏青色外墻的三層小樓前。沒(méi)有任何標(biāo)志證明林谷在這里生活;她曾說(shuō),二樓陽(yáng)臺(tái)上懸掛著紫色風(fēng)鈴,臥室窗簾是天藍(lán)色的,在夜里看著它會(huì)想到寧?kù)o的海。大門緊閉——這也是一種不錯(cuò)的結(jié)局;他完成任務(wù)了,盡管回去無(wú)法向馬麥交代。現(xiàn)在,他仍然沒(méi)想好要從何說(shuō)起,他更擔(dān)心直到離開自己什么也沒(méi)說(shuō)。十八年前,是他親手關(guān)閉了通向富足生活的罅口。她父親應(yīng)該知道一個(gè)傳菜工的存在,他沒(méi)有問(wèn)過(guò),在她與父親的較量中,他有沒(méi)有成為一個(gè)砝碼,如果父親逼迫她繼承家族事業(yè),她就義無(wú)反顧地嫁給一個(gè)傳菜工。那年春天,她生日,他用一個(gè)月工資買了條絲巾送她。后來(lái)他認(rèn)為,這是個(gè)提前來(lái)臨的錯(cuò)誤,而且是由他掀下爆破的按鈕。慶祝我們相識(shí)一周年,兩天后她回贈(zèng)禮物時(shí)找了這樣的理由,給他的感覺(jué)輕忽而牽強(qiáng)。是一只手表;三年前他用它抵償了半年房租。他送她一只翡翠手鐲,不過(guò)兩千,然后他被帶到杭州大廈,必須在一輛山地車和一架單反相機(jī)之間做出選擇。他憤怒之下全要了。它們?cè)谌ツ瓯凰舆M(jìn)舊貨市場(chǎng),換來(lái)馬麥渴望已久的電腦。她從來(lái)不會(huì)意識(shí)到這是對(duì)一個(gè)男人的傷害嗎?他想問(wèn)但沒(méi)有問(wèn),因?yàn)樗裁靼姿^非故意。她本來(lái)就是那種臨時(shí)得知新加坡有場(chǎng)演唱會(huì),會(huì)連夜坐高價(jià)飛機(jī)去現(xiàn)場(chǎng)看演出的人。富足,原本是他在夢(mèng)中都渴求的,但現(xiàn)實(shí)中真的來(lái)臨時(shí),他不知為何竟無(wú)法消除內(nèi)心里恐懼的細(xì)密陰影。只要他在昂貴的價(jià)牌前表現(xiàn)出猶豫,她必然會(huì)說(shuō):不用擔(dān)心錢的問(wèn)題,我付。她付,這正是他擔(dān)心的。我們不是一類人,有次他近乎賭氣地說(shuō)。她先是一臉愕然,然后也情緒失控了:我不理解更受不了你這渺小的無(wú)事生非的痛苦。他想過(guò),但無(wú)法向自己求證,在與她形成親密關(guān)系的原因中,富足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或許,人總是容易傾心于自己無(wú)法擁有的東西——與其說(shuō)是他吸引了她,還不如說(shuō)是貧窮,她希望過(guò)上一種與日日厭煩的富足完全不同的生活;也許不是這樣。面對(duì)她,他開始感到怯懦,有時(shí)甚至不敢開口說(shuō)話,最初和她在一起時(shí)的那種徐緩自如、快樂(lè)會(huì)隨時(shí)自然來(lái)臨的狀態(tài)從他身體里慢慢消失了。他們的關(guān)系在他又一次斷然拒絕禮物時(shí)戛然斷裂,然后從此不再聯(lián)系。并非因?yàn)楦星椴缓隙质郑R尚覺(jué)得這是命運(yùn)給他留的唯一情面。
“你是來(lái)參加葬禮的嗎?”背后傳來(lái)一個(gè)女人的聲音。馬尚轉(zhuǎn)過(guò)身,是個(gè)四十左右的女人,豐厚的嘴唇上涂著粉色口紅,臉上是那種瞬間就可能轉(zhuǎn)變?yōu)槔淠拿C穆神情,現(xiàn)在正被悲傷緩慢而艱難地覆蓋。她也許只有三十來(lái)歲。
“請(qǐng)問(wèn),這家現(xiàn)在有人嗎?”
她沒(méi)有回答,示意馬尚跟著自己往前走。她抱著一床毯子,邊走邊回頭說(shuō):“他兩天兩夜沒(méi)合眼了,殯儀館那鬼地方連個(gè)鋪蓋都不提供。”
馬尚不知該如何回應(yīng),只好努力摒除正從心里涌出來(lái)的某種寒意。
“我是他鄰居。”女人又說(shuō),“你幸虧遇到我了,是從外地趕過(guò)來(lái)的吧?”
“我只是路過(guò),我是林谷生意上的一個(gè)朋友,順道來(lái)看她,”馬尚希望對(duì)方聽清了他說(shuō)出的姓名,也許存在誤會(huì),他找錯(cuò)了地方。他感覺(jué)自己有些結(jié)巴,又補(bǔ)充說(shuō):“我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事。”
女人停下腳步,認(rèn)真地看了他一眼,又點(diǎn)點(diǎn)頭,但仍然沒(méi)有回答他的問(wèn)題,而是指著左前方的一家酒店:“等會(huì),就在這里答謝親友。”
酒店紫黑色的玻璃墻顯得雍容華貴,里面映出馬尚的影子。頭發(fā)紛亂,身形疲倦,還有生活饋贈(zèng)給他的怯懦——也許在今天都可以被人當(dāng)成悲傷。他覺(jué)得自己無(wú)論如何也不像個(gè)生意人:“我是林谷的同學(xué)。這里挺高檔。”
“附近最好的。他們家境這幾年已經(jīng)說(shuō)不上好,他卻非要選擇這里,讓人羨慕。呃,我不該這么說(shuō)。”女人說(shuō)。
馬尚看見(jiàn)自己做了個(gè)手勢(shì),但一時(shí)并不明白究竟是想表達(dá)不介意,還是驅(qū)趕心頭的惶惑。
“我是說(shuō)他們感情一直不錯(cuò)。他投資虧了些錢,”她瞄過(guò)來(lái)的目光仿佛在判斷馬尚是不是個(gè)債主。他們已走到公交站,女人接著說(shuō),“我就從來(lái)沒(méi)看見(jiàn)他們紅過(guò)一次臉,據(jù)我所知其他人也沒(méi)有看到。每個(gè)節(jié)日他都送花給她。”
車來(lái)了。她推搡他上車,似乎早已洞悉了他要逃走的念頭:“有時(shí)候就是這么湊巧,可能注定你要來(lái)送她最后一程。底站就是殯儀館。”然后,她終于沉默了。
馬尚對(duì)殯儀館并不陌生。他害怕它的任何氣味。八年前,他送走李潔。路過(guò)營(yíng)業(yè)部,他問(wèn):“我是不是應(yīng)該買個(gè)花圈。”
“要我說(shuō),最好是這樣。”女人立即回答。
“誰(shuí)?”售貨員手按在電腦鍵盤上問(wèn)。要在花圈上祭奠誰(shuí)。馬尚突然發(fā)不出聲音。林谷,女人說(shuō)。他猜到了。似乎他早已知道,不然他不會(huì)出現(xiàn)在云和。他似乎對(duì)這個(gè)消息并不震驚。誰(shuí),他聽見(jiàn)售貨員又在問(wèn),這次是落款上的名字。他遲疑著,“李麥。”他說(shuō),“我,李麥。”
終于又見(jiàn)到她了。她躺在遺像后的靈床上。她在遺像里看著他。他也凝視著她,還是她,那略顯蒼老的臉龐上依然藏著一種嬌羞。他奇怪自己在這一刻為何沒(méi)有感到悲傷。他朝遺像三鞠躬,有幾個(gè)早就等在一旁的人,也向他鞠躬致謝。他沒(méi)有去看他們的臉,他們彼此沒(méi)說(shuō)一句話。他走到一個(gè)角落里,在長(zhǎng)凳上坐下來(lái),從這兒能瞥見(jiàn)她的身體,她應(yīng)該了無(wú)生氣了吧,他閉上眼睛,不敢去看。
十分鐘過(guò)去了;或許已經(jīng)過(guò)去一個(gè)小時(shí)。有人在搖晃他的胳膊。他抬起頭,是那個(gè)女人,“走吧,悲傷是沒(méi)用的。”她的聲音里盈滿安慰的氣息,但在他聽來(lái)又近乎命令,“現(xiàn)在我們?nèi)ゾ频辍!彼幌肴ィ膊幌氪粼谶@里,他順從地起身。
他們到時(shí)很多人已經(jīng)就座。似乎寥廓無(wú)邊的酒店大廳里布設(shè)了七十多桌。他跟隨女人在其間穿梭,她似乎在尋找兩個(gè)緊挨的座位。他和很多人迎面而過(guò),他擔(dān)心突然遇見(jiàn)一個(gè)熟識(shí)的面孔,又立即覺(jué)得這種擔(dān)心太過(guò)多余。他和林谷的所有交往都只屬于一個(gè)隱秘、封閉、如今隨著她的死亡而被埋葬了的世界。女人的心愿終于得到滿足,拉著他坐下來(lái),他不理解她為何要如此,但沒(méi)有反對(duì)。他還沒(méi)離開可能只是覺(jué)得這樣做并不合適;自下出租車以來(lái),他第一次想到了此行的目的。他意識(shí)到自己正在為徒勞無(wú)功而懊惱。
“林谷的同學(xué)。”他聽見(jiàn)女人在說(shuō)話。她帶領(lǐng)他出現(xiàn),似乎就有了介紹的責(zé)任。
他朝同桌的人點(diǎn)頭致意。他依然不去看他們的臉,他不打算記住今天的任何場(chǎng)景和任何人,他已經(jīng)暗自決定要把今天經(jīng)歷的所有細(xì)節(jié)統(tǒng)統(tǒng)忘記。他覺(jué)得女人看出來(lái)了他不是林谷的同學(xué),但不明白她為何不揭穿卻還要幫他隱瞞。
突然,所有聲息都停止了。一個(gè)男人從門口慢慢走進(jìn)來(lái)。
“喏,那就是他。”女人對(duì)馬尚說(shuō)。可能是因?yàn)樗樕线t鈍的表情,她又說(shuō):“他就是唐森。”
“我知道。”他只是說(shuō)。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這個(gè)名字。
唐森正向大廳中央搭建好的T臺(tái)走去。盡管步伐緩慢而沉重,但馬尚遠(yuǎn)在二十米開外也能感覺(jué)到他整個(gè)人都表現(xiàn)出那種極度悲傷之后的極度亢奮。然后唐森站在T臺(tái)上開始說(shuō)話。馬尚要求自己不去聽他在說(shuō)什么。他厭惡唐森那貫穿在嘶啞聲音里的夸張的沉痛。他接受不了這種表演,如果它是。唐森用雙掌合十和謝謝大家結(jié)束了發(fā)言,竟然爆發(fā)了掌聲。馬尚有站起來(lái)呵斥什么的沖動(dòng),但按捺住了,他感覺(jué)到身邊的女人正在觀察他;她舀來(lái)一勺花生米放進(jìn)他的碗里,細(xì)嚼慢咽有助于平復(fù)情緒,她說(shuō)。人們都已經(jīng)埋頭吃起來(lái),異乎尋常的肅穆與寧?kù)o。但憂傷的主題只維持了三分鐘,然后就漸漸嘈雜了,很快——幾近于狂歡。
“這只是一個(gè)形式。”女人對(duì)他說(shuō)。“每個(gè)人都需要。不用過(guò)多久,所有人都會(huì)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包括你我,還有唐森。”
他不喜歡她話里的解釋甚至勸慰的氣息,似乎她已然了解一切。他盯著酒瓶。女人轉(zhuǎn)動(dòng)桌盤,拿過(guò)酒瓶,沒(méi)有征得他的同意,給他倒?jié)M:“喝點(diǎn)吧,會(huì)好受一些。”
他確定了,是從已對(duì)她有所依賴感覺(jué)出來(lái)的:女人和李潔有些相像。他似乎一直想讓李潔的形象在腦海中明朗起來(lái),從昨晚的夢(mèng)里開始,來(lái)的路上,凝視林谷的遺像時(shí),他就盡力回想,現(xiàn)在終于做到了。那年,林谷突然不見(jiàn)了之后,他對(duì)身邊的任何女人都再難有好感。有幾個(gè)女人對(duì)他表現(xiàn)出善意。他在租房里每天看見(jiàn)一個(gè)女人抱著孩子上下樓梯,她應(yīng)該就住在上面一層,他從未見(jiàn)過(guò)她丈夫,她給他送來(lái)燒好的菜。小賣部肥胖的女店主,有口白森森的牙齒,總朝他露出曖昧的笑容。隔壁花店的女服務(wù)員,右眼有殘疾,但手很美,身上總帶著清淡的香味,她送給他散落的花葉。送報(bào)紙的郵政快遞員,一年四季都穿著一身藏青色的工裝,有次給他帶來(lái)一籃自家種的花生,她的腿腳看上去不太靈便。他想過(guò)和她們?cè)谝黄穑种肋@只會(huì)永遠(yuǎn)停留在想象里。他從來(lái)沒(méi)有碰過(guò)女人。一天,他站在街頭櫥窗前,中午他喝了點(diǎn)酒,他發(fā)現(xiàn)玻璃里的那個(gè)男人憔悴、瘦弱,每一寸肌膚都在往外傾瀉著失魂落魄的挫敗感。左邊是一家洗頭房。他在它門前徘徊。不要進(jìn)去,身后傳來(lái)一個(gè)女人的聲音,是青蟬南面傣妹火鍋店的服務(wù)員,里面很臟,她說(shuō)。他知道她叫李潔,偶爾,他會(huì)在火鍋店里坐到打烊。你來(lái)店里吧,我十一點(diǎn)下班,她說(shuō),她的眼里流動(dòng)著理解又同情的氣息。凌晨,他們?cè)诨疱伒晗鄬?duì)而坐時(shí),他覺(jué)得這種氣息在她眼里有增無(wú)減。你中午喝酒了,她說(shuō),像在為一個(gè)孩子的錯(cuò)誤尋找開脫的借口。他點(diǎn)點(diǎn)頭;為什么要反對(duì)呢,如果她需要他承認(rèn)。她的手伸過(guò)桌面,按壓在他的手腕上,別去那種地方,她說(shuō),在他聽來(lái)溫慰的語(yǔ)氣多于勸誡——只要一次,性情就會(huì)變化,你看待世界的眼光就不一樣了。他倒覺(jué)得說(shuō)成女人更合適,因?yàn)閷?duì)這個(gè)世界他從來(lái)就沒(méi)有好感過(guò)。
你們看上去真般配啊,他總聽到別人這樣評(píng)價(jià)。李潔大他四歲。他并不以結(jié)婚為目的和她交往,但半年后他們結(jié)了婚。門當(dāng)戶對(duì),簡(jiǎn)單得有些潦草的婚禮上,證婚人的祝福里也有這句話。那么,這就是他選擇與李潔在一起的理由了。因?yàn)橹浪畛醯拿孛埽顫崗膩?lái)不真心信任他。在你心里我就是一個(gè)潛在的淫棍,有次李潔盤詰他的去向時(shí)他怒不可遏地說(shuō)。他自我懲罰或者說(shuō)釋放內(nèi)疚的方式,是剝奪了孤獨(dú)生活養(yǎng)成的最后一份消遣,不再一個(gè)人沉默地喝上幾杯。仿佛真如她說(shuō)的,是酒讓他在洗頭房門前徘徊。而貧窮,婚后不僅沒(méi)有改觀,反而疊加上了李潔也從未逃脫的困窘,但畢竟,它也被李潔分擔(dān)了一半。這個(gè)很多時(shí)刻表現(xiàn)得理性而克制的女人,精打細(xì)算地?fù)踉谪毟F面前,遮蔽了此前它時(shí)時(shí)刻刻投向他的陰影。然后,馬麥猝不及防地來(lái)了。他還沒(méi)準(zhǔn)備好,還從未想象過(guò)一個(gè)父親的角色,但孩子似乎是個(gè)水到渠成的東西。他沒(méi)有任何反對(duì)的意思表露出來(lái);不抗?fàn)帲敲鎸?duì)這個(gè)糟糕世界最好的自我保護(hù);夜里,他聽著身邊還談不上多熟悉的女人的呼嚕聲時(shí),就是這樣想的。他偶爾會(huì)想起林谷,但次數(shù)越來(lái)越少,時(shí)間越來(lái)越短,她越來(lái)越像他眼前一道不可捉摸的陰翳。李潔不知道也永遠(yuǎn)不會(huì)知道她的存在。
他離開青蟬酒店,去呆蟬咖啡吧當(dāng)服務(wù)生,然后去凌睿酒店管理公司做倉(cāng)庫(kù)管理員,接著又在黃金影視公司干勤雜工,它們距離很近,在同一條街道上。十一年,他沒(méi)有離開過(guò)那條街道。
“以前他是個(gè)小公務(wù)員。”馬尚半天才反應(yīng)過(guò)來(lái)女人是在向他介紹唐森。她憑什么認(rèn)為他對(duì)唐森一點(diǎn)都不了解呢。唐森正在挨桌向客人敬酒,他神色依然亢奮,但腳步已有點(diǎn)虛浮。“后來(lái)下海了,”女人還在說(shuō)著。
“呃。”馬尚希望傳達(dá)出了就此終結(jié)這個(gè)話題的意味。他不想了解唐森,一點(diǎn)也不想。他后悔沒(méi)有帶馬麥來(lái),滿桌的菜至少有一半沒(méi)動(dòng)過(guò),他們可以一起飽餐一頓,有些是馬麥從未吃過(guò)的。他尋思等會(huì)讓服務(wù)員打包合不合適;他決定就這么干。
“他開了家文化公司。”女人又說(shuō),“還沒(méi)自我介紹,我是個(gè)圖書管理員。所以我知道文化這東西可以裝點(diǎn)門面,但當(dāng)成生意做就不太靠譜了。”他不明白她為什么沒(méi)有介紹姓名,又暗自慶幸她沒(méi)有這樣做。女人換上了一種強(qiáng)調(diào)又神秘的口吻,“對(duì)這個(gè),林谷也是反對(duì)的。”
她是在暗示什么嗎,林谷的死是一起悲劇?不僅關(guān)乎情感,還有更多惡劣的東西,卻又并非疾病或者意外事件,而是和新聞里的那些犯罪有雷同之處?他覺(jué)得這一切都和自己無(wú)關(guān),沒(méi)必要深究。
“林谷的同學(xué)。”女人在向唐森介紹他。
他站起來(lái),唐森向他伸出手。“謝謝你能來(lái),”唐森說(shuō),聲音干枯、顫抖,眼角還殘留著淚痕。他們碰了杯,都喝干了。唐森又伸出雙臂,馬尚略微猶疑,然后也緊緊擁抱了他。
“等會(huì)你送他回家吧,再聊聊,多安慰他。”唐森走后,女人說(shuō)。剛才,他恍惚能捕捉到唐森和女人之間有種只能意會(huì)的親密,而且他們?cè)谡谘谶@種感覺(jué)。
在酒店門口,他攙扶著搖搖欲倒的唐森,女人向他道別。他想說(shuō)再見(jiàn),但吞了回去。
“什么病?”馬尚不想這樣問(wèn),但還是說(shuō)出了口。
窩在沙發(fā)里的唐森好像睡著了。室內(nèi)光線幽暗,淺棕色的窗簾只拉開半扇,外面天已轉(zhuǎn)陰。一如從屋外看來(lái),目光所及的每一處都沒(méi)有林谷曾經(jīng)存在過(guò)的跡象,他無(wú)法判斷那年她描述的家居環(huán)境是謊言或者只是想象,還是在后來(lái)的某一天被誰(shuí)徹底清除了。
“心肌梗塞。醫(yī)生是這么說(shuō)的。”唐森緩慢睜開眼,沒(méi)有掩飾語(yǔ)氣中的厭煩。馬尚說(shuō)對(duì)不起,不該再問(wèn)這個(gè)他幾天來(lái)一直回答的問(wèn)題。唐森搖搖頭,目光移向窗外灰蒙蒙的樓房,春天的第一場(chǎng)雨已在下落,“但我想并不是因?yàn)檫@個(gè)。”
“真可惜,她還這么年輕。”馬尚說(shuō)。
“是啊。”
“她走得不痛苦吧。”
“差不多有一年半。”唐森說(shuō),“從她臥床開始,我就感覺(jué)有些對(duì)不住她了。”
然后沉默來(lái)臨。很長(zhǎng)時(shí)間過(guò)去,沒(méi)有人說(shuō)出一個(gè)字來(lái)解救眼下的困境。唐森突然起身,去了另外一個(gè)房間。似乎應(yīng)該離開了,但馬尚還是決定再等一會(huì)兒,馬麥的問(wèn)題依然沒(méi)能解決。八年前一個(gè)春天的上午,就像在一條圓形跑道上背向而行的兩個(gè)人勢(shì)必再次遭遇,林谷出現(xiàn)在呆蟬咖啡吧。他一時(shí)無(wú)法分辨她的到來(lái)是計(jì)劃還只是命運(yùn)的巧合或者捉弄。你還好吧,她問(wèn)。嗯,還好,你呢。我,我也不錯(cuò)。好像重新見(jiàn)面只為了看看對(duì)方是否還活著。然后,尷尬密布在他們之間的空氣中,他想努力找隨便一個(gè)話題來(lái)打破,但沒(méi)有做到。很意外又見(jiàn)到你,他終于說(shuō)出話來(lái),李潔死了。她顯然花了一點(diǎn)時(shí)間才明白他說(shuō)的是誰(shuí)。來(lái),喊阿姨,他招呼在角落里獨(dú)自玩耍的馬麥。那年,馬麥三歲。李潔半個(gè)月前迅速地死于一次怪異的流感。臟兮兮的馬麥就像個(gè)流浪街頭的孤兒——林谷震驚又同情的眼光透露了她的看法。一個(gè)女人用死亡給另一個(gè)女人騰出了位置,馬尚不知為何會(huì)這樣想,也許這是個(gè)全新的機(jī)會(huì)。但那天什么也沒(méi)有發(fā)生。下午,他們帶馬麥去植物園,他們一左一右牽著馬麥的手隨風(fēng)奔跑。在風(fēng)中,他恍惚聽到她問(wèn),當(dāng)年我們做錯(cuò)了嗎?只此一次。她好像也一直在思考這個(gè)問(wèn)題,不僅有疑問(wèn),還有遺憾。她臉上已經(jīng)初顯歲月賦予的滄桑痕跡,嘴邊露出的不再是明晃晃的俏皮笑容,而是不經(jīng)意就敷上了一層酸楚,但神態(tài)又顯得平和、安穩(wěn)、泰然,仿佛什么都能接受,甚至相信了命運(yùn)。她在生活中一定遭遇了什么,但他不想問(wèn)。
你父親……,他問(wèn)。
在養(yǎng)老院,他堅(jiān)持要去的,她打斷他,語(yǔ)氣快速而清淡,仿佛在講一個(gè)不相干的人的故事,我們還是很難適應(yīng)對(duì)方。他不愿和我生活在一起,他中風(fēng)兩次了。
他沒(méi)有問(wèn)她的婚姻情況。畢竟,她也沒(méi)有主動(dòng)說(shuō)起。
身上只有這么多,她遞給他錢時(shí)說(shuō)。他覺(jué)得她的意思是下次會(huì)多帶點(diǎn)——他希望是這樣,會(huì)有下次,她再出現(xiàn)。他沒(méi)有拒絕,接受得那般理所當(dāng)然;她似乎為此有些吃驚。他還不知道一個(gè)無(wú)一技之長(zhǎng)又卑怯到自閉的男人,帶著一個(gè)幼兒該如何生活下去。他已經(jīng)在承受,而且預(yù)感到只會(huì)越來(lái)越糟。他并不為此感激她,是她出現(xiàn)了又離開,才讓他把生活過(guò)成了如今這個(gè)樣子。他甚至覺(jué)得她遞錢時(shí)小心的動(dòng)作有些可笑;她早就應(yīng)該知道,在不可改變的現(xiàn)實(shí)面前,沒(méi)有什么是不會(huì)改變的。
后來(lái)她卻再?zèng)]有出現(xiàn)。這些年他要求自己不去想這是為什么。那時(shí),疾病的陰霾還沒(méi)有盤桓在她和唐森的生活里,所以那本不該成為最后一次訣別。現(xiàn)在她死了。如果李潔不是和他、如果林谷是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們或許都不會(huì)早亡吧。選擇和這個(gè)人而不是和那個(gè)人一起生活,其實(shí)就是選擇了另外一種命運(yùn),在今天,在這個(gè)陌生、陰冷、他早就可以離開卻仍然被迫等待一個(gè)男人出現(xiàn)的房間里,他無(wú)法不這樣想:甚至還選擇了生和死。
唐森回來(lái)了,手中拿著兩只酒杯和一瓶酒。馬尚知道是米卡莎紅酒杯和花莊葡萄酒。那年,她每次都帶著它們進(jìn)餐館,如果不是米卡莎盛著花莊,她就寧可喝白開水。她經(jīng)常說(shuō),來(lái),馬尚,陪我喝點(diǎn)。看來(lái)他們已深受彼此影響,有些甚至成了習(xí)慣。
唐森坐下來(lái),斟上酒,把一只杯子推到他面前。
“她父親生意敗了。”唐森再次開口時(shí)聲音低沉,但馬尚不認(rèn)為其間注滿了憂傷。“我們,我和她從來(lái)都不屬于一個(gè)階層。已經(jīng)固化,你應(yīng)該知道的,兩個(gè)階層的人很難真正交流,情感并不能克服障礙,相反,我能這么說(shuō)嗎,情感在它面前表現(xiàn)得無(wú)比脆弱。”
馬尚在心里為這個(gè)說(shuō)法擊節(jié)贊嘆——仿佛唐森替代他生活在了某種宿命里,他想立即表達(dá)贊同,話到嘴邊卻又變成,“我不太能明白你的意思。”
“很多隔膜磨合不了,習(xí)慣難以容忍。”唐森說(shuō),然后笑起來(lái)。
馬尚點(diǎn)點(diǎn)頭。
唐森的目光在馬尚的臉上逐漸聚焦,“她曾經(jīng)和一個(gè)叫馬尚的男人,對(duì)了,我還沒(méi)有請(qǐng)教你的名字。”
林谷曾經(jīng)告訴過(guò)他什么,如何向他形容那個(gè)叫馬尚的男人;我是否像一根楔子嵌入了他們的心臟,阻斷了情感血液的流動(dòng),我是否成為一次又一次家庭紛爭(zhēng)的肇端或借口,讓原本看上去靜好的一切變成了懷疑、痛苦和夜不成眠。馬尚想承認(rèn),那就是我,那樣或許一種他眼下正急切需要的解脫感會(huì)立即到來(lái)。李麥,他說(shuō)。
“抱歉,我對(duì)這個(gè)名字一點(diǎn)都不熟悉。”
“那就好。”
唐森或許更在乎她曾經(jīng)的背叛——哪怕是在遭遇他之前,相比她已經(jīng)到來(lái)的死亡。
“我們是同學(xué),”馬尚說(shuō),決定還是用這個(gè)詞。“有幾年沒(méi)見(jiàn)了。我們畢業(yè)后就沒(méi)有見(jiàn)過(guò)。”
“那么,你能跟我說(shuō)說(shuō)她嗎?”唐森臉上布滿了真誠(chéng)的期待。
這讓馬尚對(duì)他有了一絲同情。旁人的敘述可以沖淡、彌補(bǔ)或修正記憶,她的或許已被遺忘的美好會(huì)重新呈現(xiàn)在他面前。他需要。
“她很好,人們都喜歡她。”馬尚忽然哽咽住了,“對(duì)不起,我還是不知道該從何說(shuō)起。”
“呃,沒(méi)關(guān)系。”唐森用理解的眼光看著他,仿佛該得到同情的是他。“你們以前關(guān)系很好?”
“一般,我是說(shuō),還行。畢業(yè)后我們?cè)贈(zèng)]見(jiàn)過(guò)。我走投無(wú)路了,被放高利貸的追殺,但我能盤活,如果……”
唐森伸手過(guò)來(lái)碰杯,止住了他。然后沉默再次降臨,兩個(gè)男人似乎都在傾聽外面的雨聲。室內(nèi)光線更幽暗了。又過(guò)了一會(huì)兒,唐森說(shuō),“也許你愿意帶走她的什么東西。請(qǐng)?jiān)徫疫@么說(shuō),有些東西我不想保留。我簡(jiǎn)直認(rèn)為是全部。”
“我不需要。”馬尚聽出自己的語(yǔ)氣硬邦邦的,甚至帶著宣誓的憤怒。“她所有的東西對(duì)你都是有意義的。你會(huì)害怕自己忘記她,只有它們才能讓她存在得更久些。”幾乎是為了阻止什么,他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唐森臉上露出苦笑,幾次欲言又止。
“我來(lái),原本只是想向她借錢。”馬尚說(shuō)。
“我設(shè)想了很多種可能,”唐森沒(méi)有掩飾自嘲又嘲弄的語(yǔ)氣,“唯獨(dú)沒(méi)想到是這樣。”
這樣說(shuō)并沒(méi)什么,馬尚安慰自己。懷念她,會(huì)成為以后生活中再也無(wú)法清除的情感,會(huì)成為我的生活本身。他不需要也不應(yīng)該在這一刻坦白,哪怕痛苦的悸動(dòng)已讓他無(wú)法安坐。
唐森起身走向角落,在一堆雜物中翻撿著,然后又慢慢走回馬尚身邊,遞過(guò)來(lái)一張銀行卡片。“我還剩下一點(diǎn)錢,但不想借給你。這是她的,算是遺產(chǎn),這意義不一樣,我想我這么說(shuō)你能明白。”唐森說(shuō)出密碼,馬尚跟著默念了一遍,確定那六個(gè)數(shù)字和自己沒(méi)有任何關(guān)系。馬尚接過(guò)來(lái),沒(méi)有回答唐森的問(wèn)題,甚至也沒(méi)有說(shuō)謝謝。這也沒(méi)什么不可以,曾經(jīng)的愛(ài)情——它的遺產(chǎn),再次解救了當(dāng)下的困窘。
“明天她下葬。如果可以,我想留你在這住一夜。”唐森說(shuō)。
“不了。”馬尚說(shuō)。他和這個(gè)新喪妻子的男人,他們都還有很多問(wèn)題需要解決,但只能各自解決。事情不能再?gòu)?fù)雜下去了。而且,生活中的很多問(wèn)題,它們的使命只是作為問(wèn)題來(lái)到你的生命中,無(wú)法解決,也無(wú)須解決。他還記得,多年前,在突然消失的前一夜,林谷評(píng)價(jià)他們的關(guān)系時(shí)曾經(jīng)這樣說(shuō)過(guò)。
“我還有個(gè)請(qǐng)求。對(duì)不起,能不能讓你的司機(jī)送我去車站。”馬尚聲音里透著害怕遭到拒絕的焦灼和不安。我兒子一個(gè)人在家,必須連夜趕回去,他說(shu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