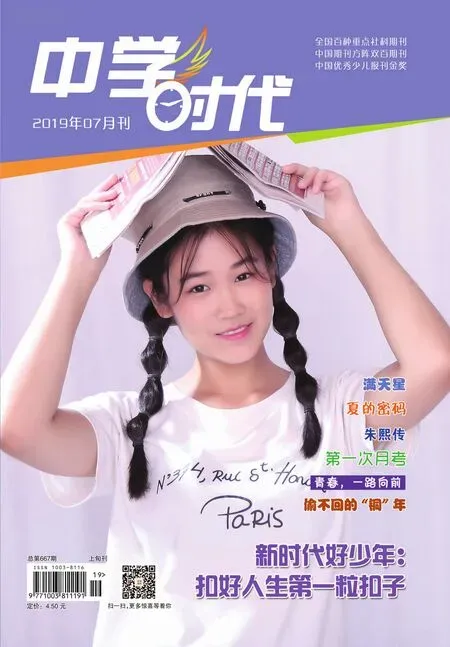創(chuàng)意寫作之第五講:細(xì)節(jié)
■凌鼎年
這一講要談“細(xì)節(jié)”,《后漢書·班超傳》有云:“為人有大志,不修細(xì)節(jié)。”這可能是“細(xì)節(jié)”一詞的原始出處。這說明,我國(guó)的古代文人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注意到細(xì)節(jié)這個(gè)問題了。
何謂“細(xì)節(jié)”呢?從字面上解釋,細(xì),就是細(xì)小的、細(xì)微的;節(jié),是一個(gè)最基本的長(zhǎng)度單位,指很短的一段,或者可以理解為主干以外的枝杈。在語言專家眼里,“細(xì)節(jié)”正規(guī)的說法是:(1)不容易起眼的小環(huán)節(jié)、小事;(2)文藝作品中描繪人物性格、事件發(fā)展、自然景物、社會(huì)環(huán)境等最小的組成單位。
我的理解,細(xì)節(jié)就是生活中的某件小事,相對(duì)獨(dú)立的一個(gè)小片段,不一定有完整的故事,也不一定有很個(gè)性很典型的人物,但確確實(shí)實(shí)是來自日常生活,屬原生態(tài)的東西。記得我有次講課時(shí)談道,故事可以編排,情節(jié)可以虛構(gòu),細(xì)節(jié)必須真實(shí)。創(chuàng)作中有編故事的說法,聽說過編細(xì)節(jié)嗎?
我曾經(jīng)聽到一個(gè)文壇小故事,說有位大刊物的主編去一位著名作家的家里約稿。作家說:你給我兩個(gè)細(xì)節(jié),我還你一篇作品。
真不愧是大作家,他深知細(xì)節(jié)的重要性。有了真實(shí)的、典型的、有價(jià)值的細(xì)節(jié),故事就好編了。
說來說去還是局限于理論層面,我來舉個(gè)例子,看看能不能說明細(xì)節(jié)究竟是怎么回事。譬如有個(gè)人的常見動(dòng)作是雙手交叉放在前腹部,在一般人眼里,最多認(rèn)為這人有點(diǎn)架子,擺出個(gè)干部的樣子,但到了作家眼里,這就是細(xì)節(jié)。有位作家在描寫一個(gè)非正面人物時(shí),就用了這個(gè)細(xì)節(jié),在他筆下,那個(gè)人時(shí)不時(shí)雙手交叉放在前腹部,好像護(hù)著滿肚子的壞水……僅這一個(gè)細(xì)節(jié),就把一個(gè)人物寫得令讀者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