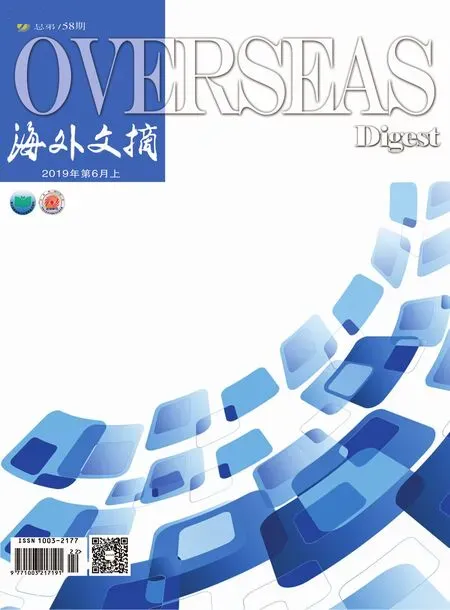從龍貴戚:宋初駙馬都尉
劉佳偉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開封 475001)
北宋前兩朝駙馬都尉的政治參與度較高,既領兵出征,又擔任地方州軍長官,為宋初國家維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學界大多將駙馬都尉的研究,多認為其“崇爵厚祿,不畀事權”,沒有對宋初駙馬都尉予以公允的評價。筆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分別對宋初駙馬都尉參與軍事活動、地方治理、中央政治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特點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1 宋初駙馬都尉參與軍事
宋朝一共有三十位駙馬都尉。宋初包括八位,即尚宋太祖妹妹秦國大長公主的高懷德,尚宋太祖女兒魏國大長公主的王承衍、尚魯國大長公主的石保吉、尚陳國大長公主的魏咸信,尚宋太宗女兒徐國大長公主的吳元扆、尚揚國大長公主的柴宗慶、尚雍國大長公主的王貽永、尚衛國大長公主的李遵勖。其中以駙馬都尉身份領兵作戰者四人,即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和吳元扆。宋朝第一位駙馬都尉高懷德在選尚宋太祖妹燕國長公主之后,就不再領兵出征,并在建隆二年(961)的“杯酒釋兵權”中被徹底解除了兵權“殿前副都點檢、忠武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
宋朝在收復幽云十六州計劃破產后,對遼策略也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御。遼軍乘勝追擊,并于遼圣宗統和四年(986)十一月舉兵南侵,蕭太后“親閱輜重兵甲”并以“以休哥為先鋒都統”。耶律休哥率領數萬鐵騎南下,遼軍在望都(今河北保定)大敗宋軍,隨后破劉廷讓于君子館(今河北河間),降邢州(今河北邢臺)拔衛州(今河南衛輝)氣勢如虹。宋太宗立刻做出反應,積極防御,同時開始重用駙馬都尉。宋太宗于雍熙三年(986)十二月下詔:“以彰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威塞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知孟州(今河南孟州),慎州觀察使、駙馬都尉魏咸信知澶州(今河南濮陽),愛州團練使、駙馬都尉吳元扆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在此危急時刻,任用駙馬都尉領兵作戰和出守重鎮,顯然是看中他們背后家族勢力對穩定局勢的重要性。宋初的駙馬都尉也不負眾望,在保衛疆土方面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
王承衍是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的長子,雍熙三年被任命為知大名兼天雄軍(今河北大名)都部署。自唐、五代以來天雄軍的戰略地位就非常重要,是開封的屏障,“慶歷二年(1042),升天雄軍為北京”。宋太宗令王承衍鎮守大名,可見對其的信任。王承衍上任一個月后的上元節,遼軍來犯“寇鎮陽,候騎至冀州,去魏二百余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獨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游宴,達旦,人賴以安。”王承衍用安然自若的表現,悄無聲息地平定了一觸即發的騷亂,從此也可看出其膽識過人。雍熙四年(987)宋太宗詔回邊將,授于《平戎萬全陣圖》“潘美、田重進、崔翰、王承衍等入隊,并召在京掌兵將帥,訪以備邊之策,帝又親為規制,為此圖以示之”。王承衍鎮守地方不僅受到宋太宗的賞識,還得到當地百姓的擁戴,“端拱初,換永清軍節度,再知天雄軍。吏民千余詣監軍,請為本道節帥,詔褒之”。王承衍在雍熙防御戰中表現出色,受到宋太宗的認可。但王承衍作為宋太祖系的駙馬都尉可以被委以重任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相關。
石保吉是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的次子,也是宋代駙馬都尉中軍功最卓著的一位,“保吉、承衍咸以帝婿致位藩鎮,其被驅策、著戎功,則保吉為優。”石保吉受到重用開始于雍熙三年鎮守河陽。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巡視河北時,石保吉被任命為行營先鋒都部署,已成為宋真宗的左膀右臂。咸平六年(1003)遼軍南下,宋真宗日夜訪求御敵之策,并制定作戰計劃。前線以定州為中心展開防御,后方則由石保吉率領重兵屯戍天雄軍,以屏京師。景德元年(1004)冬,宋遼對持于澶州,遼軍數十萬向澶州北城攻來,石保吉時任駕前西面排陣使,“保吉不介馬當其前鋒,虜甚畏憚。駕至衛南,師已告捷。及振旅舍爵策勛,特加戶邑”并用強弩擊殺遼朝的順國王蕭撻覽,一戰成名。石保吉在澶州之戰中大放異彩,促進宋遼澶淵之盟的簽訂,對于促成宋遼百年和平貢獻巨大。
魏咸信是樞密使魏仁浦的繼子。雍熙三年魏咸信出守澶州“澶淵要區,喉咽之地,慎擇能臣,無易公者,遂命公往撫之,賜白金五千兩。”咸平二年宋真宗北巡時,任命駙馬都尉魏咸信為貝冀路都部署,“時方鎮各控重兵以自衛,公至天雄軍,始得步騎二千以隨。勁敵之壘,煙火相望。公左實右偽,虛振軍聲,倍道兼行,直抵邊郡。敵亦憚公威名,辟易而退。”澶州之戰后契丹請和,宋真宗宴請功臣“面賞繼隆、保吉,咸信避席,自愧無功,上笑而撫慰之”。除此之外魏咸信在軍事上的建樹不多。以筆者之見,可能與其父為前朝遺老有關。
吳元扆為永興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的四子。雍熙三年出守鄆州。咸平三年(1000)“王超、王繼忠領兵逾唐河,與遼人戰,元扆度其必敗,乃急發州兵護河橋。既而超輩果敗,遼人乘之,至橋,見陣兵甚盛,遂引去”吳元扆準確地判斷出這場戰斗的結果,提前做好準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損失。景德四年(1007)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扆請求邊任。宋真宗對知樞密院王欽若說:“元扆繼守藩郡,御眾撫俗,頗著聲績,今已分并(今山西太原)、代(今山西代縣)禁軍屯澤(今山西晉城)、潞(今山西長治),可因以任之。”于是下詔令吳元扆知潞州。并委任吳元扆掌管澤、潞、晉(今河北石家莊)、絳(今山西新絳)、慈(今河北磁縣)、隰(今山西隰縣)、威勝(今山西沁縣)七州軍戎籍。
前四位駙馬都尉都領兵作戰的經歷,但前兩位駙馬都尉的軍功明顯超越了后兩位。其他三位駙馬都尉柴宗慶、王貽永和李遵勖則不再領出作戰。柴宗慶曾經向宋真宗請求邊任,宋真宗拒絕并解釋道:“宗慶未嘗更事,豈堪此選。卿等可召至中書,諭以疆埸無虞,恐動人情,故不許也。”王貽永雖不在領兵出征,但入主樞府“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李遵勖在判許州時,轉運使挑選士兵用來補充水兵,不考慮是否識水性,就強制調集。李遵勖反對:“強人以不能,將何用!”考察士兵的水性后,淘汰了十之七八。宋初駙馬都尉大體上呈現出,軍事參與度降低的趨勢。
2 宋初駙馬都尉參與地方治理
宋初駙馬都尉不僅在軍事上活動頻繁,也積極地參與地方治理。王承衍和石保吉的政治生活主要集中在軍旅上,參與地方治理的功績較少。魏咸信和吳元扆的政治生活既有軍旅也有地方治理,但以后者為主。柴宗慶、王貽永和李遵勖不再直接擔任帶兵將領的職務,轉向擔任地方長官。
鎮安節度使石保吉從治所歸朝,請求奉朝請“陳州民列上其政績,乞許復還本鎮。己未,詔獎保吉,仍可其奏。”可見石保吉在地方治理方面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魏咸信對澶州的水患治理和農業恢復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一雍熙三年冬,鎮守澶州時發現“河水湍悍,舊堤回曲,備御告勞,科率為患,乃徑鑿新渠二十里,以直水勢,繇是十馀年間無衍溢之患”。魏咸信對澶州水利的治理保護了百姓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淳化四年(993)九月,“澶州河水暴漲,夜沖北城,壞居人廬舍及州宇倉庫”。宋太宗任命魏咸信知澶州進行治理。最初,宋太宗派遣內殿崇班閻承翰去治理水患,后又選派魏咸信前去協助。閻承翰認為正值隆冬,兩岸冰錐堆積如山,況且水勢洶涌,不是治理的最佳時期,于是自己返京向宋太宗建議來年春天再做打算。魏咸信趁著閻承翰回去之際,自己做主“鳩集諸工,自乘小舸,截巨浪,排層冰,紼纚造舟,是日亟就”成功的解決了水患。魏咸信做事果斷,有勇有謀,同時反應出宋太宗識人頗佳。淳化四年冬,“時都大提點河堤崇儀使劉永恭大庀役徒,修筑堤塞,盛寒皸瘃,人皆苦之。”魏咸信體諒百姓上奏此事,言明利害,請求延至明年春初再修堤壩。宋太宗深表認同,決定暫緩動工。淳化五年(995)春,魏咸信親自帶領役夫二萬修筑堤壩完成工程,并減省頗多。其二,澶州水災消退之后,留下了肥沃的淤土。但百姓并沒有種子去耕種,只能相聚在一起感嘆發愁,討論著如何流亡。魏咸信看到這種情況后立刻上奏申請撥糧“公奏貸麥數萬斛,是夏大稔,民樂輸還官,襁屬不絕。由是人皆處業,貧者更富。”此舉不僅穩定民心,恢復農業生產,而且減少流民,降低這場水災對國家的危害。
吳元扆在地方的政績同樣出色。淳化五年,當時吳元扆知河陽,秋雨連綿,“嘗值河溢,城將壞,躬涉泥濘,督工壅塞。民有避水于林杪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溺。”吳元扆有勇有謀,身先士卒,又散家財以穩定民心,才使得此場天災得以安然度過。吳元扆不僅在河陽留下功績,而且在澶州和定州也做出了貢獻。咸平三年知澶州時“轉運使劉錫上其治狀,詔書嘉獎,遷寧國軍留后、知定州”,知定州任期滿之后,吏民到開封貢馬以求其可以留任“考滿,吏民詣闕貢馬,疏其善政十事,愿借留樹碑,表其德政。詔褒之”。吳元扆受到當地吏民的擁戴,也得到宋真宗的認可“深所嘉嘆,于帝婿中獨稱其賢”。
王貽永和李遵勖在地方任職之時,也為當地做出了貢獻。天禧三年(1019),王貽永知徐州“河決滑州(今河南滑縣),徐大水,貽永作堤城南以御之”。當時水勢浩大,為患三十二州縣,而王貽永及時的筑堤防水,使得徐州沒有受到水災。王貽永知鄆州時,“州自咸平中徙城,而故治為通衢,介梁山,春夏多水患,貽永相度地勢,為筑東西道三十余里,民便之”。修筑道路,減少水患,不僅保護了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而且保證通商道路的安全,促進商業發展。李遵勖同樣很愛惜民力,判許州時,“民方輸租,倉官不時至,遵勖馳往受所輸,倉官惶恐叩頭,民大悅”。
在肯定駙馬都尉地方治理功績的同時,也不可忽略他們的過失。駙馬都尉柴宗慶就因在鎮多次遣其部屬擾民而被彈劾。景祐四年(1037)陜西轉運使段少連彈劾駙馬都尉、知陜州(今河南三門峽)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康定元年(1040),詔:“判鄭州、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柴宗慶還朝,歲減公用錢四百萬,部使者言宗慶貪刻,且縱其下擾民也。”因柴宗慶多次遣部屬擾民,當再次被外任為官時就遭到了御史的強烈反對“駙馬都尉柴宗慶前在鄭州縱其下擾民,及遣使問狀,而托疾不即應,更請出為郡。公(賈昌朝)劾奏宗慶托國肺腑而所為不法,乃復使為群,恐益為民患”,于是免除了柴宗慶的外任。
3 駙馬都尉參與中央政治
宋初駙馬都尉晉升為使相并非一帆風順,基本都會遭到大臣的反對。景德元年,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曾求賞賜宰相封號。宋真宗詢問宰相李沆的意見,李沆就明確反對:“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據臺席,恐騰物議。”之后,宋真宗又數次想要封石保吉使相,都因李沆的反對而不成。直到李沆去世,石保吉又屢立戰功,才被拜為使相。大中祥符七年(1014)宋真宗“以新建南京,獎太祖舊臣,加同平章事”,此時忠武軍節度使、駙馬都尉魏咸信已年老昏花。天圣四年(1026)柴宗慶請求被賜使相。宋仁宗詢問輔政大臣的意見,王曾回答:“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且將相之任,豈容私請。”直到幾年后王曾外任時,柴宗慶才被拜為使相。
駙馬都尉王貽永在樞密執政十五年,其間中規中矩,受到當時和后世士大夫階層的贊賞,“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為聲伎之樂。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迄無過失,人稱其謙靜。慶歷間,貽永位冠西府”。駙馬都尉李遵勖在天圣末年,時常到宮殿中密奏時事,論及朝政。劉太后問起最近外朝有何言論?李遵勖回答:“臣無他聞,但議者謂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李遵勖對宮廷內外的消息靈通,了如指掌。劉太后去世后,就秘密上奏:“后乳母晉國夫人林氏前多干預國事,中外病之,宜居之別院,限其進見,以厭眾論。”幫助宋仁宗打壓了劉太后的殘余勢力。
4 駙馬都尉參與政治的特點
宋初駙馬都尉在政治、軍事和地方治理方面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并非是“崇爵厚祿,不畀事權”。但宋初任命駙馬都尉擔任實職差遣卻包含著深層的政治博弈。
宋太祖的三位駙馬都尉王承衍、石保吉和魏咸信在宋太宗組織的第一次北伐失利后沒有得到領兵的機會,而在第二次北伐失敗后得到了領兵鎮守的重任。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親征太原,并于五月占領,隨即揮師幽云。宋太宗戰敗,丟下大軍倉促而逃,“敵人追之僅得脫。……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宋太宗不知所蹤,前線將士發生嘩變欲立宋太祖長子趙德昭為皇帝,“魏王德昭,太祖之長子。從太宗征幽州,軍中夜驚,不知上所在,眾議有謀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銜之,不言”。而駙馬都尉石保吉的父親石守信也因此次事件而受到責罰。以不正常手段即位的宋太宗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宋太宗明白對他皇位的最大威脅不在外部而在內部,開始削弱支持宋太祖之子趙德昭和趙德芳的勢力。此時作為宋太祖的三個駙馬都尉不能受到重用自然不難理解。天平興國四年,趙德昭被迫自殺;天平興國六年(981)二十三歲的趙德芳暴卒;雍熙元年(984)三十八歲的趙廷美因病而卒。宋太宗第二次北伐時,皇位有最大威脅的三個人都已不存在。此三人的先后亡故,宋太宗開始放松了對宋太祖系的警惕,并重用宋太祖的駙馬都尉,給予恩賜,安撫人心。
宋初的七位駙馬都尉可分為“將二代”和“將三代”。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和吳元扆都是開國元勛之子,而柴宗慶、王貽永和李遵勖則為開國元勛之孫。“將二代”在雍熙北伐失敗之后的防御戰中開始領兵,而“將三代”則沒有領兵的經歷。原因之一在于軍中威望不同。雍熙北伐失敗后,面對遼國數十萬鐵騎的反撲,此時宋太宗任命此前并無領兵經驗的“將二代”駙馬都尉帶兵鎮守要地。危急時刻宋太宗如此用人,可能一是利用“將二代”駙馬都尉的軍事家族背景以安軍心,二是利用其安撫宋太祖系勢力。“將三代”駙馬都尉在軍中的威望則不如“將二代”駙馬都尉。原因之二生活環境和個人能力不同。“將二代”的駙馬都尉從小生長在軍中并跟隨父親出征作戰,有一定的作戰經驗,如王承衍一直在父親王審琦軍中擔任牙署。而“將三代”駙馬都尉生長在安逸的開封城內。生活環境導致他們的軍事能力和威望的不同。
宋初駙馬都尉被委以重任是宋太宗鞏固皇權的巧妙手段。宋初駙馬都尉的父輩或祖輩都是權力中心的重要人物。“將二代”駙馬都尉已經從權力中心轉到軍事,而這個軍事權力遠不能與父輩相比。“將三代”駙馬都尉從軍事轉向了地方政治。宋仁宗之后的駙馬都尉更是幾乎不再擔任差遣,和宗室一樣成為統治階層的政治花瓶。從駙馬督尉家族權力重心的轉變可以管窺到其他開國武將家族的勢力轉移。
注釋
①汪允普.《北宋駙馬群體研究》北京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主要從駙馬都尉的出身、政治情況以及尚主后對其家人的影響三方面展開論述;王曉晴:《唐宋公主婚姻生活研究》遼寧大學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論述了宋朝駙馬都尉出身家族變化,即由“重臣勛貴之后”轉變為“武將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