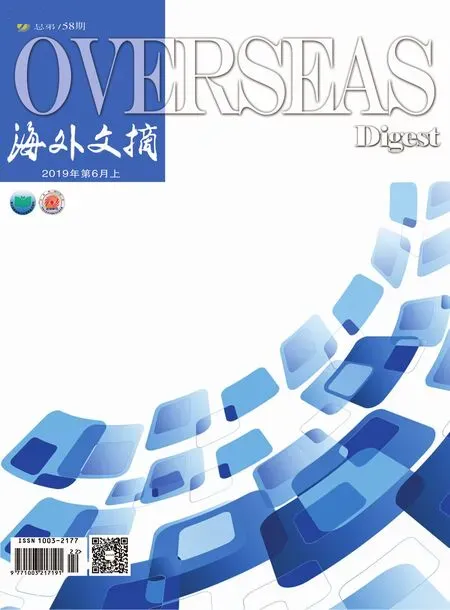小議商周時期人類活動與犀牛、大象的遷移
盧允雷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開封 475001)
自然環境對生物的生存影響很大,特別是氣候的變化極大地限制著物種的數量和分布。在特定的時空下,氣候環境發生大的波動,是造成物種減少和遷移的原因之一,但是氣溫回暖以后,卻發現大型物種的數量不增反減,究其原因這和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有關。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暖濕潤,這一區域生活著一部分現在只能在熱帶、亞熱帶看到的物種,如犀牛、大象、野牛、竹鼠等。公元前1100年左右氣候轉冷,并持續一兩個世紀,隨后氣候恢復并延續至西漢末。但這一區域至戰國后期已經很少看到犀牛、大象的蹤跡,靠南的淮河流域依然有它們活動的身影。閱讀歷史文獻發現黃河中下游地區,在這一時期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頻繁,改造自然地能力加強,加劇了大型動物向南遷移的速度。
學界對商周時期動物變遷的研究,成果頗豐。章鴻釗所撰的《中國北方有史后無犀象考》,是比較早研究動物地理的先驅和著作。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論證了商周時期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存在犀牛和大象的事實。文煥然、何業恒等對商周時期,野象的分布和變遷進行了系統的探討,在他們論述中不僅指出氣候變化是黃河流域(特指黃河下游地區平原)犀牛、大象滅絕的根本原因,并且認為是人類活動導致了大型動物的遷移甚至滅絕,論述精辟,但是他們并沒有詳細地分析是哪些人類活動對生態平衡帶來了破壞。李翼《先秦動物地理問題探索》一文,介紹了先秦分布在北方地區的大象、犀牛等其他動物種類。但作者主要是闡釋犀牛、大象等其他動物的地理分布,雖也涉及它們遷移的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特別指出人類活動是這一時期導致大型動物遷移的主導原因,但并沒有詳細分析人為因素造成的影響。筆者擬從商周書寫材料、戰爭、宮殿建材、農業開墾等多方面進行分析,論述商周時期人類活動對大型動物遷移的影響。
1 自然環境是生存基礎
在論述人類活動之前,有必要闡述一下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自然環境,主要是闡述這一時期的氣候環境,這是承載生物活動的物質基礎,沒有這一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其他無從談起。
根據考古發掘,文獻記載,包括C14和孢粉分析法以及甲骨文等材料和技術的運用,學界普遍認為商朝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為溫暖濕潤的氣候,正月的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3-5℃,“與今長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當”,當時這一區域有大量生活在現在亞熱帶和熱帶的動物。西周初期依然是溫暖濕潤的氣候,但是不久氣候轉冷,氣溫有所下降并持續一兩個世紀后再次轉暖。春秋戰國時期是溫暖期,氣溫較現在高1.5℃,這種現象延續至西漢末年。由于先秦時期很長一段時間內黃河流域都是溫暖濕潤的氣候,所以在這一時期內黃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區,草木旺盛,森林茂密。“當時全國森林覆蓋率在49.6%,南方的森林覆蓋率在90%以上”,由此不難看出這一區域的植被很多,為大型動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商代和西周中前期,殷墟一帶有森林、草原、沼澤存在。野生犀牛的分布、變遷與野生大象的情況大同小異,北界達到今河南安陽,在整個南遷的過程中,雖然有短暫的北歸,但是最終在黃河流域銷聲匿跡。歷史時期安陽出現的還有熊、貘、獐、圣水牛、猴、竹鼠等其他哺乳動物群,殷墟出土大量的犀牛甲骨,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安陽一帶的生態良好。春秋時代華北平原已經出現開墾植被地帶,進行耕種現象,但是并不明顯。戰國時期,鐵農具開始大量使用,生態景觀(森林、草原、沼澤)遭到了破壞,大型的動物逐漸消失在這一區域。
2 商周時期書寫材料帶來的消耗
商、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的書寫材料是甲骨、銘文,以及到后來的竹簡。甲骨主要是商時期用來記載卜卦的載體,是由龜甲和獸骨組成。商早期使用龜甲較少,商后期甲骨并用,而獸骨又以牛肩胛骨最多,也有部分羊、鹿等肩胛骨參用。對于甲骨文出土數量,河南安陽殷墟一地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甲骨就有十五萬片之多,其中用龜數量為16000多只,而用牛的數量是5000頭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殷商時期記載卜辭的獸骨對于牛肩胛骨的耗量來說很大,雖然這些牛肩胛骨的取材一部分來源于家養,但是很大一部分是來源于野生牛,包括犀牛和圣水牛,這就直接造成了犀牛數量的減少。
商周時期,青銅器開始出現,到西周中后時期青銅器冶煉技術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西周青銅禮器發生了顯著變化,銘文大量增加,加之周王以青銅器作為對大臣的賞賜,周人對青銅器更加重視。然而青銅器的增多,需要大量冶煉青銅器的原材料,包括銅礦的開采,冶煉需要的熱量供應。對于銅料產地,“這一時期商周王朝的銅料主要可能來自中原的中條山銅礦區”,山林遭到開發,而對于冶煉需要的熱量供應,是木材,而非煤炭,所以大量的木材被砍伐,這就嚴重影響了植被的覆蓋率,從而間接的影響了動物的棲息地,讓大型動物無處覓食,無處藏身,生存環境遭到破壞。高大植被的破壞,大型動物不易遮蔽隱藏,容易受到攻擊。西周以后關于黃河流域殷墟附近的犀牛、大象的文獻記載就很少看到了。而淮河和長江流域或者更南的區域,由于開發程度較低,成為犀牛和大象的主要生存場地。
春秋戰國時期竹簡開始做為主要的書寫材料,到秦漢時期竹子的砍伐,造成了大量竹林以及其他植被的消失,導致了食草動物的食物匱乏,從而影響生物鏈上的其他動物的生存。春秋戰國時期鐵器已經出現并得到大量的運用,至戰國時期,河南中東部地區已經沒有高大植被了,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的生物棲息地被破壞已盡。這一時期包括水牛和竹鼠等許多動物已經向南遷移,到達淮河長江流域。公元前900-公元前200年期間,犀牛分布北界曾在秦嶺淮河一線南北變遷。
3 戰爭和宮殿建設壓縮生存空間
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這里土壤肥沃,又是平原地區,便于耕作,先人很早便在此繁衍生息。夏、商、周三代都曾在這一塊土地上建都設置,文化、政治、經濟發達,聚集了很多人口。正因為如此,這里也成為爆發戰爭最多的地方,收錄在《甲骨文合集》中的商代后期甲骨文卜辭,有關戰爭的記載不下萬余條。戰爭,無論是局部性質的還是全國范圍內的,都是對人力、財力、物力的一種消耗,況且勢必會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無論是換代之際的持久戰爭,還是大動蕩期間的多國混戰,天下蒼生必然會受到影響。例如商周換代之際牧野之戰,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戰都對植被、土壤、河流等山川形便造成很大的影響。
商朝前期遷都頻繁,盤庚遷都殷以后,直至武王伐紂這一段時期內商都比較穩定。周興于關中,在討伐殷商時,必然會做好出兵的各項準備,包括兵士武器,糧草,還有戰爭路線的選擇,戰爭場地的空間選擇。制造武器自然以青銅金屬為主,商末關中姬氏控制的手工業,工程齊全,有金、木、皮、毛、磨等工種,這些工種所從事的工作雖然服務于戰事,但可以看出,所有選材都是直接從自然環境里取得。這時的作戰方式出現了戰車和步兵的配合,而戰車的制造需要大量的木材原料,毋庸置疑這些木材也會開采于就近的森林。況且一般戰車的配置不僅需要挽馬四匹,還需要甲士三人。而戰士在戰場上為防護自身安全,需要甲胄進行保護。而甲胄生產的原料又多以犀牛皮為主,原因是因為犀牛皮厚且硬。“又硬又厚的皮膚類似甲胄,在肩甲、頸下即四肢關節處有寬大的褶縫,以保持活動的靈活性”。與諸侯會師牧野前,周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而會師商郊牧野時,“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戰車數量明顯增加。商王問訊,發兵七十萬人來抵抗。由此可見牧野之戰所需戰車、甲士數量之多,不得不令人思考這些裝備的材料來源問題。顯然甲胄的制作來源犀牛皮(也有可能來源于其它大型動物的皮毛),這樣直接造成犀牛的死亡,犀牛為了生存必然會逃離。另外,對于當時進攻路線的選擇,戰爭場地的選擇都會影響植被的覆蓋。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之間長期的爭霸戰爭,包括東西之戰,南北之爭非常頻繁,僅春秋時期諸侯間的征伐就約有380余次,對自然環境破壞非常嚴重,至戰國時期,戰爭更加頻繁,戰爭規模擴大,森林、草地被破壞,并無法恢復。這一時期,由于各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使交通道路得以開辟,而這些縱橫交錯的道路很容易導致大型動物生存空間的破碎化,使大型動物正常的種群規模難以維持。隨著西周的東伐,再加上春秋戰國時期的動亂,成為這一時期大型野生動物向南遷移的重要階段。一段時期內,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現過短暫的大型動物北返景象,但是北歸之路被縱橫交錯的阡陌阻斷,當然還有農業的墾荒,貴族的狩獵等也是阻斷大型動物北回的人為原因。
商王、周王的宮殿和都城的修建,以及春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國的宮殿建設等,金碧輝煌,氣勢恢宏,建筑用材消耗巨大。位于今天的翼、魯、豫三省交界的東部地區,在公元前2世紀時已經大量缺乏薪材。宮廷建筑的用材,直接對森林造成了毀壞,動物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迫于人類活動的擠壓,動物在黃河中下游平原生存空間嚴重萎縮,而南方氣候溫暖濕潤,植被茂盛,符合動物的生存要求,動物被迫南遷。
4 農業和象文化迫使動物逃生
如果要問哪一種人類活動對動物生存空間造成的擠壓最為嚴重,毫無疑問的回答就是農業活動,特別是毀林開荒,圍湖造田。韓茂莉從農業活動對自然環境帶來的影響論述,“農業耕作的對象根植在大地上,農田與農作物每前進一步均會侵奪天然植被,毫無疑問農田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天然植被退卻、消失,也同時介入對于自然環境的改造”。黃河中下游平原地區有黃河沖積的沃土,氣候溫和,地勢平坦,易于耕種,開發較早,成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而夏、商、周分別在河東、河內、河南即三河地帶建都,所以三河地帶成為中國歷史上開發最早的農耕區。但是這一時期由于耕作技術、耕作農具的落后,致使農業只在河谷地帶發展,耕作范圍不大,況且主要分布在城邑附近。春秋戰國時期,列國混戰,大肆掠奪人口和土地。伴隨著這一時期鐵器的使用,牛耕的出現,使得私有土地創造了大量的財富。井田制逐漸瓦解,各諸侯又頒布了許多有利于開墾土地的政策,由于戰爭的需要,人口數量的增加,需要的土地越來越多,導致了大量的土地被開墾,從而種類不多的農作物取而代之多樣性的天然植被,大型動物的生存空間和食物鏈受到威脅,間接的影響其生存。農田的大量開墾,逐漸成片,也阻斷了大型動物的回歸之路。
出土的商周青銅器上有許多生動的大象形象,另有商周青銅象尊出土,這表明商周時期的象文化在上層社會比較盛行。商周時期象文化的發展也是造成犀牛和大象等動物遷移的原因之一。先秦時期,以金、玉、銀、犀、象等為珍貴物品,商代晚期的“婦好”墓出土了精美的象牙觚、杯,象牙還用于朝笏。這一時期的犀角,象牙手工品已經比較流行,但是比較缺少,而為了滿足貴族的需求,就有一些人在利益的驅逐下獲得這些物品,贈予貴族,滿足他們奢侈的消費行為。由此以來,野生大象因其牙,犀牛因為犀角和毛皮而遭殺戮。
5 貴族狩獵
對動物的捕殺是造成動物數量銳減的直接原因,也是動物為了躲避、遷移的直接原因。商周貴族對動物的狩獵最為嚴重,同時捕殺數量最多。其次是山民為了生存對動物進行的捕殺,這也造成了大型動物數量的減少。
甲骨文中對于獵獲犀牛多有記載,在殷都及其以南的太行山南麓等地“獲兕(犀牛)”或“擒兕”的記載有多次,甚至有“獲白兕”的記載。“而獵獲的數量也較象為多,有多達十幾頭的”,但是隨著卜辭的繼續出土,這一數量有些保守。陳夢家研究發現,甲骨文中記載獵獲100頭以上的動物中就有兕。西周武王伐紂時期,又有記載“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即周王室對野生動物進行直接驅離。而對于世世代代生活在深山老林的山民而言,在沒有鐵器以前,對于犀牛和大象的直接傷害是比較小的,但是他們靠山吃山,不影響他們對其它動物帶來的毀滅,這樣也導致了動物的逃生;鐵器廣泛運用以后,迫害程度加深,迫害范圍變廣。正是人為活動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動物生存棲息地無法庇護其安全,因而它們逃竄躲避或者遷移,而南方的氣候溫暖濕潤,有大量的高大植被,適合它們繁衍生存。
6 結語
商周時期動物南遷的原因總的來說有三種:一是自然環境自身的變化;二是人類改造自然的活動;三是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合力帶來的環境惡化,而后兩種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起著直接作用。
商至戰國,黃河中下游地區氣溫變化不穩定,而且氣候變化持續時間長。公元前1100年左右,氣溫降到了歷史時期的一個冰點,這是近5000年來第一個低溫期,這個低溫期持續一兩個世紀,后來氣溫轉暖。但那些喜暖、濕潤的生物受到影響,導致他們朝著適宜生存的地方逃竄。但是當這一區域氣溫轉暖后有一部分動物北歸,而大型動物,如犀牛、大象卻很少。氣溫帶的變化導致植被帶跟隨變化,而植被的變化會直接影響食草動物,這樣食物鏈上的其他動物,也會受到波及。
商周時期,人類活動頻繁,對自然環境改造能力由弱到強。戰爭不斷,且長久,物資所需對自然環境索取太多;宮殿建設對高大樹木地開采也與日俱增;人口的曾加、農田地開墾,損壞了大片的植被,生物棲息空間遭到破壞;再加上貴族對象牙、犀角等奢侈品的追逐,以及大興獵狩,對植被破壞,對動物本身迫害,是黃河中下游大型動物逃竄躲避的人為因素,同時也是阻斷大型動物北歸的主要原因。
自然環境影響人類活動,而人類活動也會反作用于自然環境。人類破壞生態平衡,生態失衡就會改變人類自身的生存環境,相互傷害,在這種惡性循環下,自然環境惡化和人類不合理活動合力,對其它生物造成的迫害不可估量。自然災害和人類活動,使山體、平原、水源發生變化,使地表形態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動物的生存,迫使它們逃生遷移。
綜上可知,商周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大型動物的變遷,特別是犀牛和大象的南移,以及北歸之路的阻斷,既是氣候變化造成的,也是人類活動造成的,而很多時候人為的破壞對動物的遷移負有主要責任。
注釋
①氣候對生物所產生的影響,可參見竺可楨的《氣候與人生及其他生物之關系》,《氣象雜志》,1936年09期,第475-486頁。
②對于出土殷墟甲骨文數量的統計,胡厚宣在他的《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北京:商務印刷館,1951年第1頁,第55頁等都有論及,數量超出十五萬片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