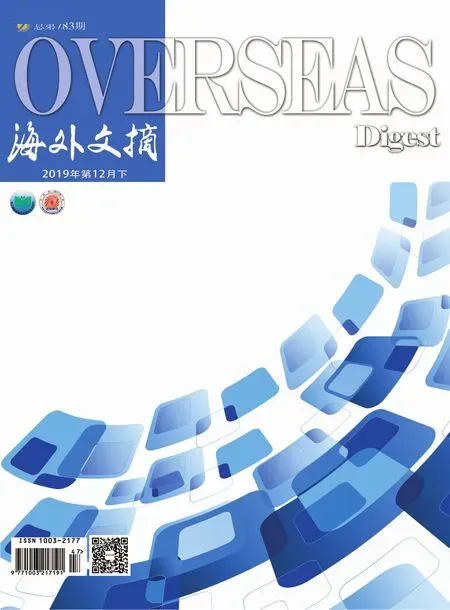多元系統理論視角下的翻譯文學
(西安外國語大學,陜西西安 710128)
0 引言
20世紀70年代在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構主義的理論基礎上以色列學者埃文-佐哈爾(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統理論(polysystem)。佐哈爾在1978年出版的英文論文集《歷史詩學論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首次提出術語“多元系統”(polysystem)。
多元系統理論認為各種符號為媒介的人類交際社會現象,如語言、文學、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不是一個由相互獨立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應是一個系統。并且該系統也是一個由若干不同行為模式,但又相互聯系和影響的子系統組成的多元系統。但是,在這個多元系統中各子系統的地位并不均等,有的位于中心,有的位于邊緣,而且彼此之間存在著持續不斷爭奪中心位置的斗爭。應用于翻譯研究實踐中的多元系統理論指的是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種文學系統的聚合。多元系統理論將翻譯文學視為譯語文學多元系統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子系統,采用描述性歷史性動態的研究范式研究翻譯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在譯語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和作用,分析翻譯文學對譯語文學的影響,從文化層面探究文學翻譯。在這種情況下,翻譯不再被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而是譯入語中一種特殊的政治行為、文化行為、文學行為,而譯本則是譯者在譯入語社會諸多因素作用下的結果。那么多元系統理論到底是如何去定義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系統中的地位和其相應功能的呢?翻譯文學的不同地位又會給譯者、給譯入語文學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呢?這將是本文將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1 概述
1.1 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系統中的位置和功能
將翻譯文學看作一個系統而非僅僅將其看作“翻譯”或者孤立的“翻譯作品”,不限于文本內的研究視角,而結合譯入語國家的文化對翻譯文學進行深入分析,是多元文化理論為翻譯理論研究開拓的嶄新研究領域。佐哈爾指出,翻譯文學不是靜態的系統,翻譯文學在文學的多元系統中不是一直處于邊緣,有時也會位居中心地位,而翻譯文學的地位是由譯語文學多元系統的特征所決定的。
多元系統理論首先描述了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可能會位居中心的三種情況。第一種是,該譯語文學多元系統還沒有成熟,就是說文學的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尚在形成過程中;第二種是某種文學(在與其相關的文學系統中)位于“邊緣”地位,或處在“弱勢”,又或者兩者皆有;第三種是,某種文學出現了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的情況。在這三種情形中,翻譯文學占據了譯入語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此時它積極地參與了多元系統中心的形成過程。這樣的情形下,它本身就成為革新力量的重要的一部分,新的文學形式慢慢定形,翻譯文學推動著建立起新形式庫。國外文學作品的特點(包括原則和元素)被引入國內文學中,并且這些特征又是以前沒有的。這不僅可能包括著用新文學模型取代失效的舊文學模型,同時也包括另外一種文學特征,譬如新的(文學)語言,或者寫作模式和技巧。
第一種情況下某種文學尚還“稚嫩”,需要參考較“成熟”的文學,借用其現成的模型。或者用佐哈爾的話來講就是,“翻譯文學滿足了較為幼嫩的文學的需要……因為幼嫩文學的制造者不可能立即創造出他們所知的所有類型的文本,所以必須借助于其他文學的經驗,于是翻譯文學成為其最重要的系統之一”。中國清末民初時的翻譯文學就與第一種情形相仿:當時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還處于初期階段,“本國作家自己創作的現代意義上的小說還沒有出現,白話詩有待探索,話劇則連影子都沒有”,所以翻譯文學就成為當時新興市民階層最重要的文化來源,“翻譯小說占當時出版發表的小說的五分之四”。國外的芬蘭語文學亦是如此,它于19世紀發展起來,主要是以法國與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為模型。第二種情況下,某種文學系統相對已經確立,但在更大的文學等級體系中處于“邊緣”或“弱勢”,它們可能還“缺少”某種文學體裁,而相關的文學系統中有這類體裁,那么就需要“引進”其欠缺的文學類型。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文學。以色列文學深受德國、俄國以及英美文學的影響,雖然低地國家有其本土文學傳統,但希伯來文化缺少古典文學作品,因此只能完全依賴翻譯文學來獲得文學的多樣性和深刻性。“如果說,荷蘭及比利時學者發現他們自己處于歐洲的十字路口,那么以色列學者則發現他們自己不僅處于蘇聯與西方世界的十字路口,而且處于西方與第三世界文化之間的十字路口”。翻譯對于以色列人非常關鍵。“在整個以色列地區,翻譯不再是精英們的智力游戲,而是最為基礎的文化活動或文化產品,整個地區的生存都依賴它”。第三種情況下某種文學的發展會出現一些轉折點,也就是說“在某一歷史時刻,對于年輕一代而言,現存的文學模式不再站得住腳了”,或者出現文學真空,即“如果某種轉折點導致本土存儲的文學內容不再被接受,出現文學真空的結果”,那么國外的文學模式就會很容易被傳輸進來,翻譯文學就會占據中心位置。以中國“文革”結束后中國的翻譯文學為例。“文革”結束后,之前極左的思想得到糾正,這也反映到文學創作上,文學創作思想出現重大轉變,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出現了轉折點和文學真空。于是當時大批重印“文革”前即已翻譯出版過的外國古典名著,還開始翻譯出版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這剛好符合論證了上述的第三種情況。
除了以上三種情況外翻譯文學在譯入語文學多元系統中位于邊緣地位,即翻譯文學系統成為文學多元系統中的邊緣系統。處于邊緣位置時翻譯文學就不再能對重要的文學發展構成影響,并且翻譯文學會去參照譯語文學系統中的主導類型早已確立的傳統模式。此時,翻譯文學不僅不能成為革新的力量,而是作為保守的元素,迎合譯語文學的傳統規范,維護舊有的文學形式。
佐哈爾指出,如果翻譯文學占據了中心或者邊緣地位,也并不意味著整個翻譯文學的系統都處于這個位置。因為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系統,其本身也是有層次之分。也就是說當某部分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多元系統中位于中心地位的同時,可能另一部分的翻譯文學仍舊位于邊緣位置。通常來自重要源語文學的那部分翻譯文學更有可能取得中心位置。例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希伯來語文學多元系統中,俄語文學的作品占據了中心地位,而英語、德語及其他語言的作品就顯然處于邊緣地位。
1.2 論文學翻譯的充分性
多元系統理論從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中或邊緣或中心的位置這個角度出發嘗試對文學翻譯的“充分性”進行解讀。佐哈爾認為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系統中的位置會對文學作品翻譯的翻譯規范、行為及策略產生很大影響。當翻譯文學在譯語文學多元系統中占據中心地位時,翻譯行為會直接參與創造譯語文學的新文學樣式、新形式庫的內容。這樣譯者能夠更加充分地發揮主觀能動性,“譯者的關注中心就不僅是搜索其本土文學系統中已有的文學模式來翻譯作品文本;恰相反,在這種情形下譯者更愿意去打破、顛覆本土的文學傳統。該條件下,翻譯成為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譯(也即復制原文主要文本關系)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況下更大”。例如20世紀20、30年代魯迅提出要“硬譯”、“寧信而不順”;50、60年代中國把蘇聯文學視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典范,譯者翻譯時小心翼翼,唯恐損害原文。這種直譯或者異化的翻譯策略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文本關系,對原作的解讀也會比較“充分”。同時,原作的文學樣式和特征,即對譯語文學而言是革新力量的元素,就會被最大程度保留和引進,推動譯入語文學新的文學模式的發展。
顯然,當翻譯文學占據譯語文學系統的邊緣位置時,譯者就會傾向于使用譯入語中現有的二級模式對外語文本進行翻譯,將原文套入其中。結果就是譯作較多偏離原作,導致譯作的不“充分性”。美國詩人、翻譯家與評論家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的翻譯實踐常會采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其翻譯的《華夏集》全部譯自中國古詩,但大多數評論家卻視為“一組基于中國素材的英國詩歌,而非翻譯作品”。我們可以分析一下他采取歸化法翻譯策略的文化背景,來探究其做法的根源。20世紀可謂是歐美文學的繁榮時期,西方文化占據世界多元文化系統的中心地位,不言而喻翻譯文學自然位于邊緣位置。多元系統理論論證了龐德在這種文化語境下“采取民族中心主義態度,使外語文本符合譯語文化的價值觀,把原作者帶進譯語文化”的歸化翻譯行為的合理性。
多元系統理論給了我們一個跳出孤立的根據原作和譯作之間的關系評定翻譯的“充分性”的視角。把譯作和譯者的翻譯策略放在歷史文化的大層面去審視。該理論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原著中心論”,將翻譯研究的視角放在譯入語文化里。
2 結語
綜上所述,多元系統理論將翻譯和譯語文化語境、社會條件綜合了起來,突破了靜態孤立地對單個文本進行共時研究的方法,拓寬了翻譯研究的視野,推動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其次,多元系統理論的文化研究視角推動了翻譯研究的范式轉變,即從規約性研究范式轉向描述性研究范式。再者,多元系統理論對翻譯文學與譯語文學的相互作用作了全面的分析,
但是多元系統理論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它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決定性,忽視了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以及譯者的能動性和超前性。又比如像“邊緣”“弱勢”“幼嫩”這些評價性術語的界定就比較模糊。但是如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所言,“(多元系統理論)盡管粗疏,它仍然是極其重要的,關于我們如何書寫文學史,如何描述過去和現在的形成力量,它展現出一種全新的再思考。”這一理論歷久彌新,后來的學者在此理論基礎上的研究更是使之達到新的高度,如圖里(Gideon Toury)的描述性研究的方法論,“操縱”學派中赫曼斯(Theo Hermans)總結的多元系統理論中的制約三要素“意識形態、詩學和贊助人”等等。多元系統理論為翻譯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的發展,在不斷完善的同時也將會繼續在翻譯研究的方法論層面上發揮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