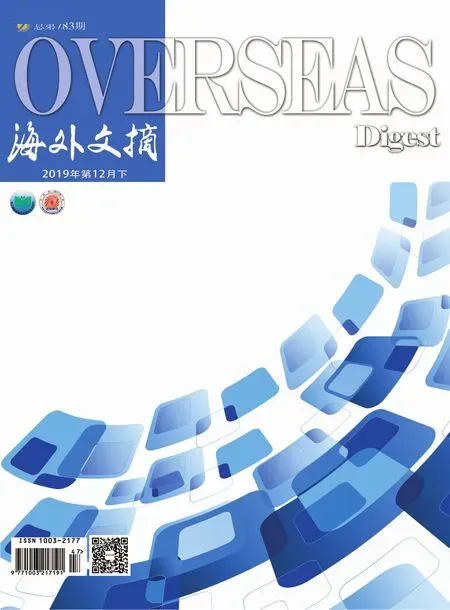邊界的模糊
——淺議小說藝術表現的創新
(河北師范大學 文學院,河北石家莊 050024)
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其創新突出地體現在藝術表現手法上,而其藝術表現上的創新同時也啟發著更深層次的對于藝術邊界問題的思考。五四之后短篇小說這一體裁的結構性變革以及不同文學體裁間的相互滲透現象似乎在無意中提供了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的可能。
1 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結構性變革
五四新文學運動標志著中國文學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激烈轉變,除了最突出的白話語體變革之外,關于文學本體的結構性變革也是不容忽視的一點。就小說這一文學樣式所面臨的變化而言,除了從在古典文學格局中的邊緣性地位漸漸走向新文學格局中的中心地位這樣一種根本性轉變之外,現代短篇小說文體的結構性變革也是其中最為鮮明的轉變。這突出體現了小說文體意識的現代化,一般認為是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所致。中國古典文學敘事傳統注重情節完整,首尾接續的單線敘述模式,而到了五四新文學時期,短篇小說就徹底褪去了中國傳統長篇小說的影子。當然,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早在西學東漸的晚清,雖然壓縮式長篇的縱向結構依舊在小說中占據主導地位,但短篇小說在結構上已經開始出現新變,盡管這種文體意識還沒有形成。一些通俗名家的短篇小說里已經開始出現對新結構的嘗試,如徐卓呆的《入場券》、吳趼人的《查功課》等,他們的短篇小說已經開始具備一種不再重視故事的始終而集中筆墨描畫生活中的某個特定片段場面的傾向。及至五四之后,短篇上新出現的這種結構形態才正式有了系統的理論和創作。在理論的倡導上,不得不提到胡適,他在《論短篇小說》中說到:“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他以西方文學為參照范本,在短篇小說方面推崇都德的《最后一課》和莫泊桑的《斐斐小姐》,認為短篇小說體裁的典型條件應當是“最經濟的手腕”和“最精彩的片段”。自然而然,剪裁與布局就被他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這與他以“經濟”、“效果”作為文學的評價標準不無關系。這種小說結構必然導致對布局的講究。篇幅的縮短,表現內容的增大,勢必使得短篇小說表現密度得到增強。小說的人物、情節和環境之間的張力、聯系更加緊密,克服了以往松散拖沓的弊病,整體更為有機。同樣,沈雁冰也主張過:“短篇小說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來描寫,而人生的全體因之以見。”如此看來,他們主張的短篇小說形態實際是采用共時性角度切入人生來取代傳統的歷時性角度,試圖通過呈現富有意味的空間場景來表現生活整體,體現了屬于空間的,富于暗示的特點。
這種短篇形態具有十分鮮明的現代意識,在當時摹仿借鑒西方成風的思想潮流中,很快就產生了與理論相呼應的作品。京派作家林徽因的短篇小說創作便是成功的范例,她同樣認同“橫截面”的短篇小說觀,但在短篇小說的功能上則認為可以有更大的開拓,需要表現“生活大膽的斷面”。她的《九十九度中》就成功體現了這一點。小說廣泛攝取社會不同階層的生活景象,其中不乏鏡頭組接的蒙太奇手法,并不注重人物的典型塑造,關注的是整個社會圖景的呈現——在華氏九十九度盛夏里北平城內的眾生相。這部短篇擴大了短篇小說的容量和表現功能,使得小說具有極大的“包孕性”。正如李健吾極富眼光的稱贊,“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
2 “包孕性片段”的展現
“包孕性頃刻”一語是萊辛在《拉奧孔》里提出的繪畫表現手法。如果從上述短篇小說產生的新變化上看,不妨將其稱之為對“包孕性片段”進行描寫的現代短篇小說。讀者在較短的篇幅里通過一個片斷便可想象寓于現在的過去和即將發生的未來,從而窺見整個人生。這樣的片斷截取了整個縱向過程中意蘊最為豐富的一個單位,其內部各要素的布局又是復雜交織呈網狀的。作者有時為了達到從此刻表現出過去以及未來種種,又難免會用到各種插敘、倒敘、開放式結尾的手法,激發讀者想象,頗具匠心。胡適也解釋過采用這種經濟的文學手段所產生的“不可增減,不可涂飾,恰到好處”的效果,這都與繪畫中“包孕性頃刻”手法所產生的效果高度吻合。在《拉奧孔》里,萊辛強調了詩與畫這兩種藝術的界限,他表示詩是時間藝術,畫是空間藝術。繪畫在描繪靜態事物方面優于詩,而詩則在敘述動作方面更有優勢。詩和畫各自有著不同的模仿對象和表現手法,界限不可模糊。而具體到藝術實踐上,我們會發現繪畫呈現出的“包孕性頃刻”并不僅限于其自身,在一些文學作品中也可以見出這種手法的影子。在中國新文學短篇小說結構形態的革新上,我們似乎看到了文學與繪畫在藝術表現上的無心契合。同樣可以使人聯想到的是文學與音樂間藝術表現的相通,巴赫金的復調理論恰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藝術價值的出色闡釋。這也啟發了文學在表現手法上的創新探索,即模糊藝術門類的邊界,借鑒文學之外的藝術表現手法,從而取得不一樣的效果。怎樣更加具體地認識詩畫藝術表現的互融性啟發著我們對詩畫界限,甚至是藝術界限更為深入的思考。
不得不面對的就是如何具體地把握各種藝術的邊界這一問題。明確各類藝術間的差異至關重要,只有在明確差異的基礎上,才有資格談論藝術間的相通以及如何融合的問題。在藝術由最初的混沌狀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當其走過了那個需要以明晰差異,劃分邊界來推動自足發展的階段,自然又有向跨越邊界回歸的可能,這并非是種倒退,而是一種螺旋式的上升。萊辛強調藝術門類的界限,而后來的克羅齊和浪漫主義運動的史雷格爾卻強調各門藝術的相互影響和轉化。歷代藝術家都是在遵守界限與打破界限的張力間發展,不可能與歷史的具體情境切斷。自尼采的一聲宣告之后,古典藝術的終結更加使得萊辛的理論在面對眾多現代、后現代藝術實踐時捉襟見肘,甚至失去曾經處于啟蒙理性時期的解釋效力,此時就不得不面對新的歷史情境來進行突破或創新。在后現代語境下,不僅藝術之間的界限被打破,藝術與生活的界限也呈消泯之勢。
3 文學體裁間的滲透
微觀地看,文學內部不同體裁間寫作方式的相互滲透也可產生出乎意料的藝術效果。不同文體間的相互滲透有時在創作形式上還會產生“陌生化”效果,散文詩、詩劇、詩化散文體小說等諸多文學體裁變體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新文學史中,詩化散文體小說應該是小說體裁里旁逸斜出的一支,表現出了較高的藝術價值。與小說本來的敘事傳統不同,這類小說沖淡了故事情節,結構趨向散文化,是無數自然環境和生活片段的描寫。不再專注于描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沒有明顯的故事之開端、發展、高潮和尾聲的固定情節模式,具有“去戲劇性”的特點,《竹林的故事》、《呼蘭河傳》、《百合花》等作品都屬這類。這些具有濃厚抒情氣質的作品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傳遞著文學的真實,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種表現手法上的變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創作主體的某種思維品質,他們抵觸故事化的戲劇性真實,尊重生活的本真樣態,這種寫作方式即他們認識生活的方式。詩化散文體小說為小說的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這無疑是文學藝術表現上的一種創新。當代文學跨界寫作更為普遍,形形色色的小說已經很難統一在特定體裁之下。當然關于“跨文體寫作”自有其客觀的社會文化因素可尋。
4 結語
藝術邊界的規定本身也是歷史性的建構,而體裁間的相互滲透和不同藝術間表現手法的交互使用一樣,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對待不同藝術形式的規定性問題。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在具體的歷史中結合不同的審美文化因素對藝術進行不斷探索。無論是不同藝術間表現手法的相互融合還是文學不同體裁間的越界滲透,對界限某種程度的開放之于藝術的創新是至關重要的。
注釋
①馬利安·高利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史(1917-1930)[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11.
②張大明.李健吾創作評論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