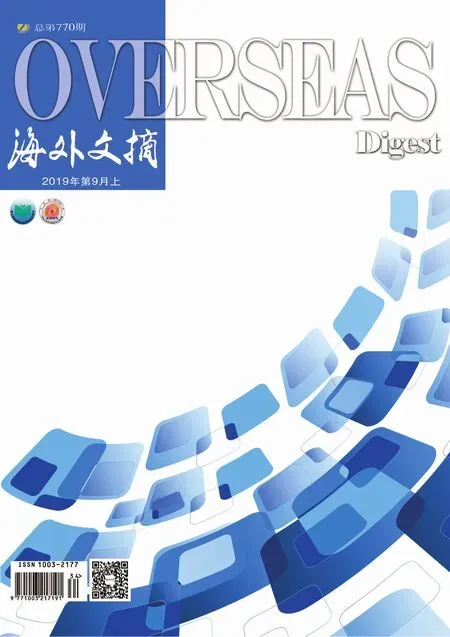《劉存規墓志》中所見遼職官考釋
賈依然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目前,《劉存規墓志》出土年代不詳,但根據現有的傳世文獻資料可以考證《劉存規墓志》的具體情況。志文最早見錄于《古今圖書集成》:“劉存規墓,字守范,河間王二十四代孫,至于大遼間屢建奇功,遼拜為積慶宮都提轄使、紫金榮祿大夫、校尉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卒于應歷五年,葬密云嘉禾鄉,子五:長繼玭,攝順義軍節度衙推;次繼英,永康府押衙;次繼昭,山河都指揮使;次繼倫,定遠軍節度衙推,見碑志。”除《古今圖書集成》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史籍對此有記載:《遼史紀事本末》、《遼史拾遺》、《(雍正)密云縣志》、《(民國)密云縣志》、《(光緒)順天府志》、《古今圖書集成》、《遼代金石錄》、《遼代石刻文編》等,這些文獻所記載的內容大致相同,只有一些細微的差別,但不影響整體,同時被多部文獻記載,可見此墓志還是具有一定地位的。在記載《劉存規墓志》具體內容的同時,有些還在墓志的結尾特意注明“有墓志”或“見碑志”,由此可以證明《劉存規墓志》的真實性。《劉存規墓志》對研究遼代的職官制度提供了珍貴的史料,但至今未見學術界有相關文獻的發表,筆者以墓志為中心對劉存規及其子所擔任的部分官職進行初步考釋,不足之處敬請匡正。
1 積慶宮都提轄使
積慶宮都提轄使,遼出土的墓志中有很多與此職相關的記載,現列舉數例如下:“統和二十年《平州趙府君墓志》:“大遼故永陽宮平州提轄使、銀青崇祿大夫、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天水郡趙府君墓志并序;天慶三年《馬直溫妻張館墓志》:曰同璋,許適諸宮提轄制置使李貽訓男石;重熙十四年《王澤妻李氏墓志》:有子二人,并登進士科,長曰紀,前知延慶宮提轄;重熙十五年《劉日泳墓志》:季曰從文,娶燕京故制衙提轄使梁公之孟女;太平六年《宋匡世墓志》:故儒林郎、前守北安州興化縣令、晉國公主中京提轄使宋府君墓志銘并序。”墓志中頻繁出現這一官職,但是《遼史》只載:“某宮提轄司(官制未詳)。”因而我們無法判斷其設置的具體情況,既然墓主人擔任的是“積慶宮都提轄使”,所以我們先要弄清“積慶宮”是什么。根據《遼史》記載:“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太祖曰弘義宮、應天皇后曰長寧宮、太宗曰永興宮、世宗曰積慶宮、穆宗曰延昌宮、景宗曰彰愍宮、承天太后曰崇德宮、圣宗曰興圣宮、興宗曰延慶宮、道宗曰太和宮、天祚曰永昌宮。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宮,丞相耶律隆運有文忠王府。”通過這一記載可以看出,這里的積慶宮是世宗的宮帳名稱,各個宮衛都是私人的機構,其中既有皇帝皇后,也有一些重臣。各個宮衛都有一定的私人兵力,如果遇有戰事,則需要出兵助伐,而提轄司就屬于這些宮帳中的機構。
《遼史》又載:“是為積慶宮,以文獻皇帝衛從及太祖俘戶及云州提轄司并高宜等州戶置……”從其中戶口的設置情況可以看出,這一宮衛所管理的人口中有漢人,由此可以推斷,提轄司應具有管理漢人的職能。《欽定續通典》中也記載:“遼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戶居之黑水河提轄司。”渤海建國,國內有靺鞨族、漢族、契丹人、高句麗人、女真族等多個民族,因而渤海俘戶由多個民族組成,提轄司的管理民族不受限制。除此之外,根據出土墓志的任官情況來看,上文中所列舉的墓志中擔任提轄司長官的也都為漢人,“以漢人治漢事”,因此這一官職可以由漢人擔任,是否有遼人出任這一官職還需進一步考證。《遼史》記載:“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太和永昌二宮宜與興圣延慶同舊史不見提轄司,蓋缺文也……諸宮衛丁四十萬八千出騎軍十萬一千,大首領部族軍,遼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余騎,小者數百人著籍皇府。國有戎政量借三五千騎,常留余兵為部族根本。”根據這段話的記載,提轄司應為遼朝的軍事機構,具有軍事職能,遼朝在大的軍事要地都要設置提轄司,每當遇有戰事各宮出相應的衛丁助戰。《平州趙府君墓志》中提到的“永陽宮”不見史載,應該也是某一宮衛的名稱。同時這段話中記載了各地提轄司的設置數目不等,重要的軍事要地提轄司設置的數目比較多,而較為安穩的內地設置的數目比較少,更確切的表明了提轄司的軍事功能。
除了上述提轄司外,遼史中還記載有“云州提轄司”、“黑水河提轄司”、“懷州提轄司”等,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某宮提轄司”外,也稱“某地提轄司”。根據上述墓志中的文字,可以大概知道遼“某宮提轄司”內設有“提轄使”、“提轄制置使”、“都提轄使”、“制衙提轄使”等官員,“提轄司”具有軍事和一定的管理漢族事物的職能,且多由漢人擔任這一官職,這些出土的墓志對補充《遼史》之缺起了重要作用。李桂芝在《遼朝提轄司考》中提到“遼朝先后所設置的提轄司數目不少于六十二個,地點至少應有上京、中京、南京、西京、東京、奉圣州、平州、懷州、黑水河等九地。提轄司并非僅有軍事職能,同時具有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職能。從提轄司設于諸宮衛,任提轄使者皆為漢官,可推斷其所掌之事為諸宮衛中的漢人事務,即掌管各斡魯朵的宮分乣軍、隸宮民戶戶口、生產活動、治安與教化等日常管理工作。”我們通過前文的分析已經大致可以知道,“提轄司”具有軍事和一定的行政管理職能,《遼朝提轄司考》指出“提轄司”還具有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職能,從中可以看出“提轄司”是一個具有多種職權的相當獨立的一個機構,但是關于其他各地設置的提轄司和提轄司所具有的其他職能還需要查閱相關的資料進一步考證。
2 紫金榮祿大夫
根據志文記載的劉存規所擁有的官職來看,可以說他是擁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享有極高的榮譽,但史籍中鮮有關于他的記載,因而無法得知劉存規及其家族的詳細情況,根據墓志可以對史料進行補充。文中所記載劉存規的官職為“紫金榮祿大夫”,然而本官職的原稱為“光祿大夫”,根據陳垣先生及史學界的研究表明,遼代確實存在避諱的現象,《遼史·本紀》中將《新五代史》中的晉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改寫為“范延廣”,謂“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將“光祿卿”改為“崇祿卿”,謂“興宗景福元年見崇祿卿李可封”,這是《遼史》中避“光”字之例,根據所處的時間表明,墓志中的“紫金榮祿大夫”是避太宗耶律德光的“光”字諱,因而改變了官職的名稱。
3 順義軍與定遠軍節度衙推
其長子劉繼玭攝順義軍節度衙推,而劉繼倫擔任的是定遠軍節度衙推。根據相關史料記載,順義軍,遼統和中年升朔州為順義軍,領鄯陽、寧遠、馬邑三縣。定遠軍,《方輿考證》曰:“周顯德二年,廢景州為定遠軍,屬滄州,宋太平興國六年,以軍直隸京師。”因而順義軍為朔州軍號,定遠軍為滄州軍號。《新唐書》又曰:“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衙推”是唐朝時節度使的衙內屬官,因而劉繼玭與繼倫擔任的是節度使的屬官,同時根據墓志,“衙推”設在各軍,應該具有一定的軍事職能,而根據《新唐書》所記載的內容,“衙推”可能同時擁有一定的行政職能。
4 永康府押衙
根據志文記載,劉繼英的職位為永康府押衙,關于“押衙”這一名稱,又稱作是“押牙”,這一名稱在遼代出土的墓志中頻繁出現,在《王紹墓志》中有“右都押衙”,《耶律庶幾墓志》中有“左都押衙”,《李內貞墓志》中有“補充隨使左都押衙”等,但《遼史·職官志》中卻沒有準確的記載。《古今事文類聚》中寫到:“押衙,武職,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為“衙門”乎?”這里提到的“牙門”指的是古代軍旅的營門,但“押衙”這一名稱何時出現的尚待考證,在這一段話中,雖然李匡義對“押衙”也沒有提出一個確切的說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押衙”是一個武職。同時根據《遼史紀事本末》記載:“世宗皇帝,諱阮,小字烏云,原作兀欲,義宗貝長子,母柔貞蕭后,大同元年封永康王。”由此可知,永康府是世宗繼位前所居住的王府,所以,劉繼英擔任的是管理永康府軍事事物的一個武職。
5 山河都指揮使
《劉存規墓志》記載:“子五……次繼昭,山河都指揮使。”通過志文可知,劉繼昭曾擔任山河都指揮使,關于“山河都指揮使”這一官職名稱,《遼史·職官志》失載,我們只能從一些關于宋朝官制的其他的史料及其遼代出土的相關墓志中可以見到。迄今為止,學術界沒有發表過關于“山河使”官職的研究,但從“山河使”在墓志中出現的頻率及相關文獻的記載,遼朝有山河使這一官職是確定無疑了,但卻缺少關于這一官職的具體描述,該官職的設置和職責需要深入挖掘。不過從字面意義上看,因為“山河使”這一官職設在各軍,所以,這一類的官職應為軍職,具有一定的軍事職能,與此相關的一些官職也在遼出土的墓志中也頻繁出現。齊作聲的《遼代墓志疏證》:“統和三年《王奉諸墓志》:次崇義軍山河直指揮使,奐。”這里提到王奉諸之子曾擔任山河直指揮使。向南的《遼代石刻文編》:“乾亨三年《王裕墓志》中曾提到王裕子七人,次曰玨,崇義軍山河指揮使;統和二十四年《王鄰墓志》:次弟諱操,武定軍山河指揮使……次守□,臨海軍山河指揮使;統和十八年《劉宇杰墓志》:有男三人,長曰日泳,威肅軍山河指揮使;統和二十三年《王悅墓志》:次遼興軍節度山河使,早亡;統和二十六年《常遵化墓志》:有女五人,長適廣德軍山河節度使耿阮;統和三年《王瓚墓志》:次崇義軍節度山河直指揮使瑍。”重熙六年《耶律遂忠墓志銘》:“別有四男二女……次曰口口,信山河指揮使;保寧二年《耿崇美墓志銘》:長孫前儒州衙內指揮使延弼,次孫前儒州山河指揮使延煦;統和二十九年《耶律隆祐墓志》:乾亨四年,自燕京山河指揮使特授崇祿大夫、檢校太尉、行右神武大將軍。”根據上述的一些墓志資料可以得知,遼朝關于山河使的相關官職至少有各軍的山河指揮使、山河都指揮使、山河直指揮使、山河節度使、節度山河使、節度山河直指揮使等,這些官職雖然不盡相同,但應該都屬于一類職務。上述墓志中記載的廣德軍屬乾州,崇義軍屬宜州,武定軍屬奉圣州,因而總體來說,山河使這一官職應設在各州。《王悅墓志》中記載的“遼興軍節度山河使”與“遼興軍節度使”中的差異還需進一步考證,遼興軍節度使是遼后期擴張時將平州納入版圖之后設置的官職。根據《遼史·地理志》記載:“平州,遼興軍,上,節度……太祖天贊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戶錯置其地。統州二、 縣三。”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遼興軍所管轄的是俘戶。同時《遼史·韓德樞傳》中也有記載:“時漢人降與轉徙者,多寓東平,丁歲災饑饉疾厲,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遼興軍節度使。下車整紛剔蠹,恩煦信孚,勸農桑,興教化,期月民獲蘇息。”這一史料同時也印證了上文中所說的平州所置的是俘戶,所管理的人是漢人,而材料中的韓德樞是漢人,《王悅墓志》中所提到的漢人王悅也曾擔任這一官職,以漢人治漢事。所以,遼興軍節度山河使這一官職是可以由漢官擔任的,除了軍事職能以外,應該也具有一定的管理民事的行政職能。
除了遼朝之外,宋朝其他的一些文獻也提到了有關山河使這一官職,如《王黃州小畜集》中記載:“次曰元度,前同州親事都頭,次曰元方,終于同州山河使,次曰元載,元翰俱未仕。”由此可以看出,其中元方的職位為同州山河使,說明在宋朝,除了“各軍山河使”之外,山河使這一官職設在州,稱為“某州山河使”,這里的職能是否有所不同,尚待考證。《宋史》中也記載:“田彥伊子承寶等百二十二人來朝,賜巾服器幣,以承寶為山河使,九溪十峒撫諭都監。”由此可以看出,宋朝的山河使也設在少數民族地區。《宋會要·職官》中記載:“衙前置都知兵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練使,散教練使、押衙、軍將,又有中軍、子城、鼓角、宴設、作院、山河等使,或不備置。又客司置知客、副知客、軍將。又通引司置行首,副行首、通引官。其防御、團練等州使院衙職悉約節鎮而差減。”所以根據這一記載,其中說的宋朝的“山河使”應該屬于衙前職,但是這段記載中也提到了“或不備置”,因而其官職可能不是一個常職。關于山河使的任官情況,根據出土的墓志資料,其擔任官員既有漢人,又有遼人,因而關于其擔任人員可能不受民族的限制。我們都知道,遼朝的官職是繼承唐、宋的官制的,但是遼朝的山河使職能及其設置范圍是否與宋相同還需更多史料的支持。除了上述記載以外,關于山河使這一官職出現的時間也相當重要。根據《姚江童氏宗譜》記載:“麟先于史惻,至李唐之季,圃一公為浙江山河節度使,因亂發家,卜居越東之剡。”由這一宗譜可以看出,麟在唐朝的時候曾經擔任過山河節度使,所以關于這一官職的設置概況,在唐朝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否會出現的更早,還有待新材料的挖掘。
6 結語
《劉存規墓志》中記載了很多遼朝的官職,傳世史料中缺少關于這些官職的具體記載,對其墓志進行考釋,有助于補充相關史料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且對于我們了解遼朝的官制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只是對其中的一部分官職進行考釋,受現有文獻資料的限制,對《劉存規墓志》中官職的考證還有一些無法證實的情況,這有待于我們的繼續努力。
注釋
[1](清)陳夢雷輯:《古今圖書集成》第二十四卷《職方典》[M].清雍正銅活字本,第2246頁。
[2]向南:《遼代石刻文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10、633、241、244、180頁。
[3](元)脫脫撰:《遼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17、718頁。
[4](元)脫脫撰:《遼史》卷三十一《營衛志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2頁。
[5](元)脫脫撰:《遼史》卷三十一《營衛志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64頁。
[6](清)嵇璜,曹仁虎修篡:《欽定續通典》[M].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第3505頁。
[7](元)脫脫撰:《遼史》卷三十五《兵衛志中》[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06-409頁。
[8]李桂芝:《遼朝提轄司考》[M].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131-135頁。
[9](元)脫脫撰:《遼史》卷三《太宗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38頁。
[10](元)脫脫撰:《遼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86頁。
[11](清)許鴻磐撰:《方輿考證》卷十《直隸三》[M].清濟寧潘氏華鑒閣本,第321頁。
[12](清)張之洞撰:《光緒順天府志》卷七十六《官師志五》[M].清光緒十二年刻十五年重印本,第2243頁。
[13](宋)祝穆撰:《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六《文章部》[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924頁。
[14](清)李有棠撰:《遼史紀事本末》卷首《帝系考》[M].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8月,第2頁。
[15]向南:《遼代石刻文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9頁。
[16]齊作聲:《遼代墓志疏證》[M].沈陽:沈陽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17]向南:《遼代石刻文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4、121、107、113、128、82頁。
[18]向南,張國慶,李宇峰(輯)注.《遼代石刻文續編》[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2010年,第74、15、51頁。
[19](元)脫脫撰:《遼史》卷四十《地理志四·南京道》[M].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00頁。
[20](元)脫脫撰:《遼史》卷七十四《韓德樞傳》[M].北京:中華書局, 1974年,第1232頁。
[21](宋)王禹偁:《王黃州小畜集》卷二十八《碑志》[M].四部叢刊景宋本配呂無黨鈔本,第210頁。
[22](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九十三《蠻夷一·西南溪峒諸蠻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4175頁。
[23]徐松(輯),劉琳、刁忠民、舒大剛等點校:《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265頁。
[24]童遠生等纂修:《姚江童氏宗譜節部 2》[M].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