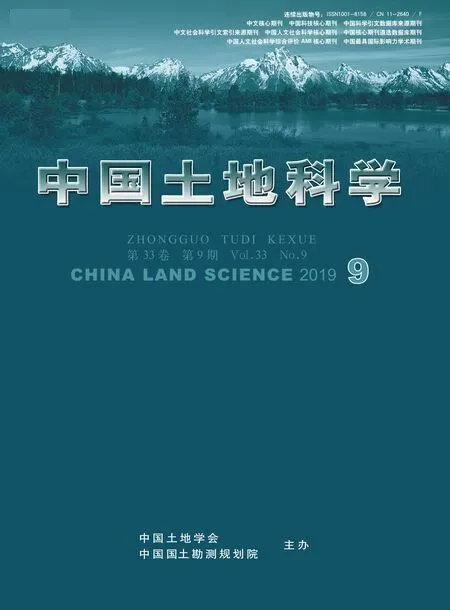城市近郊區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及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分布式認知理論的微觀調查實證
任 立,吳 萌,甘臣林,陳銀蓉
(1.湖北經濟學院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2.湖北經濟學院會計學院,湖北 武漢430205;3.湖北經濟學院財經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205;4.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0)
1 引言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穩慎推進。作為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國土空間要素綜合體,城市近郊區是當前形勢下受到改革沖擊最為頻繁和顯著的區域[1]。近年來,城市發展的集聚效應日益凸顯,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近郊區農村土地流轉集中的趨勢不可逆轉,小農經濟向農業現代化階段轉型升級[2]。在此背景下,各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應運而生,而城市近郊區農戶也面臨由傳統“農業生產勞動力”向新型“農業經營決策者”的艱難轉型[3-4]。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健全的現實條件下,土地制度變遷勢必產生社會成本問題,由此產生的風險會增加農戶土地投入的交易費用,從而降低改革進程中農戶的獲得感,使其存在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的潛在需求[5-6]。
本文研究的土地投入是指農戶主體以農用地為對象所進行的生產性投資行為,其風險包括各類要素成本、機會成本和不確定性。針對農戶土地投入及其風險認知的研究,大量學者基于不同的視角展開了豐富的探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土地投入是農村地區最為常見的生產性投資行為,一般認為其受到內部因素(如個體、家庭特征和資源稟賦)和外部因素(如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環境)的影響,且表現出一定的空間異質性[7-8]。在此基礎上,有學者總結了農戶土地投入行為決策的路徑范式,并得出當前形勢下中國農戶仍是典型的“風險規避者”[1,6]。更多學者認為,隨著土地投入“高成本、高勞耗和低效益”的風險特征日益凸顯,土地資源閑置和撂荒現象在部分地區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從而引發了對土地經營權有序退出的必要討論[9-11]。與此同時,農業現代化過程中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3,12-13]、農業社會化服務對傳統土地利用方式帶來的機遇和挑戰[4,14-15]等問題,都將深刻影響傳統農戶的土地投入和風險認知,而這背后的影響機理和復雜邏輯尚待進一步明確。
上述分析表明,農戶土地投入風險的本質正在發生顯著變化,這種變化的背后是土地流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社會化服務等新鮮事物對農戶認知環境帶來的外生沖擊。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線地區,城市近郊區農戶的土地利用方式、社會保障需求和家庭生計格局必將隨著風險認知的變化而變化,而現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農戶行為意愿,而對其背后的認知機理則鮮有關注。本文旨在探索當前形勢下城市近郊區農戶對土地投入風險的認知狀況,在分布式認知理論的分析框架下,結合483名城市近郊區農戶的微觀調研數據,構建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結構方程模型,從“個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三個認知功能系統的角度深入研究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及影響因素,進而為提高農地資源利用效率、提升農戶風險管理水平、促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合理完善提供決策依據。
2 理論假說與研究設計
2.1 分布式認知理論
分布式認知理論(Distributed Cognition Theory,DCT)源于心理學中對個體認知活動的研究,該理論提出了一種觀察認知活動完整過程的全新視角,并認為認知活動受到個體特征、地域環境、社會文化的多層次影響。HATCH和GARDNER率先提出了分布式認知的同心圓模型(圖1),區別于傳統影響因素分析一味強調認知主體個體特征的局限,該模型以個體與環境之間互動博弈的功能系統作為研究的基本單元,這對于處于復雜社會環境下的個體認知活動具有較強解釋力[9,16-17]。學者基于分布式認知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個體認知活動是在“個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的綜合作用下發生的,而這三個功能系統之間也會相互影響、彼此關聯,并最終決定個體的認知水平[9]。基于此,本文在同心圓模型的基礎上提出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分析框架(圖1)。
2.2 研究假說與問卷設計
心理學研究指出,認知活動是個體基于主觀經驗對客觀世界的信息進行加工的過程[17]。土地投入作為一種生產性投資行為,農戶對其風險的認知會具體表現為對各種經濟損失、心理負擔和不確定性的主觀響應和敏感程度。為了實現對這一抽象概念的定量分析,本文借鑒農戶土地投入感知風險層次模型對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 of Land Investment,RP)進行測度,從而將其具體細分為經濟風險(Economic Risk,ER)、心理風險(Psychological Risk,PR)和情境風險(Situational Risk,SR)3個現實維度[1,6]。在此基礎上,結合分布式認知的基本框架和近年來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待驗證的研究假說:
H1:個人力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個人力(Individual Force,IF)是分布式認知的基礎和核心,強調的是個體經驗對認知客體的影響。已有研究指出,農戶特征如年齡(AGE)、受教育程度(EDU)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認知能力與水平;農戶的兼業程度(Parergon Level,PL)越高,表明其對土地投入的生計依賴越弱,耕作土地的機會成本就越高[6-9]。理論上,農戶的風險韌性(Risk Resilience,RR)和風險偏好(Risk Appetite,RA)等性格特征會促使其在行為決策過程中對風險因素更加敏感[12]。基于此,本文假設個人力與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之間存在正相關。

圖1 基于同心圓模型的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分析框架Fig.1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rmers’ risk perception on land investment based on DCT
H2:地域力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地域力(Regional Force,RF)是分布式認知的關鍵,強調認知主體和客觀環境之間的互動。已有研究指出,作為生產經營決策主體的農戶,需要同時考慮諸如農業生產資源的稟賦狀況如承包地面積(Agricultural Acreage,AA)、土地流轉比例(Land Transfer,LT),耕作土地的本地情境如農業基礎設施(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AI)、農業社會化服務(Socialized Service,SS)和非農務工環境(Job Market,JM)等因素[4-11,14-15]。理論上,土地經營規模越大,生產投入的要素成本就越多;非農就業環境越好,農戶進行土地投入的機會成本就越高,風險感知也就越強烈。基于此,本文假設地域力與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之間存在正相關。
H3:文化力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文化力(Cultural Force,CF)是對具體認知活動能夠產生間接影響的抽象事件,其對認知活動的影響不可忽視。已有研究指出,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產生間接影響的其他因素可能包括非正式制度下的土地情結(Land Complex,LC)、熟人社會中個體之間的從眾心理(Crowd Mentaily,CM),以及認知對象以外的因素對認知主體的影響如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PI)、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CI)和家庭認同(Family Identity,FI)[1-2,6,9-11]。理論上,穩定的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能夠有效降低個體對風險因素的敏感程度。基于此,本文假設文化力與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之間存在負相關。
在分布式認知理論的分析框架基礎上,結合預調研階段農戶半結構訪談的結果,對課題組前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問卷量表予以進一步開發[1,6,9-11],共設計18個觀測變量題項,以測量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模型中的4個潛在變量,問卷結果采用李克特五點量表的有序分類變量形式予以表征(表1)。
3 數據來源與樣本描述
武漢城市圈位于湖北省東部,是中國中部地區重要的城市群,同時也是研究城市近郊區土地利用問題的典型樣本區域。本文采用的數據來源于課題組2018年7—8月對武漢城市圈近郊區農戶的問卷調查,樣本區域覆蓋了武漢市(童周嶺村和群益村)、孝感市(埠鎮村、龍崗村和同昶村)、天門市(紅花堰村和劉楊村)、潛江市(雙豐村)、仙桃市(興隆村)、咸寧市(高橋村和石橋村)、黃石市(楊橋村和袁大村)、鄂州市(池湖村和路牌村)和黃岡市(南湖村)。樣本抽樣方式為偶遇抽樣,數據獲取方式為入戶一對一調查和農戶半結構訪談,問卷發放共計500份,回收有效問卷483份,有效問卷率96.60%。樣本描述性統計特征如表2。

表1 量表開發與問卷設計Tab.1 Scale development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表2 樣本農戶特征描述Tab.2 Characteristics description of the samples
由表2可知,調查樣本主要來自城市近郊區的普通農戶家庭,樣本結構上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中老年男性為主,農戶兼業程度的異質性分化特征明顯。調查樣本符合農村勞動力城市轉移背景下城市近郊區農戶群體的現實特征,樣本抽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 研究方法與模型分析
本文建立的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模型是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過程的高度抽象,其模型結構和變量關系符合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的特征。其中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為SEM的潛在變量,4個潛在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SEM的結構模型;經濟風險(ER)等、年齡(AGE)等、承包地面積(AA)等、土地情節(LC)等為各個潛在變量的觀測變量,各組觀測變量與潛在變量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SEM的測量模型。
4.1 數據檢驗與模型修正
根據結構方程模型對數據質量的要求,本文采用SPSS 21.0對觀測變量分別進行了信度與效度檢驗,并運用AMOS 21.0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了探索式建模,以避免出現“違反估計”的情況[18]。初始模型的運行結果顯示,部分變量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估計值大于1,或誤差項變異系數的方差估計值為負數,表明初始模型出現違反估計。根據觀測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在保證觀測變量對潛在變量具有解釋意義的前提下,通過人工選擇和逐步回歸的方式將風險偏好(RA)、農業基礎設施(AI)和從眾心理(CM)從模型中依次剔除,模型得以有效修正。對此一種可能解釋是,風險偏好(RA)、農業基礎設施(AI)和從眾心理(CM)的指標含義已經分別在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的其他觀測變量中得以體現,不宜單獨作為新的觀測指標項進行處理。修正后的模型所對應的信度與效度檢驗結果如表3。
由表3可知,信度檢驗中各潛在變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數在0.712~0.860之間,大于0.6的閾值條件;效度檢驗中各潛在變量的KMO值均在0.619~0.760之間,大于0.5的閾值條件,且Bartlett球體檢驗的伴隨概率均小于0.01,因子分析結果顯示,觀測變量在各自歸屬的因子上載荷系數的絕對值在0.716~0.891之間,大于0.5的閾值條件。由此表明數據具有較好的信度與效度,模型選用的樣本數據質量通過檢驗。
4.2 結構方程模型結果分析
根據數據檢驗與模型修正的結果,本文基于樣本數據構建包含4個潛在變量和15個觀測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圖2)。其中測量模型的因果關系用“→”表示,方向由潛在變量指向觀測變量;而結構模型的變量關系則用“→”或“ ”表示,表明前置因素對后置因素的影響或潛在變量互為相關。測量模型中觀測變量的殘差用e1~e15表示;結構模型的測量誤差用re1表示。考慮到變量方差之間存在的合理共變關系,增列e2與e11、e3與e6、e4與e9、e8與e10、e9與e10共計5組共變關系,從而在不違背理論假設的前提下有效降低模型卡方值。根據AMOS 21.0軟件輸出的適配度檢驗結果,整理得到模型擬合優度指標表如表4。

表3 信度與效度檢驗結果Tab.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results

圖2 結構方程模型及標準化參數估計結果Fig.2 The SEM and the standardized 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表4 模型擬合優度指標表Tab.4 Goodness of fi t index
由表4可知,各項擬合優度指標的統計值均滿足閾值條件,該SEM對樣本數據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模型通過穩健性檢驗。最終確定的結構方程模型及參數估計結果如圖2。
由圖2可知,15個觀測變量的標準化載荷系數均小于0.95的閾值,方差估計值全部為正,且達到0.01的顯著性水平,表示測量模型滿足適配條件。同時,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之間以及增列的5組共變關系之間的協方差估計值也達到0.01的顯著性水平。綜合模型參數估計結果,進行分析如下:
(1)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對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的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在0.01、0.01和0.05水平上顯著,研究假說H1、H2、H3均得到有效證實,表明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符合分布式認知理論的分析框架。農戶對土地投入風險因素的主觀響應和敏感程度,受到個人力(IF)、地域力(RF)和文化力(CF)三個認知功能系統的綜合影響。其中,個人力(IF)包含了個體特征、生計經驗和風險韌性等描述農戶主觀能力的內生性功能指標;地域力(RF)表征的是農戶在土地投入風險認知活動中對外部環境和本地情境的功能性反饋,如土地資源稟賦特征、農業生產方式和土地投入的機會成本等;文化力(CF)描述的是農戶對現階段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特征的功能性績效評價,包括對土地的情感依賴、對社會、集體和家庭生活的滿意度等。
(2)地域力(RF)→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728,在分布式認知的三個功能系統中路徑系數絕對值最大,表明地域力(RF)是影響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主要功能系統。承包地面積(AA)、土地流轉比例(LT)、農業社會化服務(SS)和非農務工環境(JM)這4個地域力觀測指標的因子載荷系數分別是0.873、-0.853、0.811和0.674,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越大、對農業社會化服務越依賴的農戶對土地投入的風險認知越強烈,其次是將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而土地流轉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沖土地投入帶來的風險。
(3)個人力(IF)→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416,在分布式認知的三個功能系統中路徑系數絕對值相對較大,表明個人力(IF)是影響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重要功能系統。年齡(AGE)、受教育程度(EDU)、兼業程度(PL)、風險韌性(RR)這4個個人力觀測指標的因子載荷系數分別是-0.830、0.602、0.844和0.626,表明農戶對土地投入風險的認知水平受到其生計方式的顯著影響,其次是個體的儲蓄習慣和文化水平,而農戶所處的年齡階段與其土地投入的風險認知高度負相關。
(4)文化力(CF)→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的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395,是分布式認知中唯一路徑系數為負的功能系統,表明文化力(CF)是調節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有效功能系統。土地情結(LC)、政治認同(PI)、集體認同(CI)和家庭認同(FI)這4個文化力觀測指標的因子載荷系數分別是0.751、0.646、0.645和0.891,表明家庭生活的幸福感能夠有效抑制農戶對土地投入風險的負面情緒,對土地資源的情感依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作為生計方式帶來的風險,政府、村集體提供的公共管理和服務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農戶提供風險應對的有效支持。
(5)經濟風險(ER)、心理風險(PR)和情境風險(SR)對土地投入風險認知(RP)的因子載荷分別為0.721、0.758和0.704,且達到0.01的顯著性水平,表明農戶對土地投入的風險認知是多層次的,包括對土地投入產生的經濟損失、心理負擔和不確定性的綜合考慮。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基于分布式認知理論的分析框架,構建了關于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結構方程模型,結合樣本區域483名城市近郊區農戶的微觀調研數據,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方法對研究假說和理論模型進行了有效驗證,并得到三個認知功能系統和各認知影響因子對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標準化效應系數如表5。
綜合全文研究內容和表5中的效應系數結果,得到主要結論如下。
(1)城市近郊區農戶的土地投入風險認知活動遵循分布式認知的基本框架,受到個人力、地域力和文化力等認知功能系統的綜合影響。其中,地域力和個人力分別是主要和重要的正向影響因素,而文化力是有效的負向影響因素。這說明現階段城市近郊區農戶的土地投入風險主要來源于“地域力”和“個人力”的局限,而“文化力”則是調節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有效手段。
(2)在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現實背景下,農業勞動力的匱乏改變了傳統小農家庭“親力親為”的土地耕作方式,土地耕種主要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機構提供的有償服務來完成,而城市近郊區農戶也隨之由“農業生產勞動力”向“農業經營決策者”轉型,這種社會分工條件下的土地投入成本有著更高的顯示度,同時也更容易量化。研究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越大、對農業社會化服務越依賴,農戶主觀上對土地投入的風險認知就會越強烈;與此同時,非農行業的高效益提高了農戶進行土地投入的機會成本,土地投入在認知層面上是“虧損”的;而土地流轉不僅可以帶來一定的流轉收入,還可以釋放家庭勞動力,規避土地投入風險,在合理的流轉價格和穩定的承包關系條件下,農戶具備退出土地經營權的潛在需求。

表5 模型變量對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標準化效應系數Tab.5 Standardization effect coef fi cient of the model variables
(3)當前形勢下,中國農戶群體的異質性分化正在發生,農戶特征分化是研究“三農”問題不可忽視的重要視角。研究表明:就土地投入這一典型的生產性投資行為而言,農戶的年齡、受教育程度、兼業程度、風險韌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風險認知。其中,對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風險韌性的高兼業農戶而言,土地投入“得不償失”,選擇非農就業更符合其經濟理性;而對于留守城市近郊區的中老年農戶而言,土地投入既是對土地情結的有效滿足,同時是“自食其力”的可持續生計,家庭承包地在很大程度上發揮著這種“弱保障”功能,而在實際上處于低效利用的狀態。因此,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對土地保障功能的有效替代,是進一步提高農村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前提。
(4)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大量農村勞動力發生了城市轉移,這一現象在樣本區域的城市近郊區尤為明顯,人口結構的“弱化”和“老化”,深刻刻畫了中國農村“凋敝”的現實。研究表明,村落聚居的熟人社會依然保有農耕文明的底層邏輯,即農戶對家庭生活的滿足和對土地的情感依賴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抑制風險因素帶來的負面感知,從而提高自身的安全感。與此同時,通過政治文化宣傳和對集體意識形態的引導,能夠實現對農戶風險認知的有效調節,但相關部門在這一方面提供的公共管理服務水平仍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本文受樣本數據和研究方法的局限,對理論模型中風險偏好(RA)、農業基礎設施(AI)和從眾心理(CM)三個指標進行了剔除,但并不能明確排除其對農戶土地投入風險認知的影響,如何將其合理納入分析框架,仍有待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