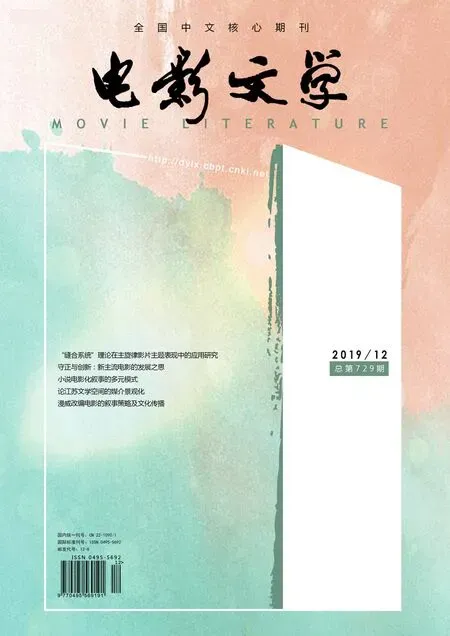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愛情片的風(fēng)格化
劉 高(重慶工商職業(yè)學(xué)院,重慶 400052)
作為大眾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電影,其創(chuàng)作往往必須在個性化(personalize)和風(fēng)格化(stylize)之間取得平衡。所謂風(fēng)格化,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含義,一為使之符合某種風(fēng)格或模式,二為使之因襲。愛情電影在當(dāng)代類型片中,一直具有較為強(qiáng)勢的地位,這除了愛情電影有投資小、回報(bào)周期短以及包容力強(qiáng)等優(yōu)勢,也與電影人在創(chuàng)作時有意識地犧牲了個性化,走向風(fēng)格化有關(guān)。電影人的這種創(chuàng)作傾向,保證了愛情電影能適應(yīng)大多數(shù)觀眾的口味,在院線上能取得較好的成績。近期上映的,由臺灣導(dǎo)演林孝謙執(zhí)導(dǎo)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2019),盡管翻拍自韓國同名電影,但在內(nèi)地上映之后迅速引發(fā)觀影熱潮,可以說,影片正是這種愛情片風(fēng)格化的典型范例。
一、對模式的必要重復(fù)
如前所述,風(fēng)格化首先指的是在創(chuàng)作時,以普遍性的特征來呈現(xiàn)事物,而一旦這些特征被約定俗成地固定下來以后,它們就會為后繼的創(chuàng)作者所重復(fù)、因襲。最直觀的風(fēng)格化莫過于美術(shù)設(shè)計(jì),如被一圈發(fā)散的線圍繞的圓,就是太陽的風(fēng)格化圖標(biāo)。風(fēng)格化使得藝術(shù)能夠跨越文化與語言的障礙。“交流取決于雙方是否存在共同點(diǎn),比如都認(rèn)可的象征符號、用法或定義,令人難以忘懷的交流必須是雙方都愿意在這些方面進(jìn)行深入探討的。”電影藝術(shù)亦是如此,為了實(shí)現(xiàn)更順暢的與觀眾之間的交流,愛情電影往往也會對其他同類電影,甚至是更早的民間傳說、文學(xué)作品等進(jìn)行因襲。如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遭遇“第三者”,出現(xiàn)危機(jī),但最終還是戰(zhàn)勝危機(jī),走向復(fù)合與團(tuán)圓。這就是一種常見的敘事模式,如明代馮夢龍的《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講述的便是這樣的故事,妻子王三巧兒與陳大郎偷歡,但最終還是得到了丈夫蔣興哥的原諒。而在當(dāng)代愛情電影中,如徐崢的《港囧》(2015)等,采用的也是這一敘事模式,有著“尋找初戀”這一精神出軌嫌疑的徐來最終也意識到了妻子蔡波和家庭的重要性,回歸到了原本不滿的婚姻中。無論讀者抑或觀眾,始終都有著對出軌者在付出一定社會代價(jià)后回心轉(zhuǎn)意,原有婚姻得到延續(xù)這一“破鏡重圓”敘事風(fēng)格的喜愛。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采用的并非這樣的圓滿型敘事模式,但是同樣有著屬于風(fēng)格化的重復(fù)性。唱片制作人張哲凱的父親在他幼年時就因患白血病離世,隨即母親也拋棄了他一去不復(fù)返。高中的時候,張哲凱認(rèn)識了叛逆的女生宋媛媛,而宋媛媛同樣是一個孤兒,家人在一次車禍中去世,宋媛媛便住在張哲凱的家中,度過了多年溫馨快樂的時光。長大后兩人又一起進(jìn)入唱片公司工作,不料就在兩人即將對對方剖白情感時,張哲凱發(fā)現(xiàn)自己也患上了家族遺傳的白血病并已時日無多,他便決定在自己還活著時為宋媛媛找到歸宿,而宋媛媛則在張哲凱的刺激下相中了事業(yè)有成英俊瀟灑的牙醫(yī)楊佑賢。張哲凱在調(diào)查了楊佑賢后,暗中幫助成就了這段姻緣,親手將穿著婚紗的宋媛媛交到楊佑賢的手中,自己則病發(fā)而死,不久知道真相的宋媛媛留下遺書殉情而死。男女主人公情投意合,卻遭遇意外打擊(如車禍、癌癥等),最終被迫忍痛分離這樣的敘事套路,在愛情電影中屢見不鮮。觀眾與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之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經(jīng)得起意外考驗(yàn)的愛情,才是偉大的愛情,愿意舍己從人的愛人,才是理想的愛人。于是,張哲凱舍棄了自己成婚和病重時被照顧的機(jī)會,宋媛媛舍棄了生命,共同譜寫了這段“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電影人和觀眾之間的交流得以完成。
又如在人物的符號化設(shè)計(jì)上,電影也是模式化的。愛情電影常常塑造出頗為完美的、情圣式的男性形象,他們對女性往往有著引導(dǎo)者、保護(hù)者的意義,這樣便能喚起觀眾尤其是女性觀眾的向往。例如在薛曉璐的《北京遇上西雅圖》(2013)中,來自北京的司機(jī)郝志便是這樣幾乎沒有道德缺憾的符號化人物,他對女兒有著無微不至的疼愛,對已離婚的前妻則百般遷就,對文佳佳也給予著溫暖關(guān)懷。《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中的張哲凱也是這樣的“暖男”形象。在事業(yè)上,他支持著宋媛媛;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他包容著宋媛媛。如宋媛媛說他名字難聽,提出以后就叫他“K”,他全盤接受。在人生大事上,他則力圖為宋媛媛安排好一切,不僅暗地里調(diào)查了楊佑賢,還親自出面,懇請已經(jīng)出軌了的楊佑賢未婚妻辛迪主動退出等。張哲凱、郝志等男性形象,是一種社會期望漸漸沉淀下來的產(chǎn)物,是女性對于某種安全、溫暖情感棲息地的需求的代償者。
二、與現(xiàn)實(shí)的微妙距離
除了被重復(fù)的具有普遍性的特征,風(fēng)格化還包含了有意的“失真”的含義,因?yàn)閯?chuàng)作者往往會使用夸張或簡化的方式來實(shí)現(xiàn)對風(fēng)格的靠攏,來實(shí)現(xiàn)和藝術(shù)理念或習(xí)俗的一致,如古埃及的被拉長了的貓的雕塑,理想而完美的人體塑像等,戲劇和電影的創(chuàng)作亦然。有學(xué)者指出,所謂風(fēng)格化,即“以一種簡化的形式再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手法。……戲劇文學(xué)和舞臺寫作一旦放棄模仿地再現(xiàn)某個整體或某個復(fù)雜的現(xiàn)實(shí)時就會求助于風(fēng)格化”。電影人所要刻畫的,并非復(fù)雜、千人千面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兩性愛情關(guān)系的樣貌,而是一種偏向于理想、完美的愛情關(guān)系,為了保證這種理想和完美,愛情故事中的部分元素就要被夸張(如人性的真善美部分)或簡化(如現(xiàn)實(shí)的困厄殘酷等),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個體,往往難以擁有電影中人的情感經(jīng)歷。
在《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中,張哲凱和宋媛媛對于情感的執(zhí)著,以及他們的際遇,就略顯“超現(xiàn)實(shí)”,卻保證了電影符合浪漫、深情藝術(shù)理念的一面。張哲凱和宋媛媛自幼失怙,但兩個人都保持了陽光、樂觀的心態(tài),缺乏家庭支援雖然使宋媛媛養(yǎng)成了吸煙等惡習(xí),但是沒有影響兩人的學(xué)習(xí)成績。兩個人在一起之后,情投意合,生活上充滿了種種情趣,如一起吃冰激凌等,同居期間從未爭吵決裂。主人公的生活狀況無疑是令觀眾向往的。而在病魔來臨后,由于張哲凱表示希望宋媛媛去找一個能給她帶來幸福的人度過余生,不明真相的宋媛媛賭氣撩撥了牙醫(yī)楊佑賢,用送飯等方式讓楊佑賢感受自己的溫情,而人品穩(wěn)重的楊佑賢則表示自己已經(jīng)訂婚,但在張哲凱的調(diào)查中,楊佑賢未婚妻、攝影師辛迪早已投入他人的懷抱,在張哲凱說出自己的托付意愿后,辛迪竟寬宏大量地表示愿意退出,條件是需要張哲凱配合她拍一組關(guān)于死亡的照片。隨后辛迪在和楊佑賢攤牌時也極為堅(jiān)決果斷,令楊佑賢備感受傷。辛迪的態(tài)度令張哲凱的“成全”成為可能,然而這卻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極為少見的。更與常人的婚姻觀有距離的是,在宋媛媛知道張哲凱的一片苦心之后,竟然撇下自始至終并無過錯的楊佑賢自殺殉情,顯然,宋媛媛的最終決定,是電影繼承了梁祝、羅密歐與朱麗葉等愛情故事后,為“生命誠可貴,愛情價(jià)更高”理念設(shè)計(jì)的一個流行文本。宋媛媛和張哲凱“真愛至上”,不顧一切的行為固然令人感動,但是也有著缺乏思考,道德立足點(diǎn)不穩(wěn)的一面,對于絕大多數(shù)重視婚姻穩(wěn)定性,認(rèn)可婚姻責(zé)任感、珍視生命的觀眾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是自己絕不會選擇的。
必須承認(rèn)的是,絕大多數(shù)的愛情電影并非現(xiàn)實(shí)的一面鏡子。對于愛情電影來說,它既不能過于脫離現(xiàn)實(shí),違背時代的價(jià)值觀念,從而讓觀眾對主人公的情感體驗(yàn)缺乏代入感,在心理上缺乏能說服自己的理由;同時又必須抑制個體差異,拉開與現(xiàn)實(shí)的距離,以給觀眾一定的夢幻感,滿足觀眾的獵奇心,而這種距離是十分微妙的,它需要電影人妥善處理。
三、愛情片風(fēng)格化的文化成因
首先,愛情片的風(fēng)格化來源于人類對幸福生活,浪漫愛情的永恒的、普適性的向往。愛情電影通過男女主人公或是坎坷不順,或是甜蜜美滿,或是團(tuán)圓廝守,或是陰陽分離、人鬼殊途等經(jīng)歷,來填補(bǔ)觀眾在情感體驗(yàn)上的不足或喚起其情感焦慮的共鳴,電影中角色必然要陷入戲劇性的事件,如誤會、爭吵等,觀眾的諸般情緒才能得到宣泄,如《同桌的你》(2014)中人物的出國導(dǎo)致關(guān)系無疾而終,《何以笙簫默》(2015)中的父輩恩怨等。這種心理決定了愛情片的重復(fù)、巧合等特點(diǎn),以及最終的同質(zhì)化和風(fēng)格化。《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也是這樣,張哲凱和宋媛媛因?yàn)楦髯约彝サ钠屏讯嘁罏槊陂L達(dá)十年的同居生活中只發(fā)生了“零點(diǎn)五”次性關(guān)系,感情浪漫而純潔,兩人都愿意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成全對方,最終雖然沒能結(jié)為夫婦,卻相隨于地下。而他們身邊的楊佑賢、辛迪和伯妮等人無不都是善良的,樂于助人的人,驕縱任性的伯妮盡管一開始難為過宋媛媛,但在與宋媛媛結(jié)為朋友后便全心全意地關(guān)懷她和張哲凱之間的感情。一言以蔽之,電影雖然是一出悲劇,但是其情感氛圍是極為和諧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是極為唯美的,也是與現(xiàn)實(shí)生活存在一定反差的,這正好為觀眾構(gòu)筑了一個關(guān)于現(xiàn)代都市下“純愛”的想象空間。
其次,當(dāng)代國產(chǎn)愛情片的風(fēng)格化,還與經(jīng)濟(jì)全球化以及中國社會經(jīng)濟(jì)實(shí)現(xiàn)高速發(fā)展,人們進(jìn)入消費(fèi)社會,逐漸習(xí)慣消費(fèi)主義生活方式與行為習(xí)慣有關(guān)。在消費(fèi)文化的語境中,人們消費(fèi)的目的相對于實(shí)際需求而言,更是一種被制造和刺激出來的欲望,人們消費(fèi)的對象相對于商品本身的使用價(jià)值而言,更是其符號象征意義。愛情電影就是人們消費(fèi)的商品之一,觀眾之所以愿意走進(jìn)電影院,主要是為了其背后的各種象征意義,例如充滿自嘲意味,有著詼諧幽默情節(jié)的《失戀三十三天》(2011),就是有著治愈失戀情傷意義的商品,在此之后,類似的治愈系失戀題材的愛情電影便大行其道;又如《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2011)、《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2013)等,則是以青春歲月為賣點(diǎn),滿足觀眾回顧純情學(xué)生時代經(jīng)歷的商品,電影人的創(chuàng)作顯然需要考慮觀眾的消費(fèi)心理,對其進(jìn)行針對性的批量生產(chǎn)。以“唯一觀影提示:請帶足紙巾”為宣傳點(diǎn)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依靠的則是觀眾對“生死相隨”“至死不渝”感情的需求,電影要喚起的是已經(jīng)走上社會,出入職場的觀眾的認(rèn)同,已經(jīng)擁有社會經(jīng)驗(yàn),各自的婚戀觀多少被功利目的所影響了的觀眾需要以虛構(gòu)的電影,考問各自的內(nèi)心狀況,因此電影中人物的自我犧牲,殉情等故事盡管夸張,激進(jìn)且套路化,但是能引發(fā)觀眾的震撼,反思與感懷,電影由此徹底成為合格的消費(fèi)商品。
當(dāng)我們剖開當(dāng)代國產(chǎn)愛情電影的發(fā)展橫斷面后,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其顯而易見的風(fēng)格化。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以及人們千姿百態(tài)的情感關(guān)系被提純出來,經(jīng)過具有重復(fù)性、失真性的處理后形成了銀幕上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的影像,而這種重復(fù)性與失真性并非愛情電影的缺陷,其背后有著深厚,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因。人們對于真摯的愛情有著強(qiáng)烈、持久的憧憬和期待,愛情電影在滿足人們的情感需求,正面引導(dǎo)社會價(jià)值觀方面,有著積極的意義。《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就代表了愛情電影在風(fēng)格化方向上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盡管其依然有不足之處,但在國產(chǎn)電影踏上產(chǎn)業(yè)化道路,愛情電影迎來機(jī)遇與挑戰(zhàn)并存的時代的今天,它的借鑒意義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