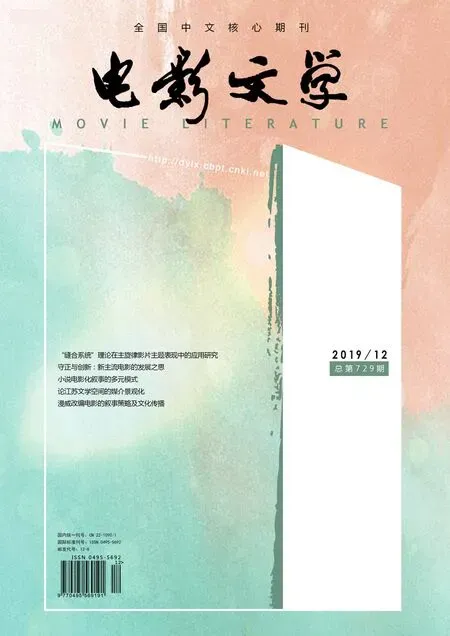影片《流浪地球》的視覺架構策略
張 啟(華北水利水電大學,河南 鄭州 450046)
鏡語敘事的魅力在于通過電影獨特的敘事語言與視覺影像相結合架構出一個屏幕中的虛幻世界,并通過銀幕中的影像傳達出影片意旨、人文語境與影片的美學理想。作為鏡語敘事中傳達影片語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起到了支撐影片敘述環節與呈現影片視覺效果的作用,而且還左右著影片的精神意旨與美學基調,所以,電影中的視覺一直以來被作為電影理論的重要研究課題,為了敘事的有效書寫,如何合理地將視覺納入到敘事單元中,能夠使視覺最大化地發揮其能效性,并通過這種安排展現出影片的深層語義與美學價值,成為電影視覺架設的一種策略。在當代科幻史詩類影片中,視覺架構已成為彰顯影片美學理想與獨特審美格調的重要環節,電影創作者通過視覺架構將影片的宏大敘事映入觀看者內心,達成影片敘事與視覺融合,經由奇幻視覺體驗帶來的感官沉溺與價值認同也成為科幻史詩類影片的目標與追求。在影片《流浪地球》上映以來,受到了觀眾的認可,在這樣一部科幻史詩影片中,由獨特的視覺架構產生的災難鏡語震懾人心,不難看出導演在影片視覺上的精心設計,同時由于視覺上的成功,更加凸顯出影片所展現的災難憂思與人文觀照,賦予了影片深刻的美學烙印。
一、視覺架構與史詩敘事
電影作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語言,從其語言形式來講是多元混合的,這其中既有其敘事的成分,同時還囊括了視覺與聽覺等多種要素,電影就是將這些要素集合在一起,形成有別于傳統文學、圖書、音樂、繪畫等一元敘事的多元語言,而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成分則是作為情節敘述主體的鏡語敘事與作為影像傳達功能的視覺,在二者的相輔相成作用下,電影語言最大化地展現著其獨特的敘述能力。在電影語言中,觀看者的感受是由視聽影像的畫面與聲音傳達到大腦中樞神經而形成的,“觀看”是電影最為直觀的語言呈現,也是鏡語敘事最為重要的語言媒介,通過影像傳達的視覺在獨特的電影敘事方法下呈現出多種語義與美學基調,也成為當代電影標新立異,尋求突破的重要方式與角度,尤其是在依賴于視覺烘托的科幻片、災難片、魔幻片、武俠片等商業類型片中,影片中大量的視覺鋪設不但建立了觀影快感與感官愉悅,更是借由視覺彰顯影片獨特的人文語境與美學意境。《流浪地球》是國產科幻史詩電影具有里程碑的作品,影片在視覺架構上體現了與鏡語敘事的深度融合,構建出逼真而震撼的災難語境,成為書寫災難史詩的一部時代力作。
在影片《流浪地球》中,視覺架構呈現了與鏡語敘事的兩種關聯,第一種關聯是服務于鏡語敘事的視覺架構,為影片搭建出具象的災難空間與現實處境,如在影片的劇情設定中,人類所面對的災難環境是極度艱難的,在地球開始實施了“流浪地球”計劃之后,由于地球與太陽漸行漸遠,地表溫度驟降,而海平面突然升高導致許多城市已經完全被湮沒,在地表零下80攝氏度的超低溫與稀薄空氣環境中,人類已經無法生存,只能轉移至地下城。為了能夠真實地通過鏡語展現出這一災難環境,并透過災難體現人類無法承受的磨難與殤別之情,影片架構出了幾個具有典型特征的視覺空間,首先在影片的開始,鏡頭下是三個人在夜幕下傷感的對話,父親劉培強告訴還是孩子的劉啟:“當你不用望遠鏡就能夠看見木星的時候,爸爸就回來了”,影片用慢鏡頭展現出一幅寧靜而略顯哀傷的畫面,背景是一座巨大的行星發動機,配上悲情而舒緩的音樂,儼然預示著這是災難即將來臨之前的平靜。緊接著這種平靜戛然而止,影片以旁白解說的方式,通過災難圖像的拼接將整個事件背景全盤托出,同時,在這一小段旁白中,影片也將幾個重要的敘事空間利用視覺圖像一一呈現,地表的災難環境、人類寓居的地下城、伴飛的領航員空間站等,緊湊的畫面拼接與悲壯的背景音樂使整個影片立刻變得分外凝重。在劉啟領著妹妹韓朵朵逃離地下城時,影片架構出了一個極致的地表景象,鏡頭由升降梯門打開的一剎那開始,一股寒風伴著暴雪呼嘯而來,隨著鏡頭的推進,超大型的運載車正在極寒的地表環境中運行,而人類在地表只能穿著特殊技術制作的防寒服,帶著氧氣罩艱難前行。
視覺架構與鏡語敘事的第二種關聯是視覺架構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鏡語敘事,利用視覺轟炸感官,使感官沉溺于奇觀視效中,或者形成一定意義上的印在觀影人心中的永恒畫面。在影片中,通過片頭的旁白介紹了人類如何逃離的方法,就是利用人類所有的能力建造出一萬臺行星發動機,而地球是依靠這一萬臺行星發動機的推力才得以逃離,影片通過鏡頭的多個角度與多種機位切換,利用不小的篇幅架構出這一震撼場景,首先是從行星發動機的局部開始,鏡頭快速向上拉伸,逐漸體現出一個龐大的巨型發動機畫面,而鏡頭隨之一轉,以一個航拍角度將這一巨型機械以量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一萬臺行星發動機推著地球前進的畫面在銀幕中出現,地球冒著藍色的火焰在星際中前行,呈現出壯麗的星際奇觀景象。對于行星發動機的視覺呈現,影片采用了近景的局部特寫與遠景的星空俯瞰,在近景中通過與人類、運載車等作為對比參照,體現出行星發動機的巨大,在遠景中,通過地球與一萬臺行星發動機組合成星際奇觀。影片對于行星發動機的視覺架構不但使觀眾看到了人類文明在面對災難時的頑強與能力,也通過星際中的奇觀圖像傳遞給觀眾人類在星體災難面前的脆弱與渺小。
二、視覺架構與人文語境
在《流浪地球》這樣一部科幻史詩電影中,不但展現出奪目絢麗的視覺奇觀與具象的災難情境,而且還有著奠定影片現實基礎的人文語境,人文語境為影片提供了一個真實的社會形態,將影像中的虛幻視覺拉進現實維度,對于科幻史詩類影片來說,人文語境的視覺架構空間更多的是觀照影片的現實維度,將影片中的人類生存現狀、社會秩序、人物內心情緒與價值觀等進行體現,在電影語言中,對于人文語境的視覺架構有著奠定影片基調與烘托出影片價值取向的重要作用。
在影片《流浪地球》中,人文語境的視覺架構體現在對生存現狀的現實展現、災難降臨的親情書寫與人類不屈精神的刻畫等幾個方面。首先在人類生存現狀的展現上,除了對地表災難景觀與人類文明奇跡的刻畫,影片構建了幾個反映人文形態的視覺空間,一是在地下城中,影片架構出平民的生存百態,昏暗的地下城背景下人類文明在這里延續,這里依然有商家店鋪,平民們躲在地下城陰暗的環境中,雖然依然在生活,卻在無形中透著一種壓抑,影片的燈光與布景呈現出頹廢破敗的氣息,形成了對災難現狀的現實呼應。二是在領航員空間站,承載著伴飛與守護地球使命的航天員劉培強等人,與地下城眾生的頹廢形成了視覺反差,為影片構建出了信念與使命的人文語境。
而在人文語境的情感刻畫上,影片著墨于親情書寫,在影片中,為了凸顯出災難來臨而不得不面對的人生抉擇與偉大信念,影片從最開始就鋪墊出一個充滿父子溫情而又傷感的畫面,當父親劉培強抱著兒子劉啟,告訴他:“爸爸即將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時,鏡頭下的夜景平靜中卻蘊含著悲壯。而在影片中人類因為行星發動機噴射距離不夠無法點燃木星時,父親劉培強毅然決定犧牲空間站而成全點燃木星的行動,這也意味著他將赴死,影片利用特寫鏡頭展現出劉培強堅毅的面部神態,并在這一階段架設出劉培強與兒子劉啟的隔空對話,傷感的背景音樂中,影片展現出了無比動人的傷感畫面,隨著木星被點燃,父親劉培強在最后用生命兌現了影片最初他對兒子的承諾:“當你不需要拿望遠鏡就能看見木星時,爸爸就回來了”。這一部分的視覺刻畫不僅起到了催人淚下的作用,更是從另一個層面體現出影片的人文關懷,使影片中構建的虛幻災難更顯真實而深刻。
三、視覺架構與自然奇觀
在影片《流浪地球》中,自然奇觀的視覺呈現是影片架構的一個重要環節,這里既有對自身數字特效制作技術水平的考量,同時也是影片實現視覺架構的關鍵。尤其是對于依賴于災難視覺的影片,自然奇觀的架構需要符合影片中敘事情節的需要,同時以突出而新穎的方式博人眼球,進而達到視覺轟炸的目的。自然奇觀的表現又是對于影片災難程度的佐證,對于災難電影的敘事,脫離開自然奇觀的視覺架構會使整個敘事具有無病呻吟的意味,而獨特的自然奇觀反而會為影片帶來極大的關注,能夠吸引到更多的受眾群體,所以,災難電影極力去表現自然奇觀也就不難理解了。在本片中,由于對劇情獨特的思考角度,影片中出現許多非凡的自然奇觀,這些奇觀異景也成為本片有別于其他科幻史詩片的獨特風景。
以影片中架構出的三個自然奇觀為例,在地表空間中,影片營造出了一個極度寒冷,文明盡被冰雪淹沒的凄慘景致,當營救隊眾人開著厚重的運載車來到上海地區時,鏡頭以完整的影像呈現出了被冰雪覆蓋下的上海,城市中的所有建筑已經被吞沒,唯一可辨識的只剩下東方明珠電視塔的殘像,影片鏡頭通過對眾人的表情特寫與姥爺對于往日上海的回憶將災難的殘忍景象進行架構,使這一景象成為觀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災難印記。而在表現天頂異景中,影片卻著力架構出壓抑與絕望的視感,當劉啟一行人運送火石進入永夜之后,仰望天空,一個巨大的木星覆蓋了大半個天空,隨著聯合政府的最后播報宣告地球即將被木星引力吸引而突破洛希極限時,人類所有的掙扎與努力最終變成徒勞,這個最后播報如同死亡宣判的喪鐘,也將所有人都帶入到絕望,影片展現出如同死神的巨大木星懸在天上,大紅斑也像死神之眼一樣凝視著眾生。當眾人抬起頭,仰望木星時,影片以特寫的鏡頭展現出絕望的眾生群像,人們的目光呆滯,眼神中又都透著不甘,心中充滿著對這個美麗星球的復雜思緒,影片在這里利用悲情的音樂與暗淡的色調將這一絕望情境展現得淋漓盡致,而由于影片的渲染,觀眾也對木星這個陌生星球產生了復雜的情感,在視覺的獨特架構下,這個自然景觀最大限度地體現出了自身的圖像價值。在體現星際奇觀時,鏡頭通過遠景的幾個角度體現了星空環境中的瑰麗景象,兩個不同體積不同色彩的星球被并置于同一畫面中,影片中因為地球逃離的特殊原因,使二者產生了關聯,在木星表面散發著黃色氣焰,一個巨大的黃色氣柱拖拽著地球,地球的大氣也被木星的引力牽引而散發出藍色氣焰,地球的尾部在行星發動機的推力作用下形成狹長的藍色尾跡,影片將這一幕展現在人類絕望的時刻,使瑰麗的圖像中蘊含著死亡的意味,影片中的這一幕不僅以獨特的視覺形態震撼了觀眾的審美認知,而且使影片中構建的災難影像更加具有災難史詩的特質。
四、結 語
影片《流浪地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產科幻史詩電影的空白,雖然從影片的制作水平上尚不足以與歐美史詩科幻巨制比肩,在學術領域的縝密性也稍顯欠缺,難能可貴的是影片通過偉大的想象與震撼的視覺效果,構建出了具有獨特美學意味的災難史詩,也使本片具有了國產科幻電影里程碑的現實屬性。影片最大化地發揮了視覺的能效性,通過巧妙的安排展現出影片的深層語義與美學價值,并以此彰顯影片的美學理想與獨特審美格調。在視覺架構與敘事的深度融合下,透過其表層的災難景觀描述,是影片對于人文語境的觀照,同時也是影片對人類不屈精神的頌歌。《流浪地球》開了國產科幻史詩電影的先河,而其在視覺架構策略上的成功值得后來者分析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