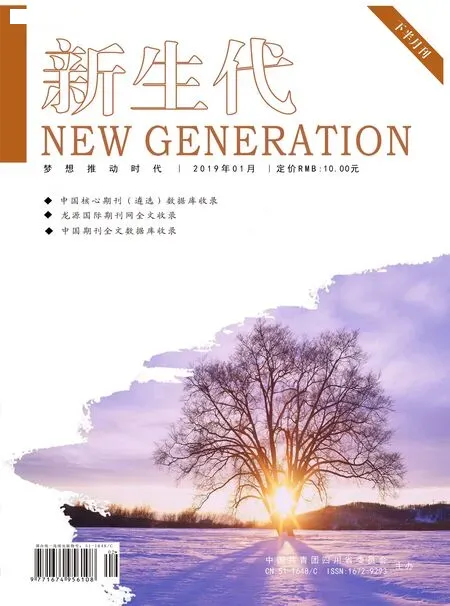淺析《螢火蟲之墓》與《赤足小子》中的意象表達
張雨萌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100024
序言
1945年之后,日本各行各業(yè)逐漸進入了恢復(fù)期,動漫行業(yè)也隨之復(fù)蘇,進而取得了飛速發(fā)展。在題材紛繁的日本動畫中,二戰(zhàn)題材始終占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日本國寶級漫畫大師手冢治蟲創(chuàng)作的《鐵臂阿童木》到2016年上映的頗具口碑的動畫電影《這世界的角落》,隨處可見戰(zhàn)爭對于日本動畫的深遠影響。
美國學者蘇珊·j·納皮爾在她的著作《ANIME》中曾寫到:“在描寫二戰(zhàn)題材的日本動畫電影中,最出名的兩部要數(shù)《赤足小子》和《螢火蟲之墓》了。這兩部影片從片中主角的個人角度出發(fā),以自傳的形式為我們展現(xiàn)出那個集體主義語境下的日本記憶。”在這兩部經(jīng)典的日本動畫電影中,戰(zhàn)爭的殘酷和反戰(zhàn)思想表露無遺,但更耐人尋味的,是一系列意象背后的文化根源與心理依據(jù)。本文將通過對比《赤足小子》和《螢火蟲之墓》兩部影片,淺析影片中諸多意象背后的含義。
一、影片的時代背景
戰(zhàn)敗后的日本,從1950年代后半期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的時期,直到1970年代初,經(jīng)歷了“神武景氣”、“巖戶景氣”等大型景氣的日本,漸漸從戰(zhàn)亂的廢墟中恢復(fù)過來,國民生產(chǎn)總值也一度直逼美國。但進入八十年代,這種高速增長的模式有所減緩。1980年代中期,日本經(jīng)歷了所謂的“泡沫經(jīng)濟”時期,經(jīng)濟市場開始陷入低迷。另一方面,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天皇制與家族制所代表的封建主義制度幾近崩潰,人們的價值觀也發(fā)生了變化,更加趨向于“自由”和“多元”。這種經(jīng)濟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動蕩勢必影響到文化的層面,《赤足小子》和《螢火蟲之墓》正是基于這樣的時代背景而產(chǎn)生的。
二、影片概述
《螢火蟲之墓》在一片灰暗蕭條的景象中,以男主角清太的一句自白“我死了”奠定了影片凄美悲情的打開方式。螢火蟲若隱若現(xiàn)的光輝,仿佛清太奄奄一息的生命,清太的靈魂已從虛弱的肉體分離出來,隨著地上的糖果罐子,終于與異世界的妹妹節(jié)子重聚。
相比于悲情凄美的《螢火蟲之墓》,赤足小子的基調(diào)則要更加“勵志”。影片開頭就是一片翠綠色的麥子地與小元父親充滿男子氣概的演說:“麥子啊,渡過嚴酷的嚴冬,不依不饒地在大地上發(fā)芽……”。本片主要從男主人公小元的視角,講述了二戰(zhàn)時期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顆原子彈后,日本終于無條件投降,在這次災(zāi)難中失去了父親、姐姐、弟弟的小元與母親和剛出生的妹妹相依為命的故事。在影片的結(jié)尾,小元與隆太看到土地上新長出的麥子芽,想起了父親說的話,于是重新振作起來,決定要堅強地活下去。
三、“小元”與“清太”
《赤足小子》中的“小元”似乎一直“在陽光下奔跑”,在那個悲慘的時代,父親的鼓勵給予了他莫大的支持。小元的父親是個堅定的“反戰(zhàn)主義者”,痛恨戰(zhàn)爭與發(fā)起戰(zhàn)爭的日本政府,認為“政府”是在迫害人民。而從父親那里繼承而來的鮮明的反戰(zhàn)思想也使得小元的內(nèi)心沒有太多反復(fù)與掙扎,這一點在小元哼唱反戰(zhàn)歌曲這個情節(jié)中顯現(xiàn)出來。因此,小元和母親的那種在經(jīng)歷了核爆災(zāi)難后的悲傷與憤慨就顯得格外純粹,是一種“血與淚的控訴”。與此相比,《螢火蟲之墓》對于主角清太的塑造就更為復(fù)雜。從影片中清太看到螢火蟲聯(lián)想到參觀軍事演習,并高唱軍歌的情節(jié)可以看出清太原本對于戰(zhàn)爭的理解是較為正面的,但后面清太唱到一半的戛然而止,體現(xiàn)出了清太的掙扎與迷茫。在聽到“大日本帝國戰(zhàn)敗”與父親所在的艦隊沉默的消息之后,清太更是陷入了混亂與絕望。節(jié)子的夭折無疑是壓倒清太的最后一根稻草,讓清太失去了最后的希望,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這種矛盾的扭曲,一方面增加了“清太”的角色維度,與旗幟鮮明的小元形成了強烈對比,在加深了影片悲情效果;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日本究竟是如何在“民眾的擁護聲”中將自己推向修羅場的,更能引發(fā)人們對于戰(zhàn)爭的思考。日本的這一系列“天災(zāi)”,又何嘗不是“人禍”呢?
四、日本人的“依賴心理”
說起清太“孤獨地死亡”這一情節(jié),究其根源,則不得不提及日本著名精神分析學家土居健郎在《日本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一書中提及的“依賴心理”這一概念。漢語語境中的“依賴”不盡相同,這里的“依賴”指得是一種“相互容納的,被動的愛”。簡而言之,就是內(nèi)心深處的一種對于“被愛”的極度渴望。這種渴望是人類欲望深處的,本能的存在。土居認為,這種“依賴心理”存續(xù)與日本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這是由于日本人已經(jīng)把相互依存的人際關(guān)系貫穿到社會規(guī)范之中,所以在日本依賴心理得以發(fā)達。那么,接下來我就從“依賴心理”的概念出發(fā),解析下面的諸多意象。
1、女性角色
在這兩部影片中,“母親”都是女性角色中的重要人物。土居認為,“依賴心理”是一種在嬰兒時期形成的心理活動。當嬰兒逐漸意識到自己與母親各為一體,而感覺自己不能離開母親的時候,“依賴”就產(chǎn)生了。不僅如此,“孤獨感”也誕生于這一時期。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梅蘭尼·克萊因在其著作《嫉羨與感恩》一書中曾經(jīng)提到,“孤獨感”來源于嬰兒的一種無法被滿足的渴求,當他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母親”的渴求無法時時刻刻都被滿足時,就會產(chǎn)生這樣的心理活動。因而“母親”這一意象本身,就帶有著“依賴”的意味。而母親角色的缺失(死亡),則代表了這種內(nèi)心深處的渴望趨于終止,從而營造出一種深層次的孤獨。
除此之外,女性角色通常也被認為是文化根源的象征。這一點在《螢火蟲制之墓》中也有所參照,當清太帶著節(jié)子到海邊玩耍,海風拂面,清太想起了媽媽生前的樣子。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日本傳統(tǒng)女性形象,穿著粉紅色的和服,輕輕舉著粉紅色的傘,一陣風吹過,傘被吹落在沙灘上。隨風舞動的裙擺,盡顯女性的柔弱溫情,櫻花一般,如同日本的文化情懷。而天真的節(jié)子與《赤足小子》里剛出生的友子,則代表了文化中最純情文弱的部分。她們支撐起清太和小元的精神世界,是“幸福感”和“快樂”的源泉,并在災(zāi)難降臨之后,給予他們生存的希望。
但是,戰(zhàn)敗后的日本,受到了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沖擊,傳統(tǒng)封建天皇制與家族制的禁錮被解除,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已經(jīng)建立起了如同西方社會一樣的個人主義的思想觀念,“思想的解放絲毫沒有減弱人們相互依賴的心理,反而造成日本精神和日本社會的極度混亂。”而友子與節(jié)子的死去,恰恰體現(xiàn)出創(chuàng)作者對日本傳統(tǒng)文化在這樣極度混亂的社會情景之下能否存續(xù)的深深擔憂。《螢火蟲制之墓》中,節(jié)子在最后抱著清太,呼喊著“不要離開我……”,則也是傳統(tǒng)文化的呼聲。
2、父親
“父親”是兩部影片中極為重要的意象。而在這兩部影片中的父親角色又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赤足小子》中小元的父親是一個“有存在感”的父親。在影片開頭一直到影片中部,小元的父親都占據(jù)了相當?shù)膽蚍荨6≡诟赣H的鼓勵和家人的陪伴下,他那見證了“慘絕人寰的災(zāi)難”的幼小心靈,并沒有受到極大的扭曲與顛覆。甚至在母親因目睹丈夫和兒女的死亡而陷入崩潰的時候,是小元將母親從火場拖走,救下了母親和尚在腹中的妹妹友子。小元腦海中,似乎始終回蕩著父親對自己的教導(dǎo),模仿父親的樣子,學著如何成為一個男子漢。相較之下,《螢火蟲之墓》中小元的父親就是一個幾近“虛無縹緲”的存在,蘇珊·j·納皮爾曾提到,“清太的父親是海軍軍官,代表的是政府的一方”。而這種“縹緲”的感覺與二戰(zhàn)時期政府“虛無縹緲”的存在感相一致。就像清太的父親只存在于別人的話語中,相框里的照片中和清太的記憶中那樣,“日本政府”也只存在于廣播和火葬場周圍。
更深層次去發(fā)掘“父親”一詞的含義,不禁會想到日本的“父權(quán)文化”。以天皇制和家族制為首的父權(quán)制度在日本戰(zhàn)后分崩離析,開始進入“父權(quán)失墜”的狀態(tài)。經(jīng)歷了這場浩劫的人們,終于認識到了以往所謂的傳統(tǒng)“義理”已然腐朽破敗,此時,人們強烈迫切地想要有所依靠的愿望收到了極大的挫敗。年輕的一代開始不斷地懷疑甚者拋棄以往父權(quán)文化語境下的許多觀念。然而,從《赤足小子》的結(jié)尾我們不難看出,其實人們內(nèi)心對于強大的父親形象的指引和回歸還是充滿期待,希望能夠重塑一個偉大的父親形象。
3、“家”
“家”的意象在這兩部影片中都占據(jù)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螢火蟲之墓》中,清太和節(jié)子在家被燒毀后一直試圖建立并守護他們自己的“家”。無論這個家有多簡陋,對他們來說,都如同之神天堂。節(jié)子死后,火化的那一段情節(jié)中,背景音樂的歌詞則強調(diào)了“無處為家”的凄涼。也為清太的一蹶不振埋下伏筆。《赤足小子》中的小元之所以能夠堅強的活下去,也是因為有家人的陪伴。這其中也體現(xiàn)出日本人內(nèi)心深處對“家庭”深深的依賴。
4、“被害者形象”與“被害意識”
然而無論是怎樣的主題,我們總是能在許多二戰(zhàn)題材的影片中看到日本人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控訴戰(zhàn)爭帶給人民的痛苦之時,似乎完全沒有考慮過作為真正“受害者”的被侵略國國民的感受。究其根源,日本人之中強烈的被害意識也與“依賴心理”脫不開關(guān)系。
無論是戰(zhàn)爭中受害的民眾,還是受傷的“日本大兵”,“被害者形象”甚至于影片各處,以至于有時我們會忘記這是在看一部“描寫侵略國”的影片。土居健郎在“受迫害感”這一章節(jié)解釋說,“受迫害感”起源于受干擾的意識,這種受干擾的意識正是“依賴心理”的體現(xiàn)。而“加害心理”則“是受害心理受干擾之翻版”,因此這種加害心理便很容易轉(zhuǎn)換為受害心理而存續(xù)。因而“被害者形象”也是根植于日本人內(nèi)心深處的一種真實寫照。
五、影片中的生命意象
《螢火蟲之墓》中的螢火蟲是貫穿整部影片的線索性的存在,也揭示了創(chuàng)作者想要在這部影片中索要表述的生命觀——生命,美麗卻又短暫。在贊嘆生命美妙的同時,又強調(diào)了生命的脆弱易逝。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正是明白了生命的脆弱與短暫,人們才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呼吁和平,感恩和平。
而《赤足小子》開篇那一片綠油油的麥子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麥子”這一意象背后,則體現(xiàn)出了與《螢火蟲之墓》截然不同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觀念。與之相似的,還有小元的頭發(fā)。之后,小元的頭發(fā)也全部都掉光了。不過幸運的是,小元并沒有因此而死,在影片的最后,小元和弟弟隆太在一片土地上找到了新長出來的麥苗,小元的頭發(fā)也長出來了。這種“生生不息”的思想觀念,為當時處于社會“精神動蕩”期的年輕人提供了方向,無論經(jīng)歷過怎樣的動蕩甚至是災(zāi)難,總有一天將會好起來的,就像麥子總有一天將會發(fā)芽。
六、結(jié)語
通過分析這兩部優(yōu)秀的動畫影片中的意象,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文藝做作品與時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會心理方面的緊密聯(lián)系。藝術(shù)作品的內(nèi)涵,與創(chuàng)作意象的選擇和表達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希望通過這樣的分析比較,可以在將來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有所滲透,從而增加藝術(shù)作品的表達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