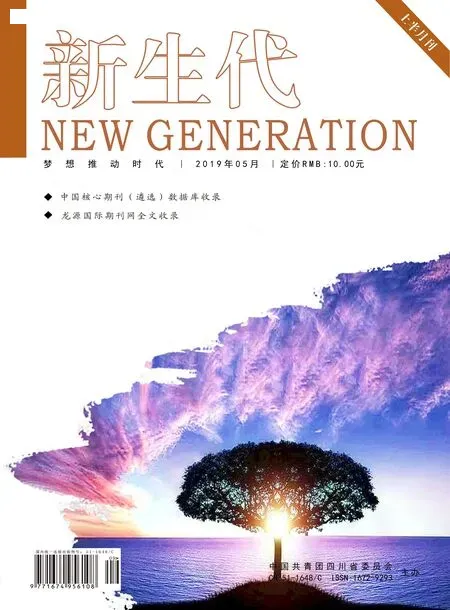馬克思生態哲學思想初探
汪燦榮 天津外國語大學 天津 300204
一、馬克思生態哲學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對象性活動是馬克思生態哲學思想的出發點
對象性活動,是主體通過工具作用于客觀自然界的過程,生態問題的產生就是因為主體人在對象性活動的過程中價值取向不正確所導致的惡果。馬克思批判以往的舊哲學家“對對象、現實、感性,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他們本沒有從人的實踐活動和主體能動性的角度去理解。在實踐關系中,人與自然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人類社會的進化與發展也正是由于人與自然二者之間不斷進行的物質、信息和能量的變換所推動的,但是自然界并不能為人類提供現成的物質資料,人類必須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來改造自然,從中獲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源,這就說明了實踐活動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的關鍵,它創造著不同于思想客體的感性客體。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這種對象性關系的存在中,人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自然是人的對象性存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就內在于對象性活動之中。
(二)資本主義是造成人與自然異化的真正根源
我們知道,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和諧便會導致生態問題,其實質則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資本主義社會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以及生產方式即是導致這種異化的根源。馬克思表示,人和自然關系異化所帶來的生態問題,歸根結底是人自身的原因。當今社會世界范圍內的環境污染及各種生態問題的出現,究其根本便是人類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不協調所導致的后果。
近些年來,由于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國家開始意識到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制定了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同時發展了不少循環經濟和生態產業,對生態危機的加重有一定的緩解作用。但是由于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自私本性,只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沒有認識到生態環境的保護應是全球性的問題,地球上每一個民族的共同責任,因此,他們在重建人與自然物質變換關系的同時,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的優勢地位,將一些具有嚴重污染的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來獲取高額利潤。殊不知,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生態危機向全世界蔓延的情勢下,一旦發展中國家環境破壞狀況嚴重,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便無一幸免。
(三)共產主義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對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破壞,因此,重新構建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發展的關系,要改變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他尖銳地指出,防止人類對生態系統平衡的破壞。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改變了人類經濟上的貧窮和精神上的貧瘠,從而實現的人的真正本質,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在自然解放的基礎上,解放了人類自身,同時公平的享受自然與社會和諧之美,馬克思提出,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才能和諧相處。
二、馬克思生態哲學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拒斥現代性意識的侵蝕
馬克思對于生態危機的診斷體現出的思維傾向,讓我們重新對現代性文明進行反思,正是這個曾經帶給人們無限豐富的物質財富的文明,在走向他的反面,同樣攜帶著我們走向毀滅。而之前批判的資本主義只是現代性其中一個表現形式,其根源在于這種現代性意識形態對人的控制和支配。
從啟蒙運動的到來,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劃分,割裂了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們開始了一種理性主義統治的時代,主張用理性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滿足人的主體性的實現。這種理性的高揚在人的心中扎下了跟,把人看成是機器,自然是機器的原料,它們把自然改造的面目全非,也喪失了價值和本真的狀態,毀滅的人和自然的靈性,用孤立和短視的眼觀來看待發展,而造成人和自然的破壞。由于現代性的內在邏輯本身就在威脅著人類生存的境遇,因此如何正確的對待現代性問題就至關重要。但是,現代性意識的操控帶來的危害總是隱藏在財富和先進之后的,當人們沉醉于這種“文明”帶來的種種虛幻世界時,讓人喪失思考和反思的能力,我們只有先破除眼前現代性帶來的虛構世界,才能找到真實的現實世界,那才是人們的此岸世界。
(二)有助于培養公民的生態環保意識
當今全球性的生態危機是人類在處理自身與自然之間關系時錯誤的價值取向所導致的,人類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顧長遠發展,自然界進行無節制索取的結果。換句話說,這種生態危機的形成是由于人類沒有擺正自己在人與自然關系中的位置。長期以來,人類都把自然界看作是自己的奴仆,毫無節制的獲取自然資源,又將一切生產和生活垃圾又直接投入到自然界中去,沒有考慮到自然界的承載能力,沒有認識到自然界也會有承載的極限。但是人比動物更為高級之處就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意識指導下進行的。因此,當代社會要從根本上消除生態危機對人類的威脅,先要從人類的觀念入手,使全人類樹立一種生態環保的意識。
馬克思認為,自然界是人類的衣食父母,不僅提供人類生存和發展所需的物質資料,且自然界還是人的對象性存在,人類要通過實踐活動來確證自身的存在。因此,人們要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的過程中倡導生態實踐,自然界給予人文關懷,即開展有利于環境保護的實踐活動,如對野生動物的保護、退耕還林、減少私家車的數量、對生活和生產垃圾的分類處理等等,并且通過諸如此類的環保實踐活動來推動生態環保理念的大力宣傳,而使全民都參與到生態環境保護的實踐中來,以此來促進人們盡快地樹立起生態環保意識,而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
(三)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哲學依據
近代以來,由于不斷上演的科技革命促使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因此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增強,盲目的樂觀導致了自然界對人類的威懾力日益下降,人類只顧眼前利益,面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并通常以 GDP的增長率作為衡量社會發展的尺度,忽略了這種增長有時是以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破壞為代價的,也沒有考慮到自然生態環境對后代人生存發展的承載能力,這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當人類開始意識到破壞自然生態環境將對自身的生存和繼續發展造成威脅之時,開始反思這種生態問題產生的原因并探尋解決方法。
馬克思的生態哲學思想中關于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和諧統一的思想恰好為當今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提供了哲學依據。早在 1844 年的《手稿》中,馬克思就在對勞動過程的論述中不斷地強調勞動的可持續性發展,尖銳地指出人類不顧自然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一味追求經濟利潤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之下是無法正確認識人類的勞動實踐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他說:“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完全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土地改良后傳給后代。”在上述的這段話中,他明確地闡述了人類作為土地的使用者而非占有者,必須善待土地,保證后代人最基本的生存基礎,這充分地表達了他希望通過尊重自然和善待自然而達到自然資源永續利用的價值理念。因此,我們要繼承馬克思的這一偉大思想并以此作為指導,深刻認識到我國乃至全球深入貫徹和落實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必要性。
三、結論
當然,《資本論》中確實存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但在我們看來,這種思想并不必然導致環境危機,不能成為生態危機的思想根源。正如馬克思所說:“像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他都必須這樣做。”問題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這種態度,是我們今天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所必須堅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