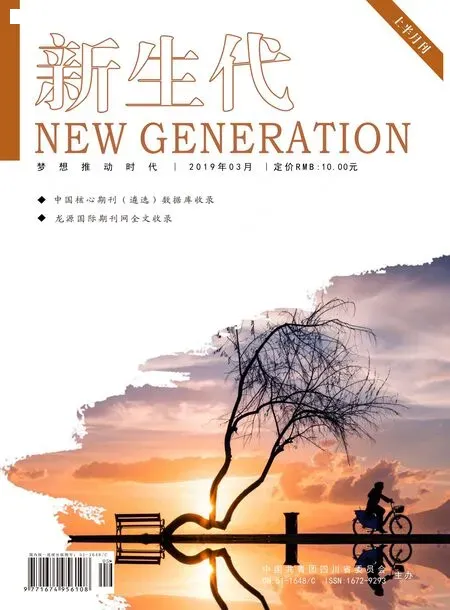2018年土耳其里拉匯率暴跌原因分析
陳安邦 云南民族大學
自2018年6月成功謀求連任以來,埃爾多安在國內權力大增。土耳其央行也在連任后推出了首個貨幣政策,主要是為了維持17.75%的利率,借以降低土耳其國內的通貨膨脹;根據數據顯示,6月土耳其通脹率就達到了15.4%,這是土耳其十五年來的最高通脹水平。2018年土耳其里拉一直面臨著拋售的風險。這可能導致土耳其未來的通脹進一步上升,加劇其國內經濟危機。從宏觀方面看土耳其貨幣暴跌主要有一下幾個原因:
一、美土關系惡化是里拉暴跌的政治因素
土耳其里拉貶值的根源在于國內長期的政治經濟問題,但造成2018年里拉快速貶值的原因卻是逐漸走向惡化的美土關系。
美土關系的惡化,始于埃爾多安對中東事務的積極干涉和參與,在敘利亞內戰初期,面對共同的敵人阿薩德與伊斯蘭國。美國與土耳其還能在對敘問題上達成一致和共識。然而隨著敘利亞局勢逐漸穩定,特別是敘利亞當局在俄國的扶持下成功擊敗反對派并穩固政權之后。美土對部分問題尤其是對待擊敗了伊斯蘭國的庫爾德人武裝的去留產生了的激烈的分歧。一方面,美國扶持庫爾德武裝繼續打擊伊斯蘭國殘余并且希望在敘利亞東部地區建立一個類似于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的國中之國;另一方面,土耳其出于自身國家安全考慮并不希望在國境線附近出現一個新的“庫爾德斯坦”之類的勢力;因為這無疑會鼓勵和刺激土國境內庫爾德勢力加強分離運動。為此土耳其在庫爾德人控制的阿夫林地區的發起的強大攻勢,得到了俄羅斯的默許,也遭到了美軍的抵制,美軍和法軍源源不斷降落在敘利亞庫爾德地區,修建訓練營和野戰機場。在事實上阻隔了土耳其軍隊和敘利亞庫區,阻撓了土耳其軍方的行動,進一步撕裂了美土關系。
2018年4月,土耳其對涉及居倫一案的美籍牧師布倫森進行審判,美方多次要求釋放布倫森,雖遭到土方強硬拒絕,但7月布倫森被改判為軟禁于家中。特朗普于同則于7月27日在推特上發文并表現出強硬姿態,要求土耳其立刻釋放布倫森否則將對土方進行嚴厲制裁。土耳其對此不屑一顧,另外土耳其軍隊準備購買俄制S-400防空系統這一事件導致美國極為不悅,最終停止向土耳其銷售先進戰機F-35。除了外交和軍售,美國還在經貿方面加強制裁,并開始波及金融市場,美國首先對土耳其鋁關稅調整為20%、鋼關稅調整為50%,隨后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宣布對土耳其的特惠免稅待遇進行重新審查。此舉使土耳其里拉伴隨著暴跌模式進入8月,導致土耳其國內金融危機徹底爆發。
二、土耳其經濟發展的缺陷是里拉暴跌的國內因素
截止2012 年底,里拉對美元的匯率還在維持在1.8左右,2013年則匯率降低至2.0,2015年底接近3.0,2017年初匯率逐步接近4.0。從這4年數據來看,土耳其面臨著匯率貶值的嚴重金融風險,這種風險其實早就被金融界所關注。只不過近期由于美土爭端,土耳其里拉匯率貶值的風險又重新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這些風險是土耳其經濟發展長期累積的必然惡果。里拉對美元的匯率從7月中旬到8月中旬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從4.5暴跌到7.0的水平,此后匯率雖然有所恢復,但急劇的貨幣貶值導致土耳其陷入嚴重的金融動蕩,即使危機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平息,土耳其的經濟與金融行業也需要經歷數年的事件才能得以喘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土耳其在全球新興國家中表現突出,多次經濟增速突破10%的大關。根據土耳其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8年土耳其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為7.2%,出口是拉動土耳其經濟的主要動力。這一增速超過市場預期。然而風光的背后隱藏著無數危機,土耳其第二季度增速降至5.3%、第三季度受貨幣貶值影響甚至降低到1.6%。土耳其經濟自身就隱藏著各種各樣的隱性風險,貨幣貶值只是加速了經濟危機的爆發。
從土耳其貿易來看,首先是巨大的貿易逆差占其GDP總量比重過高。2011年對外貿易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高達9%,雖然之后幾年比重略有降低,但逆差占GDP比重依舊在4%到5%之間徘徊。特別是2018年第一季度,該指標則再次惡化,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突破了6%,由于里拉的貶值,經常項目逆差將會進一步擴大。這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需要外國資本持有大量的本國債務,而外資進入某國的債務市場的前提就是資金能夠順利流動出入。這種對外國資本的妥協也變相打開了資本賬戶,將會使得債務國失去對本國資本的監控能力,土耳其亦為如此。
其次,土耳其近年來主要靠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擴大財政支出等手段帶動經濟增長,金融政策上通過行政手段降低銀行利率。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模式極易造成經濟泡沫和金融結構性問題。第一:為了推動經濟增長,土耳其擴大了財政支出,并大規模推動PPP項目。此舉雖然帶動了經濟增長使得土耳其在2017年交出了增速為7.4%的滿意答卷,甚至比2016年增加了4.2%,然而經常項目赤字進一步擴大,2017年此項指標擴大為5.5%同比2016年的3.8%暴增了1.7%。特別是2018年上半年開始,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貶值。因此土耳其經濟如果以美元計算反而是負增長。第二:通貨膨脹抵消匯率貶值帶來的出口紅利,自2011年以來土耳其通脹水平一直保持在8%左右,居高不下。這導致國內進口需求暴增,由于高通脹帶來的高物價,市場更愿意通過進口的方式滿足國內需求。此舉不僅抵消了土耳其匯率貶值帶動的出口紅利,還進一步擴大了貿易赤字,進一步加重里拉的貶值。第三:土耳其產業結構的缺陷。土耳其旅游業與農業十分發達,但是其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以及中高端制造業十分匱乏,沒有形成相關的工業支柱,基礎產業鏈不完善,特別是出口工業產品以鋼鋁等初級產品為主,沒有競爭力,其產業無法起到穩定匯率的作用。第四:錯誤的央行利率變動。低利率與通貨膨脹相結合是不可持續的貨幣政策。土耳其央行沒有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來保護匯率,這其實是埃爾多安大權獨攬后為追求支持率和經濟增長而行政手段故意壓低匯率。埃爾多安認為,高利率對窮人是一種“剝削”并且會抬高土國內融資成本,不利于經濟發展,盡管高利率可以保護匯率。面對貶值,土耳其央行并非沒有行動,曾經于2014年進行加息來穩定匯率。然而在2015年到2017年間,土耳其基準利率并沒有太大變化。此舉是希望借助低利率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卻將匯率置于無保護的狀態之下,一旦匯率貶值,崩塌的金融市場信心會使得加息這種辦法毫無用處。目前土耳其的基準利率已經達到了24%,在這樣的利率水平下,盡管2018年年末里拉匯率已經相對穩定,高基準利率將會使經濟發展異常困難。
三、美元與美國經濟是造成里拉暴跌的國際經濟因素
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經濟強勁復蘇,FOX電視臺總結2017年美國失業率為17年來新低。美國經濟的復蘇,帶動了美元的上漲,黃金價位在2018年一直處于下跌趨勢。以上消息對于相關新興經濟體都不是好消息。從尼克松時代開始,每次美元升值走強,都會無意間引起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上世紀80年代拉美金融危機與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都與美元走強相關。如今新興市場國家與老牌發達國家患上同樣的經濟問題——凈債務與GDP比率的水平都處于最高水平,風險居高不下,在新興經濟體中最脆弱的,正是里拉。隨著美元不斷走強,再加上2018年美聯儲不斷加息,截止12月19日美聯儲已經將基本利率提高到2.25%-2.5%,美國長期債務收益率有望上升,將會導致全球資本向美國流動,與此同時也就代表著新興經濟體國外資本流出增加,流入減少。對于這些國家很可能就造成匯率貶值,對于這些國家的經濟實體而言,如果本身負有美元債務,強勢的美元會導致融資成本增加、融資困難以及財務成本暴漲,破產幾率大增。土耳其2017年總體外債為768億美元,彌補土耳其資金缺口的都是外國投資。多年來,土耳其外債規模不斷擴大,2017年外債漲幅甚至高達11.15%。不妙的是,截止2018年2月,土耳其外債已經高達4666.6億美元,占土耳其GDP比重高達53.3%。土耳其外匯儲備自2013年呈現萎縮態勢至2018年8月其外匯儲備僅為689億美元,僅為外債規模的 1/6。由此可見,不斷惡化的國際收支,美元的持續走強與美國經濟復蘇,都是導致里拉暴跌的國際經濟因素。
四、警惕土耳其危機對新興經濟體的沖擊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復蘇也一直領先于新興經濟體甚至領先于歐洲,這無形中強化了美元的價值與地位。美國利用其全球領先的經濟地位,動輒對部分在政治上不配合其國策的新興經濟體進行制裁,往往造成外資逃跑,對新興經濟體形成踩踏效應。土耳其本身就需要外資填補巨大的資金缺口,而一旦里拉大幅度貶值,最終仍然需要外資來緩解困難。
目前來看,土耳其危機已經不是國內危機,但其傳染效應已經波及到歐元和其他相關經濟體。一方面,如若美元對各個新興經濟體貨幣繼續升值,當前一些經濟較差的國家,會面臨巨大經濟壓力,特別是俄羅斯已經在本輪里拉危機帶來的沖擊。這符合美國制裁和打壓俄羅斯的既定國策。另一方面,美國通過對土耳其的制裁,落井下石,通過土耳其影響歐元區經濟,打壓歐元向心力,提高美元的競爭力。
從新興經濟體角度來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都可能成為借此投機目標,這些經濟體共同的問題就是是經常項目赤字較高或者海外資本在國內債券市場的占比較高。國際資本基本符合采取“順周期”效應,通俗的說就是漲時助漲、跌時助跌。頻繁的資本流動也給經濟體當局帶來了巨大的管理困難。
而如果問題進一步擴散,那么市場表現良好的國家也難以避免受到“沖擊”,經濟危機的傳染性表現為匯率的大幅貶值與資本的大幅流出。由于國外資本的快速流出,盡管很多新興經濟體保持著良好的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速,但迫于體量小且產業不完善、不發達,往往無力抵擋這種釜底抽薪式的資金外逃與金融沖擊。這個時候就需要可能或者已經受到金融沖擊的國家頒布預防性舉措。因為在金融危機面前,市場信心極易崩塌,危機到來后的任何舉措都可能被市場進行反向解讀,從而造成更加難以管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