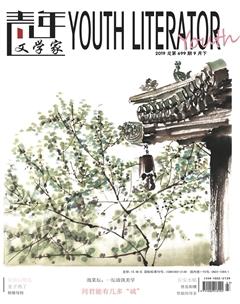《立春》電影特點及電影語言分析
馮華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7--01
電影《立春》是顧長衛導演所導演的專注邊緣群體的劇情片,電影鏡頭剝離時下的流行元素,而是將最平實的語言鏡頭娓娓地向受眾鋪展開來,鏡頭、構圖及色調等等多種電影元素及語言的運用,極大地增強了電影人物的真實感。
電影主要講述的是在改革開放后期的一個閉塞的縣城中,抱有歌劇癡迷向往的王彩玲成為了民眾眼中的異類,她放棄一切只為追尋,而夢想卻被現實打敗。這無疑不是一個小人物的悲劇,使王彩玲這樣擁有“夢想”的人群成為了“沆瀣一氣”的組織,他們的夢想難以實現,只能無情地逡巡在他們的現實周圍,他們不僅僅是別人眼中的“魚刺”,實則不然,他們的向往也成為了他們自己的“魚刺”,他們不想拔出也不能拔出,或許它連同著經脈與靈魂,一旦剝離身體她們也就喪失了自己,所以《立春》不僅僅是王彩玲一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下一群人的無奈。
立春是希望的開始,一切在此刻都是欣然之態,立春之時,向前走是溫暖,向后退是寒冷,就是一步的距離,它們也確實是劇中人物現實和理想的距離。電影從煙囪由暗到深的引入,高聳的煙囪凸顯出了明確的年代感,后面鏡頭切換到人群騎行的鏡頭,前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煙囪的高聳給受眾一種孤清難以觸碰之感,而后面蜂擁的人群讓人感受到了一種世俗及愚昧之感。電影開場需要介紹全片的基本的情境,在聲畫協作的表現下需要體現出故事的時間,地點等基本信息,甚至也需要用象征的手法按時主體思想與任務的命運,而顧長衛導演通過開場的精心構建,來通過反差甚至帶有戲謔的效果為王彩玲的出現形成了鋪墊。
在《立春》中,鏡子也成電影體現人物的重要符號。王彩玲接受了周瑜的教他唱歌的請求,王彩玲對著鏡子自彈自唱,閉著雙眼完全沉浸在音樂中,伴隨著她的歌聲周瑜直視鏡子里的王彩玲,仰慕的情感油然而生,這不僅是來于對王彩玲本身,而是對于一種美好藝術的純粹向往。鏡子往往有注視自我、深入靈魂的作用。在這一段落中,一曲唱完,王彩玲看著鏡子里的自己。鏡頭此時沒有任何的變化,也不移動,也不對焦,畫面此時相對靜止,此時的鏡頭不是為了敘事,而是為了體現人物及渲染情感服務的,這種靜止的鏡頭與王彩玲的面容及聲音形成的強烈的關系,并且大量的深色背景與略顯光亮的鏡子強烈的對比,一種壓抑感不言而喻,也深沉地體現出了人物的孤獨與無助。從視覺語言上來說,運用鏡面的反射可以使人物與鏡中人像形成照應,營造實與虛、真與假的關系。
在整個影片中運用鏡子表現人物的還有胡金泉最后的一段芭蕾舞,那樣的一個決定,對于胡金泉來說是一種解脫,也是新的“束縛”的開始,而最后這一段芭蕾舞有一種無畏的涕零感和悲壯感,他全程幾乎注視著鏡子,音樂、表情與肢體有一種變態的扭曲之感,就如同電影《黑天鵝》中妮娜最后那一支舞,極具絢爛卻又有回光返照之征兆,這也是一個最美的涅槃過程,燈光似舞臺的追光,既渲染出一種無力的蒼白,又凸顯出一種孤獨的力量,相駁之力充斥著無限的力量與能源,而鏡像又似乎在影射著一種生活、一種志向近在眼前的咫尺,卻有虛于飄渺。
影片中最為吸引人的兩個鏡頭是王彩玲兩次來到天安門廣場的長鏡頭。導演充分運用了景深鏡頭,透過虛實的交映構建出不同時期的人物心態及歷程。
第一次王彩玲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時,導演將王彩玲及行李聚焦,將天安門及一切物體進行虛化處理,形成了有一定景深的視覺畫面空間,將人物與景物通過虛實的方式呈現斷離,體現出人物的孤寂與無力之感,并且也強烈地體現出人物對夢想的向往和對北京的迷戀。王彩玲趴在欄桿上,用實際的物品將王彩玲與向往的最具有北京代表性的地標進行隔離,體現出人物的理想與現實的距離感,將原本無形的距離通過有形的方式進行表現,在景深空間里出現了巡邏的軍人,一種無形的力量,使得受眾更加感受到了人物的渺小和前進的渺茫。整體色調偏深,王彩玲也穿著暗黑色調的衣服,孤獨的背影被對焦,而明亮的熱鬧的天安門作為失焦的背景,無論是從色彩還是從畫面空間來看,都與王彩玲孤獨的背景和冰冷的心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長鏡頭的運用使受眾能夠真實感受到“虛擬”中的真切,使得鏡頭更為莊嚴肅穆,并且留出足夠的時間即空間讓觀眾進入導演所營造的電影世界。
第二次是王彩玲帶著領養的女兒在天安門廣場游玩,與第一次出現進行對比:整個畫面的色彩更為鮮亮,并且沒有對天安門進行過度的失焦處理,將人物和整個背景進行融合;人物的服裝色彩也更加跳躍;沒有柵欄等其余外來力量,使畫面更加開闊;背景中融入多種積極因素,例如穿校服的小學生,冉冉飄升的紅旗等。此鏡頭也是運用了長鏡頭,整個鏡頭無論是色調還是構圖都有了積極的轉變,但是在畫面之下似乎也體現出人物的一種無奈,天空雖然明亮了,一切似乎明朗了,但是王彩玲的夢想到底去了哪里,她似乎也成為了庸庸碌碌的一員,女兒也成為了他生活的中心,取代了藝術在她心中的位置,她的心不再是為藝術而生,而是回歸了世俗,找回了平凡,但是這對于王彩玲是不是一種無奈和一種失去。
《立春》的結尾似乎成為了導演留給觀眾的一個謎題,但是從父親的那一滴眼淚中我們看到,至少王彩玲實現了別人眼中的“幸福”,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家”,而她的真正幸福吶,這份答案我們只能捫心自問,也如同顧長衛導演說的那句話“特別地道的理想主義者,其實意味著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