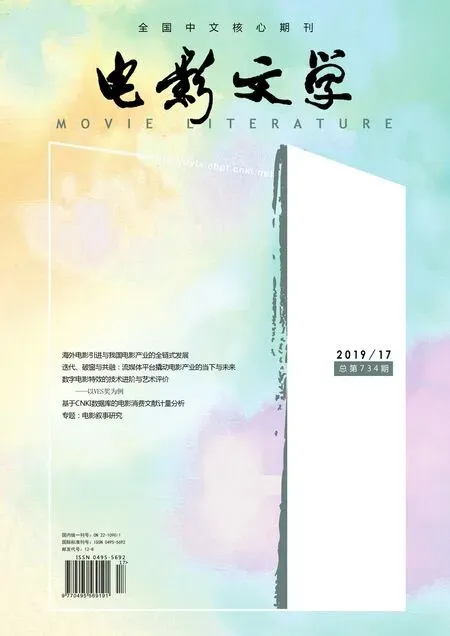《老師·好》場景設計中的符號表現策略
張 引(海南師范大學 美術學院,海南 海口 570000)
電影《老師·好》的成功離不開兩點,其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這一身份在中國的儒家文化里是僅次于“天地君親”的長者,有著崇高的形象,描寫老師的詩詞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奉獻精神。影片摒棄了傳統思維中老師的至高無上,奉獻至死的精神,辯證地弘揚了其師德師風,產出的是現實生活中真實樸素的老師形象,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其二是近年來以校園為題材的電影主要以學生視角進行拍攝,突出了青春的色彩。電影《老師·好》一改往日校園背景影片描寫的側重點,關注了老師這一群體,以此作為創新點激發了廣大觀眾的興趣。
一、場景中表意元素塑造教師形象
(一)樸素的教師形象
影片開篇運用一組慢鏡頭拍攝了老師的辦公桌,以畢業留影、鋼筆、教案本、茶水杯、作業冊等一系列富有場所精神的物品,將觀眾帶入了校園場景,沒有浮夸的表演和道具,平緩地將發生年代及背景進行了交代。苗宛秋老師隨后推著自行車步入校門,背景的文化墻上書寫著20世紀80年代的主流價值觀,并非其他校園篇中大面積使用毛澤東主席的畫像來奠定時代基礎,這樣一個別出心裁的設計從側面體現了苗宛秋所任職的南宿一中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不動搖以及求真務實的校風。隨后鏡頭對苗老師的自行車做了一個特寫,重點突出了這輛自行車是市優秀教師的獎品,于是這輛蘊含獎勵意義的代步工具在此轉化成了象征著榮譽的符號,并在接下來的劇情中反復出現,起到了貫穿影片的作用。與之意義相同的是苗老師的水杯,上面寫著一個大大的“獎”字,這些都在輔助塑造苗老師是一名十分注重個人榮譽卻又不是貪慕虛榮的樸素教師。
(二)“苗霸天”的多元色彩
苗老師的戰場在課堂上,與傳統意義上三尺講臺上揮灑汗水的教師形象不同的是,苗老師在出場的第一時間并未表現出其過硬的專業素質,而是游走于講臺之下。此時的場景一改昔日老師諄諄教誨,學生聲情并茂朗讀的范式,而是放置了口紅、香煙、雜書、斧頭等物品,這些物品的潛臺詞與嚴肅、正經的課堂形成沖突。面對油腔滑調的王海、囂張跋扈的洛小乙,苗老師的態度是堅決不讓步,處理態度堅定且執著,其為人師表、立德樹人的教師形象與這些三教九流的表意元素形成鮮明對比,鞏固了其果敢、有魄力的教師形象。教室后面的黑板報上宣揚著夢想的力量,“讓我們揚帆起航”寓意著每一個學生都有實現夢想的可能,然而溫馨而又純真的教室場景以苗老師的呵斥而結束,目前這個班級里既沒有凝聚力也沒有良好的規矩,場景設計與現實的沖突不斷提醒著各位觀眾,苗老師任重而道遠。走出校園后,苗老師騎著他的自行車穿梭在街坊里,車后座放著他買的菜。與普通人一樣他融入了市井,在菜攤挑選著蔬菜。夕陽灑落在他佝僂但不卑微的背影上,這一幕場景設計充滿生活氣息,用蔬菜與挑選蔬菜的動作來突出苗老師身為一名教師的平凡,而正是因為平凡而不平庸的生活態度,塑造了苗宛秋深入人心的教師形象。
(三)豐富的人生形象
然而苗老師并非如圣賢一般出現在銀幕里,當洛小乙出現在他家院子里遞交入團申請書時,苗宛秋展現了膽怯的一面,他拿起掃帚胡亂揮舞的樣子淋漓盡致展現了一個普通人面對危險時的懦弱。同樣苗老師也是一個血氣方剛的人,他為了挽救洛小乙去到地痞流氓的酒桌上要人,他深知一名教師肩上的責任和義務。“九龍一鳳”和桌上的酒瓶子與形單影只的他形成視覺上以及邏輯上的沖突,場所精神在此發揮作用,在不是苗宛秋的戰場上他表現出強烈的立德立威精神,成功地喚回了迷途少年洛小乙。綜上所述,場景對于苗宛秋教師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單一的概念和品質構成的扁平形象,而是糅雜了不止一種的品質的凸圓人物。正如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評論家戴錦華評論道:“這部電影顯得有某種老舊,有某種拙,但當我把他看完時,不止一次我的心被撞擊,刻意掩藏起的柔軟之處被打動。我非常喜歡電影中的那個老師,他不可愛、不完美、不優秀、但正是像他這樣的人托舉起中國社會,托舉起一代又一代的人。”
二、場景設計推動劇情發展
(一)場景激化矛盾
貫穿劇情始末的自行車很好地起到了制造矛盾與激化沖突的作用,在實際作用層面,自行車作為那個年代的主要代步工具是十分奢侈的存在。內涵層面,自行車作為苗老師的榮譽感象征,是其自我價值的體現。當學生第一次向苗老師“宣戰”時,自行車就承擔起了犧牲品的責任。在這一次矛盾產生時,學生卸下了苗老師自行車的擋泥板,自行車基本還能正常運行。苗老師和往常一樣下班騎車回家,鄰里賣菜的也依舊和他寒暄兩句,并沒有什么特別。然而鏡頭一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苗老師自行車后輪因沒有擋泥板的緣故,泥巴全都濺在了衣服上。整潔的白色襯衫上泥巴顯得格外刺眼。
這一場景的設計十分獨到,如往常一樣的歲月靜好畫面突然畫風一轉,略帶喜劇無傷大雅的“侵略”使得學生在這場戰役中拔得頭籌,也讓觀眾越發期待接下來的劇情發展。苗老師對于這件事的處理十分巧妙,這一場景發生在體育場上,并不是觀眾們印象中的課堂里,處理方式也不同于傳統的挨個問話,而是進一步地激化矛盾。苗老師有意識地將刺頭洛小乙抓出來頂包,在二人的呵斥中再次體現了苗老師強硬的一面,眼看事態無法控制時,前后共有三個學生站出來緩解事態,然而前兩個都失敗了,只有學習成績優秀的安靜同學站出來為洛小乙做不在場證明成功,苗老師借此機會就坡下驢,表示愿意相信每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與之前完全不信任洛小乙任何爭辯形成對比。隨后苗老師出人意料地重打輕罰放過了這群不安分的學生。看似這一局是學生取得了勝利,苗宛秋并未抓到真正的操刀人,但苗老師的意圖并不是為一個代步工具報仇,而是借此機會先是有意識地培養班級凝聚力,再是傳遞出老師信任品學兼優的孩子的信息,鼓勵學生向此努力。無形中煽動了學生團體中互幫互愛、努力學習的氣氛。
(二)場景促進師生感情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操場上,寓意著并非只有課堂才是苗老師的戰場。學生對苗老師態度的轉變取決于一件件小事,不僅在課堂上苗老師是傳道授業的老師,生活中他也承擔起了一個人民教師光輝的責任。最終苗老師的自行車是被盜了,學生們在距離高考還有51天的時候每天晚上幫他尋找他的自行車,怎奈他們的好意卻換來苗老師劈頭蓋臉的訓斥。學生與苗宛秋的身份不同,他們思考問題的角度也截然不同,實則在苗宛秋的大義與榮譽面前,學生能有一個好的歸宿勝過他一切的獎勵與獎品,也正是這一次發生在操場上的又一次沖突,苗宛秋的內心開始變得脆弱和柔軟。
隨后的劇情逐漸由校園向校外過渡,校園的生活也并非一帆風順。苗老師從派出所把因賣貨引發打架斗毆的劉昊帶出來后,來到了一家路邊攤。由此得知總是做點小生意的劉昊得了腦瘤,他賺錢也是為了救自己的命。這樣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從劉昊口中說出是那么弱小和無助。路邊攤的場景由一張桌兩張椅,一碗熱騰騰的面構成,散發著平凡卻又溫暖的氣息,簡單樸實的路邊攤卻承載著相當分量的情感寄托。此刻夜幕也已經降臨,進一步渲染出苗老師對學生校外生活的關心以及那個年代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可能。隨后苗宛秋在班級里組織募捐,加深同學之間的團結力和凝聚力,為以后劇情所發生的故事進行了鋪墊。
三、場景設計烘托主題
苗宛秋光輝的教師形象塑造離不開其演員對演技的把控,其師德師風的建設同樣離不開劇情與場景的塑造。當苗宛秋的老婆三番五次抱怨生活清貧,既沒有房子分又沒有外快賺的時候,苗老師一句“自古圣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道出了其內心的氣度,鏡頭中苗老師的家中雖然狹小,但書柜占據了很大的空間,畢業照、榮譽證書擺在第一排,一家三口吃飯的桌子也是在這一個區域,并沒有富裕的就餐空間。一方面描寫了苗宛秋清貧拮據的生活,一方面也為他清高的氣節做出了交代。然而苗宛秋始終是一個平凡的人,他也十分渴望分到房子,渴望能夠多賺些收入改善生活。他透過窗戶縫窺視隔壁辦小班賺錢的老張,雖然只是一瞥,老張家中的環境便可得以推論,明顯老張的生活條件是優于苗宛秋的。然而在苗老師內心的取舍中,他最終選擇了不收取任何回報幫助學生進行補課。這一場景十分溫情,因家中面積拮據,無法容納過多學生,所以苗老師把授課的位置擺在了家門口,來聽課的學生甚至排到了街坊里。這無疑是對那些收費授課教師的一種打壓,敢于打破常規、弘揚崇高師德的苗宛秋卻因此被人舉報,印證了那句古話:“好人不長命,壞人活千年。”這一場景的描寫直擊影片主題——老師,大家都知道好,好在哪里?好在其真性情的抉擇中,毅然而然地站在了維護學生利益的一方。一聲“老師好!”就能全然讓人民教師忘卻一切紛繁雜亂,一切以學生至上。
影片末苗宛秋獨自一人坐在空蕩蕩的教室里,此刻他坐在了一個學生的位置上,回想起他的青春歲月,思考著到一直以來自己所秉承的,他的老師所教導的“士不可不弘毅”究竟是怎樣一種取舍。此時的場景設計銜接恰當,當苗宛秋不再是站在講臺的老師,當學生都已離去,空教室與苗宛秋的身份發生呼應,恰如其分地宣泄出苗宛秋內心深處對于高等學府的向往,對于自身責任任重而道遠的解讀,讓觀眾切身體會到苗宛秋的不幸與遺憾,再一次將觀眾感情推至高潮。
四、結 語
青春總是洋溢著活力卻又充滿著遺憾,正如影片末尾安靜的車禍和苗老師的不辭而別,似乎就像一首優美的詩歌被截去下闋。類似于這種老師最終離開學生的影片還有《死亡詩社》和《放牛班的春天》,比起這兩部中因制度問題引發的矛盾,《老師·好》中苗宛秋的離別更加具有溫度,導演善于運用場景中的物件進行感情宣泄,運用鏡頭對不同場景切換達到氣氛的渲染,影片最終也不是以一個圓滿的句號落幕,而是以書店、咖啡、蝴蝶等寓意歲月靜好的一組鏡頭銜接,誠如每個人的青春歲月,在遺憾中取舍,在取舍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