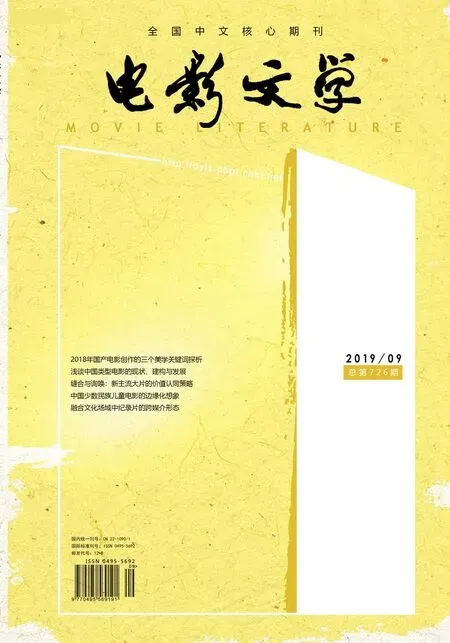美國軍旅題材電影及其反戰(zhàn)意識解析
王玉蘭 (山東青年政治學院 外國語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3)
美國作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軍事強國,其自立國以來就不斷陷入戰(zhàn)爭的歷史,其對軍事建設一以貫之的重視,以及人們對國家、個體從戰(zhàn)爭中獲取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付出了慘痛代價的感受,這多種因素推動著美國的軍旅影像書寫走過了近百年的發(fā)展歷程。在當下,軍旅題材電影已經成為美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重要方向之一。而面向全球的美國電影,又注定了它是一種承載普世價值的語言,人們對戰(zhàn)爭的深惡痛絕,是美國軍旅題材電影的主要意識形態(tài)。在其他部分國家的同類電影依然停留在對戰(zhàn)爭進行淺層表現甚至是欣賞的階段時,美國電影人就已經開始了對戰(zhàn)爭的反思表達。
一、反戰(zhàn)維度確立的必要
電影的維度即電影的創(chuàng)作視角,它直接關系著電影的主題、內容選擇和思想導向。而與民族形象、國家歷史和政策緊密相關的軍旅題材電影,往往被認為是與價值觀引導緊密相關的“主旋律”電影,美國亦不例外。如前所述,美國的軍旅題材電影盡管也存在部分以戰(zhàn)爭或軍隊生活為外殼,而填充的是搞笑、青春愛情等內容的浮濫之作,但是在大體上,其選擇的依然是反戰(zhàn)維度,以直擊戰(zhàn)爭的丑陋和罪惡,引發(fā)觀眾對正義與非正義、暴力與和平等問題的思考。
戰(zhàn)爭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意味著家園的毀滅,生命的喪失以及人類文明的破壞,這些珍貴之物在戰(zhàn)爭面前無比脆弱,這也是為何戰(zhàn)爭往往被稱為“絞肉機”的原因之一。尤其是電影得到長足發(fā)展的20世紀,更是被稱為“以戰(zhàn)爭始,以戰(zhàn)爭終”,人類經歷了空前慘烈戰(zhàn)爭的一個世紀。在這樣的情況下,電影有必要符合絕大多數人的立場,對戰(zhàn)爭進行否定,對發(fā)起戰(zhàn)爭浩劫者給予批判,而對受到戰(zhàn)爭迫害者給予同情。一旦電影違背了這一立場,那么無疑也就觸碰了絕大多數觀眾的利益。
當然,有少數人能從戰(zhàn)爭中獲益,或誤以為戰(zhàn)爭具有進步性,或低估戰(zhàn)爭的惡劣,電影則要對其進行藝術性地批駁。例如在根據德國作家雷馬克同名小說改編而成,被譽為“電影史上最偉大反戰(zhàn)電影”的《西線無戰(zhàn)事》(1930)中,以保羅·鮑曼為代表的德國青年在德國政府的宣傳之下,將戰(zhàn)爭等同于愛國和英雄理想,而最終面對的卻是不堪入目的場景,最終,保羅在戰(zhàn)壕中伸手抓一只蝴蝶時中彈身亡,沒能實現自己回家的愿望。美麗的、翩翩飛舞的蝴蝶在此就象征了美好可貴的和平。又如在《辛德勒的名單》(1993)中,奧斯卡·辛德勒原本更是認為自己之所以沒有能發(fā)橫財,欠缺的正是一場戰(zhàn)爭。他將戰(zhàn)爭視為自己攫取財富的機遇,然而在目睹納粹在克拉科夫毫無人性的大屠殺,以及與猶太人伊扎克·斯坦等人接觸后,辛德勒徹底改變了自己發(fā)戰(zhàn)爭財的念頭,不僅開始了對猶太人不惜血本的營救,最后甚至冒著生命危險讓自己的工廠長達數個月生產不合格的軍火,他成為一位猶太人的“救世主”,實現了人性的復歸。與之類似的還有如反映諾曼底登陸的《最長的一天》(1962),用一句美國諺語“在理智與瘋狂之間,只有一道細細的紅線”點明戰(zhàn)爭危害的《細細的紅線》(1998)等。這一類電影,都跨越了國界,得到了觀眾的高度肯定,而那些美化戰(zhàn)爭、鼓吹戰(zhàn)爭的軍國主義之作,則早已成為被人們遺忘的“速朽”之作。
二、美國軍旅電影的反戰(zhàn)意識表現
反戰(zhàn)意識必須要建立在具體的劇情之上,美國軍旅題材電影往往從以下幾個角度出發(fā),將戰(zhàn)爭給人帶來的痛苦拉近到絕大多數并未有過戰(zhàn)爭或軍旅生活經歷的觀眾面前。
(一)對戰(zhàn)爭殘酷的渲染
首先是以各種方式,包括強有力的戲劇沖突,或動人心魄的視聽體驗,渲染戰(zhàn)爭的殘酷,從而讓電影成為控訴戰(zhàn)爭的有力工具。在這類電影中,面對戰(zhàn)爭機器,人在肉體和精神上被摧殘,被剝奪自由和生命,失去尊嚴和權利,都被表現得十分露骨。
例如在以海軍為主要表現對象的《珍珠港》(2001)中,電影以接近四十分鐘的時長,來表現日軍偷襲珍珠港時的無情轟炸,給予觀眾強烈的視覺沖擊。在軍艦上服役的軍人在遭遇偷襲時很難組織有效反擊,亞利桑那號被日軍擊沉,困在艙內的戰(zhàn)士只能望著水逐漸淹沒自己而毫無辦法,在敲擊求救后最終還是窒息而死;在甲板上的人則遭到機槍的無情掃射,在岸上基地休整的人多為爆炸、燒傷等所困,女主人公伊芙琳身為護士,看到寧靜祥和的夏威夷淪為人間地獄。在表現陸軍的《血戰(zhàn)鋼鋸嶺》(2016)則表現了沖繩島戰(zhàn)役的冷血殺戮,戴斯蒙德作為軍醫(yī),目睹了無數人在看不清敵人面孔的情況下應聲倒地,或肢體斷離,或肚破腸流,他在滿是尸體的戰(zhàn)場上匍匐翻爬,分辨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身軀是否還有療救的可能,在漫漫黑夜之中,戴斯蒙德和戰(zhàn)友失散,加之身上沒有任何武器,陷入了一種近乎絕望的困境。在這些電影中,一條條年輕、鮮活的生命就在席卷而來的戰(zhàn)爭面前流逝,人所能做的反應通常是無力的。
(二)對人性閃光的高揚
戰(zhàn)爭是與人性相對立的,戰(zhàn)爭能使人瘋狂,對其他人的屠戮能改變人的心志,使活著的人成為行尸走肉,或是無視生命的魔鬼。也正因如此,在戰(zhàn)爭這一黑暗時期一點人性的閃光就尤為可貴。肯定人性,張揚人的真、善、美,就是對戰(zhàn)爭的一種間接否定。
例如在《美國狙擊手》(2014)中,牛仔出身的克里斯·凱爾參軍后成為伊拉克戰(zhàn)場上的優(yōu)秀狙擊手,在硝煙彌漫的戰(zhàn)斗中,憑借神奇的槍法為美國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成為當地武裝分子聞風喪膽的“拉馬迪惡魔”。戰(zhàn)爭沒有消磨他的人性,當他的瞄準鏡中多次出現拿著炸藥充當人彈的婦女與兒童時,身為丈夫和父親的凱爾產生了對戰(zhàn)爭的強烈厭惡,他決定退役回歸溫馨的家庭生活。而在退役后,為了拯救那些罹患了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戰(zhàn)友,凱爾忙于設立基金會,探望老兵,但也就是在一次陪伴老兵前往射擊場時,凱爾被對方槍殺。凱爾從槍林彈雨中全身而退,但終究沒能躲過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這一“隱形殺手”。擁有美好人性凱爾之死,正體現出戰(zhàn)爭的陰魂不散。又如《戰(zhàn)馬》(2011),電影“刻意淡化了直面戰(zhàn)爭的深沉悲痛,以溫暖的細節(jié)給予人們絕望中的希望,張揚了人類的普世價值”。導演斯皮爾伯格在電影中既表現了人類與動物的和諧關系,實際上也表達了對人與人和諧共處的期待,促使著觀眾思考人性的本真與善良。如在電影中,戰(zhàn)馬不顧一切地奔向自己的主人,以至于被鐵絲網纏住動彈不得時,原本敵對的兩邊戰(zhàn)士們或扔出工具,或走出戰(zhàn)壕,齊心協(xié)力地拯救戰(zhàn)馬,這無疑是令人動容的。
(三)對軍隊黑暗的刻畫
最后,美國軍旅題材電影中,也不乏對美軍陰暗面進行反省的一面。作為戰(zhàn)爭的一端,作為干涉國際事務的武裝力量,美軍并非永遠立于正義、光榮的一面,尤其是在美國發(fā)動錯誤戰(zhàn)爭,給美國社會留下深重的“后遺癥”的時候,美國軍旅電影往往就會暴露軍隊中有違常理、虛偽的一面,軍隊成為戰(zhàn)爭荒謬性的集中點。例如在《現代啟示錄》(1979)中,美軍的敵人竟然就是美軍自己,威拉德接受的任務是去刺殺一名曾經是越戰(zhàn)英雄的前美軍上校,也就是在尋找這位上校的過程中,威拉德目睹了美軍士兵在長期作戰(zhàn)中的種種暴行,美軍們對當地人玩的是“先用機槍掃個半死再用紗布包扎”的把戲,這讓威拉德感到惡心不已,他也理解了自己刺殺對象為何要“背叛”國家。與之類似的還有如《生于七月四日》(1989),生在國慶節(jié)的羅恩懷著愛國熱情踏上越南戰(zhàn)場,結果卻看到美軍屠戮手無寸鐵的婦孺,他自己也在受傷癱瘓后陷入到頹廢、低落的情緒中,對于女友唐娜的反戰(zhàn)游行,羅恩的態(tài)度從抵制到支持。軍隊的黑暗面不止表現在對敵國百姓的欺凌,也表現在內部的霸凌、作風腐化上,例如在《全金屬外殼》(1987)中,為了把新兵們培養(yǎng)成戰(zhàn)爭機器,軍官們給予士兵們各種各樣的折磨,以至于他們精神崩潰,迅速被異化;在《野戰(zhàn)排》(1986)中,伊萊亞斯等人用吸毒來麻痹自己,巴恩斯更是公報私仇,害死伊萊亞斯,最終泰勒又殺死巴恩斯為伊萊亞斯報仇,美軍的自相殘殺觸目驚心。
三、“美式”反戰(zhàn)意識缺陷
應該說,美國軍旅題材電影在藝術與思想上已經達到了相當高度,其對戰(zhàn)爭的反思是較為全面和深刻的,但它們也是被打上了鮮明的美國烙印的電影,其反戰(zhàn)意識也是“美式”的,代表了美國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加之其大多數必須走商業(yè)片的道路,必須考慮票房收益,因此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是對歷史的虛構。美國軍旅電影的反戰(zhàn)意識,有時是依托于真實事件的“演義”式敘事的,這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電影的教化力量。如在《拯救大兵瑞恩》(1998)中,原型中的士兵很快被找到并被送回美國,而在電影中,主創(chuàng)設計了一段相當坎坷的尋找和拯救瑞恩的過程,以讓電影的情節(jié)顯得更為跌宕起伏,充滿戲劇性。如果說這種藝術處理可以算作是必要的,那么在部分電影中,美國人則有著將自己包裹為正義之師,或丑化敵方之嫌,例如在《天與地》(1993)中,越共士兵強暴了原本就支持越共游擊隊的越南姑娘黎里,在《獵鹿人》(1978)中三個主人公被越共俘獲以后,更是被逼迫玩“俄羅斯輪盤”的殺人游戲,越南人以此來打賭取樂,狀若癲狂,讓主人公們在扳機扣響的聲音中驚恐不已。敵人在這些電影中被塑造得猶如禽獸。與之類似的還有如《黑鷹墜落》(2001)等,在此不贅。
其次,在美國電影人意識到不應將敵方塑造得過于猥瑣愚蠢或毫無人性時,往往又會暴露出立場模糊的弊病。當“戰(zhàn)爭”成為人類的共同敵人時,電影往往就會忽略戰(zhàn)爭中的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或是自我矮化,或是對敵人有著引發(fā)爭議的同情和贊美。這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于《父輩的旗幟》(2006)與《硫黃島家書》(2006),前者講述了幾個“人造”英雄的故事,四個所謂的插旗英雄僅僅是因為新聞的需要完成了擺拍,就得到了令他們不安的名利,電影暗示了歷史的真相并不是唯一的,美國的榮耀與驕傲亦是可以被質疑的;而后者則將日軍塑造為熱愛生活、有情有義的普通人,意在表現是戰(zhàn)爭將原本可愛的小人物變?yōu)槟Ч恚@固然是伊斯特伍德的用心良苦之處,但是對于長期受到日本法西斯壓迫凌辱,飽含悲憤情緒的中國觀眾而言卻難免難以接受,這是中國電影人要謹慎借鑒的。
正如美國導演西米諾曾經指出的那樣:好的戰(zhàn)爭題材電影必是反戰(zhàn)的。這一觀點擴大到軍旅題材電影亦然。美國軍旅題材電影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固定的戰(zhàn)爭倫理觀,在文化價值上,其基本上都站在反戰(zhàn)的立場上,進行了否定戰(zhàn)爭、呼吁和平的表達,在內涵以及藝術手法上,有著不可否認的可資借鑒之處。但我們也要意識到的是,美國軍旅題材電影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美國神話”的代言者,其反戰(zhàn)話語是服務于這一神話的塑造的,美國軍旅電影的反戰(zhàn)意識表述是存在缺陷的,我們在肯定和學習美國軍旅電影的創(chuàng)作時,亦有必要對此進行辨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