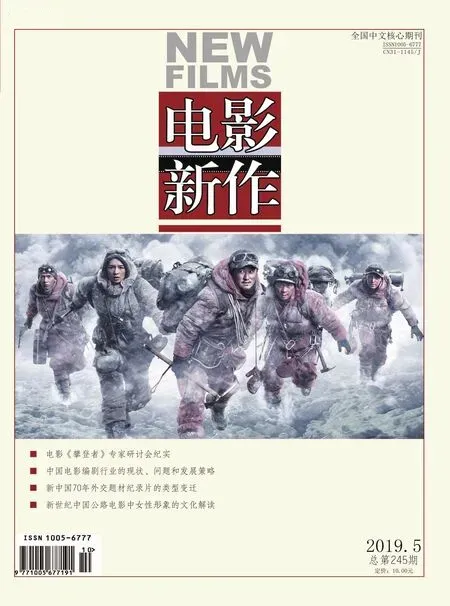《開天辟地》創作談
汪天云
時光荏苒,滄桑巨變。我參與影片《開天辟地》的創作到現在整整30年了。那年夏天,我大學畢業,留在上海師范大學當老師,受邀去嘉興,給浙江創作評論協會舉辦的講習班做演講。講完課后,一群人赴船宴,在船上聊天時,大家就談起,世界上有很多的政黨,但沒有一個政黨是在船上誕生的。當時程衛東、黃亞洲,還有其他十幾個人都說建黨這件事寫個電影,你覺得怎么樣?我覺得行,我就提出可以寫一個國民黨追捕共產黨建黨名單的驚險片。結果沒多久,那天的創作熱情就被落實下來了。黃亞洲到上海來找我,我們兩人在上海開始策劃,寫出了一個詳細的提綱,相當于是一個初稿,然后拿著這個初稿去找上海電影制片廠文學部。文學部的主任是楊時文和孟森輝,他們還沒看,首先是讓編輯祝洪生看。祝洪生當時說:“這兩個年輕人倒是蠻有意思的,要寫共產黨誕生這個從來沒有人敢寫的題材。”劇本就留下了。最初,電影的名字叫《開天辟地大事變》,于本正說,“大事變”就不要了,就叫《開天辟地》,氣派大。這個片子的誕生,真要感謝他,還有吳貽弓。
黨史浩如煙海,人物眾多,我們當時寫了78個有名有姓的人。上影文學部領導們跟我們商量,到底是以史攜人還是以人托史。討論來討論去,寫過來寫過去,我跟黃亞洲兩個人就在這個文學部的小樓里一稿一稿地改,改得昏天黑地、胃吐酸水。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還是要以人來托史。因為寫這個過程,可以寫很多情節,但是關鍵還是刻畫人。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三位黨的創始人怎么把握主次詳略。當時從北大的角度來講,陳獨秀是教授,李大釗是圖書館館長,毛澤東是書記員。也有人說,把李大釗放第一位,因為李大釗是烈士,毛澤東是領袖,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
最后是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陳至立同志,她拍的板。她用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她說:“我們還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寫,這樣經得起歷史的考驗。”那么按照這個觀點,歷史唯物主義、實事求是和辯證唯物主義來統領全片寫作就是結合以后的歷史的狀態,這三個人是有堅定信念的。所以我們就把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的關系最后定位,主要的筆墨集中在陳獨秀,然后是李大釗,之后是毛澤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個旁白就成為這個戲的主心骨。
當然還有其他人,因為這里面有13位黨的代表,我們是用例推的辦法來寫他們早年的性格行為的。這個經驗后來也用到了《鄧小平1928》,小平同志能力挽狂瀾堅持改革開放,來源于他早年的革命理想,也可謂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這個創作實踐也是改革開放以后才被共識的方法論。它既是尊重事實,又是要寫出歷史人物在以后的世紀風云當中的表現傾向。
我們遇到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小細節和大情節的相互關系。大事件是不可以隨便去改變的,比如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等時代風云,包括從上海的石庫門轉移到嘉興南湖的船上。但是小細節我們是可以創造的,最典型的就是陳獨秀和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因為這兩個孩子后來實際上都是我們黨的重要領導和烈士。但是陳獨秀對他們很嚴酷,晚上讓他們勤工儉學拉大鋸,但是他又很愛自己的孩子。最后我們就創造了陳獨秀捧一鍋茶葉蛋去看孩子,這個情節其實來源于我們自己的生活,那時候我們在學校里補習英語,晚上放學餓了,就買一點茶葉蛋吃。
還有所謂“大手筆”就是陳獨秀作為一個大學教授,穿著白西裝就跑到上海大世界去撒傳單,然后被人家抓住,但他很有個性,人家打了他一記耳光,他打還對方一記耳光,以牙還牙。他也很欣賞毛澤東,認為毛澤東在湖南宣傳革命的過程中創辦的那些傳單、海報、宣傳品,認為他是個大手筆。這些實際上都是史料上找不到的,但是在電影當中它是有畫面感的,是有感染力的,是有激情的。還有就是第一次讓毛澤東下跪,就當時這一點,我跟黃亞洲商量了很長時間,當時很多人勸我不要這樣寫。起因是毛澤東去找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當時楊昌濟是倫理學的教授,他對毛澤東是有一定保留的,但是他又很糾結女兒的感情,毛澤東是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人,所以毛澤東最后在求婚的那一夜是跪下了,希望楊昌濟同意把女兒嫁給他。這里面寫出了他們兩人的情感,毛澤東的那種內心的執著和人生的浪漫。
我們寫《開天辟地》那年,市委宣傳部搭了四套班子來做這個選題。祝洪生給了我們很多幫助,不斷地把其他的情況也告訴我們,讓我們能夠做成。當時導演其實已經選定是李歇浦,但李歇浦自己也拿不準到底是用哪個本子更好。要感謝的是張駿祥先生,他是李歇浦的老師,他對李歇浦說:“這幾個本子我都知道,你們不用他們大學里出來的用哪個?他們比較嚴謹地按照黨史一件件一樁樁來編寫。完全按照浪漫主義隨心所欲去寫建黨恐怕不行。”李歇浦也就此拿定了主意。
我覺得這個本子的誕生真不是我們兩個人能夠寫的,是有很多的前輩、領導、藝術家給了我們幫助,給了我們指點,給了我們力量。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李歇浦是非常有創意的導演,在挑選演員的問題上也很嚴格,這部電影里面大概有50多個演員,都是對照真實的歷史照片去找的。那年冬天,我們在松江中外電影研討會上看片子,是內部片。制片主任柴益新跑來說,“唉,你們太舒服了,兩個人天馬行空地寫,我們拍得累死累活,你們也來體會體會。”就把我找去了,讓我演其中一個角色。他說邵力子這個人物跟你很像,也是大學教授。隨后他拿著邵力子的照片,叫了沈東生和殷麗華來給我化妝。邵力子的腦門很大,然后就按照他的照片把我的頭發拔掉,眉毛拔掉,拔得像了,他才點頭。拔了兩天,我第三天就受不了了,幸虧只有兩句臺詞,也就過去了。正是這次表演,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電影表演藝術家。特別是邵宏來,邵宏來是青島話劇團的演員,他演陳獨秀,他對這個人物的研究非常全面,所有陳獨秀的文稿、書信、照片,所有的史料細節他都掌握得很清楚。還有孫繼堂,他的內在個性跟李大釗很像,比較內斂,演得非常棒。
當時為了找能夠演年輕時代毛澤東的演員,幾乎找遍了全國。因為1921年的毛澤東很年輕,古月想演,但年齡確實大了。后來攝制組就根據我們寫的毛澤東,找了杭州紅旗越劇團的一個演員叫王霙。這個人現在已經是演毛澤東的專業戶了,因為他和青年毛澤東的形象、氣質很接近,就是人矮了一點。后來黨史辦的人說毛澤東是在長征路上長高的。還有一個難題,根據劇本找來找去,找不到能演鄧小平的演員。最后是在某一個大學的食堂里看到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過來一問,是廣西的。與此同時,也找到了一批能演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共產黨優秀骨干的年輕人。佟瑞欣就在那會兒被選上了。
所以這個戲的所有的人物造型,其實功勞是屬于導演部門。因為在寫劇本的時候我們能看到的史料有限,但是我們總覺得那個年代的人,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氣質,那種勇敢、堅定、智慧、激情是很可貴的。
當時我覺得這部片子的誕生是非常了不起的,得益于當時國家電影局的領導、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領導給我們的指示,也感謝老一輩的藝術家,像張駿祥先生,以及當時上影廠的領導,吳貽弓、于本正,還有李歇浦、沈妙榮、楊乃如、朱永德、柴益新、胡立德。現在回過頭看看,很多人都已經不在了,他們為我們的主旋律,他們為我們建黨的電影,為我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和這些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真是默默地做出了很多貢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所以后來《開天辟地》就成為這一類主旋律電影的一個標桿,或者說是一個樣式,這種樣式就被很多電影所吸取。然后我們就有了一種信心,一種信念,或者說有了一種經驗,就說敢于這樣去寫,領袖人物也是真實的人,源于生活可以高于生活,領袖人物可以用他們當年的風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準去寫。所以現在,我們描寫這一類題材的作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好,越來越感人。
就當時來說,去寫建黨題材是很難的,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年輕;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得到了老一輩的支持;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這部電影誕生的時候,正好走上了改革開放的坦途;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上影廠許多藝術家的支持。他們的那種態度是上影廠的傳承,上影廠70年留下的,不僅是一批作品,還有上影廠的工作作風和敬業精神。這部電影我記得當時只花了900多萬,拍得是極其的認真,及其的負責。所有的道具、服飾、化妝,所有的煙火、燈光,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上影廠的精華。包括作曲、旁白各方面。所以這部電影后來在各地方放映的時候都受到了高度的贊譽,而且每年7月1日這部電影都會在電視里重播。我覺得做這樣一部電影其實對我來說是鍛煉,是教育,也是提升,要感謝上影廠,這個已經有70年歷史的藝術單位。這個單位給了我們智慧、力量、勇氣和收獲。在我們以后的日子里,也做了很多類似的作品。到上影廠來工作以后,我還和李歇浦一起創作了《鄧小平1928》、傅東育導演拍了《西藏天空》,當然還有現在的《攀登者》,所以這種精神一直沒有斷,這種精神一直在延續,不管我們現在電影更市場化了,或者說更強調它的三性統一了,這個創作過程當中的這種嚴肅認真,還是有這樣的一種精神的繼承和延續。只有這樣,我們的電影才能夠真正對得起我們的歷史,對得起我們的觀眾,也能對得起我們的后人和未來。
創作《開天辟地》是我一生中不可忘卻的藝術歷程,也是上影廠70年歷程中永遠鼓舞我們奮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