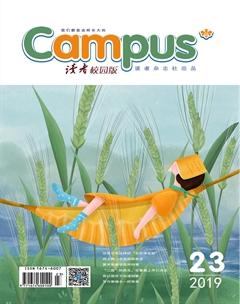黑色曼陀羅
劉昊然


黑色曼陀羅
在拍《唐人街探案》之前,我在《黑色曼陀羅》劇組有過一次對我來說很重要的試戲經歷。在和這部電影的角色一步步接近的那段時間里,我被逼著不斷去直面自己最絕望的情緒,去體驗人類最無望的深淵。雖然因為檔期原因我最終沒有參演這部電影,但那段學習和不斷被刺激的時光,真的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我試戲的角色是一個具有雙重人格的青年,他的一重人格像天使,而另一重人格是殺害自己母親的兇手。
這個角色稍微有點兒像《一級恐懼》里愛德華·諾頓飾演的具有雙重人格的亞倫。亞倫在平時是一個很弱小、無公害、講話結巴、沒有自信的人;而在受到欺壓又不敢正面反抗時,他的身體里就會出現一個叫作羅伊的人,羅伊性格暴躁、語言粗鄙、行為殘暴。
《黑色曼陀羅》想要進行的是一種對人性和人格的探討。這個故事說的是,一個很需要安全感,卻永遠處在不被保護狀態下的人,是沒有辦法表達真實的自己的。
每個人天生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一個小孩子他能夠表達出善良、純真、有愛心這類“善”的部分,也可以表達出自私、霸道、極端等不那么“善”的部分。而這些表達,本身就說明這個孩子是處在一個有愛的環境里,是處在一個有安全感的環境中。
當這些“善”的行為出現之后,家人會鼓勵他;當不那么“善”的行為出現之后,家人也會告知他規矩。這些鼓勵和規矩,都是一個人性格形成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性格中的好和壞,都能夠被有效地引導和轉化。
但是有些人,他們是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下長大的,可能從來不敢把自己壞的一面暴露出來,只能拼命地往下壓;壓著壓著,有一天那些隱藏的惡的部分就會成為第二人格表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故事里,我覺得它展現出來的雙重人格的最大特點,就是當這個人物處在不安全環境中時,他沒有辦法把比較壞的一面表現出來,只能一直藏在自己的心里,并且沒有人告訴他這樣是不對的。
第一次試戲試到崩潰
《黑色曼陀羅》的導演之前是一名話劇導演,我去劇組時,劇組成員都在。導演很直接,他說:“我知道你表達天使的這一面是沒有問題的,純真、美好、善良,這一塊兒大家對你都沒有懷疑。但在這個角色身上,最重要也最出彩的地方,是他性格反轉的那個部分,那個惡的或者說陰暗的部分。希望你能將這些東西表達出來。”
剛開始嘗試時,我表現得很生硬,我的想法是讓自己安靜下來,能夠表現出那種沉默中的陰郁。導演看了并不滿意,他開始激我。他希望看到的不是冷靜,而是瘋狂。他想激出我身體里理性背后的那種不受控制的憤怒。
每個人的憤怒是不同的,有的憤怒是來去都十分迅猛的平常的憤怒,而我理解的電影里的憤怒是一種高智商的、條理清晰的、深層次的憤怒。所以一開始導演用言語刺激我、用身體給我威懾的時候,我腦子里還在想著要怎么演,畢竟我的余光能看到攝影機在拍。可是跟隨著導演的引導,我開始慢慢放任自己陷進主角的那種被傷害、被否定、對世界無盡的失望與對人性的嘲諷之中了。
現在,我都有點兒回憶不起來我是什么時候進入狀態的,這種狀態也不是我能夠控制和復制的。那應該是我第一次體驗到忘記自我的失控,那是一種有點兒“上頭”的狀態。后來導演喊“卡”時,我整個人都有點兒崩潰了。我發現自己在瘋狂地咒罵,身子因發抖而扭曲,眼淚和鼻涕不受控制,腦子也混混沌沌的,好像從身體到心靈,都被一場風暴襲擊過。
我想起自己。我并不是一個完全無公害的人,小時候脾氣還是挺暴躁的。可能是因為從小就獨自外出求學,身邊都是老師、同學,大家沒有忍讓我的義務,在那種沒有安全感的環境里生活,我就用很厚的殼把自己包起來了。我自己也沒有太多的安全感去排除這些極端化的感受。
小黑屋剝離實驗
確定了角色,進了劇組。還沒有開拍時,導演安排了一個表演老師對我進行訓練,希望幫我進一步去體會這個角色性格里那些沉重的情緒。我當時住在劇組安排的酒店,每天起床之后就去找老師訓練和上課。
這個角色從小被親生父母拋棄,在養父家長大,又被養父忽視和虐待。他有些自閉,又因為小時候哭鬧,被關在狹小的黑屋子里,而有明顯的幽閉恐懼癥傾向。
為了體驗這種“被空間限制、剝奪時間的失控”,老師讓我進了一次小黑屋。
當時在我們住的酒店房間里,有一間屋子的衛生間沒有窗戶。這個密閉空間在房間內側,很小,大概只有5平方米,里面有一個排風扇。老師讓我把手表、手機等跟光和時間有關的東西都放在屋外,然后一個人走進衛生間。關掉燈,關掉排風扇,讓整個衛生間完全處于一個密閉的黑暗狀態,門是虛掩著的。我在里面待著,除了不能睡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直到自己覺得待不住、想出來為止。
進去之后,我剛開始還在琢磨著要想點兒什么才行,一定要堅持下去,要在里面待久一點兒。于是腦袋里就想各種各樣的事情,把能想的都想了一遍,思緒是沒有指向性的,東想一下,西想一下。
可能前一秒還在想導演長得挺有特點的,下一秒就開始想等一會兒要吃什么,接著又想到自己平時跟同學打鬧的場景,想工作上的事,再想到自己好像已經好久都沒有回家了,真的好想休息一段時間,回家看看……各種事情都想,但每件事情又都不會想得很仔細,因為在那種封閉、黑暗的環境下,想這些純粹就是為了消磨時間。
我在想的時候手里還拿著牙刷玩,后來又拿起梳子玩。但到最后,我把能想的事情都想完了,就完全像靈魂出竅了一樣,腦子里一片空白。過了一會兒,又猛然醒過神來,想:“我到底坐了多久?是不是已經很久了?”
整個人越來越焦躁,感覺周圍越來越熱,渾身癢,連空氣也變得稀薄。我開始想:“是不是因為排風扇沒有打開,里面沒有氧氣了?我再不出去會不會被憋死?”我開始為自己想要出去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一會兒想:“實在待不住了!我要出去!”一會兒又想:“不會這么快就認輸吧!萬一只過了5分鐘呢?”
慢慢地,我就開始沒有時間概念了,就開始感覺自己呼吸不上來了,越感覺呼吸不上來就越呼吸不上來,腦子里想著肯定是因為排風扇沒有開,衛生間里都快沒有氧氣了。其實里面是有足夠的氧氣的,雖然沒有開排風扇,但那個空間不是全封閉的,還是有氧氣進來的。所以當時我一邊掙扎著想出去,一邊又猶豫要不要再堅持一下,后來覺得真的不行了,一秒都待不下去了,要被逼瘋了。
最后實在忍不住,心急火燎地奔出衛生間,在觸到門把手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那一刻我又感覺還能待會兒。出來之后我被告知,我在里面只待了兩個多小時。
導演雖然沒有細說,但我大概明白了他想要我體會的那種在黑暗中焦灼、無助、無人訴說又無法忍耐的感覺。剛進去的時候我待得很認真,心態很平和,到后面就開始煩躁、不安、焦慮。因為在那種讓人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下,沒有任何人看著你的時候,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冒出來,會更深層次地了解自己到底處在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會感覺到身體里那些被隱藏的、負面的東西。
所以在試戲時,導演會想辦法把我這種極端的情緒激發出來,我自己也在嘗試,因為那種情緒釋放出來對自己會更好一些。
其實我很期待一個不是很平順的角色,但又很清楚那樣的角色不是輕易就能演好的,那種角色的情緒不是輕易就能釋放出來的。畢竟不是你覺得演得爽,就可以拼命地邪惡下去,那樣反而顯得很假。人真正陰暗的一面,其實不是那么容易演出來的。就像希斯·萊杰演的那個小丑角色,在表演過程中,他其實已經把自己的元氣傷了,那是一種精神上的創傷。
我在生活中并不是一個大大咧咧的人,那些負面的東西都是要靠自己來消化的,而消化的辦法就是忘記它,想一下之后就不要想了,就去想別的事情。說白了也沒有忘,只是不去想而已。
雖然最后因為檔期原因那部戲我沒有拍成,但還是很開心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導演。后來大家碰面時,都會提起那次試戲的經歷,他們都說我是只兇猛的小野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