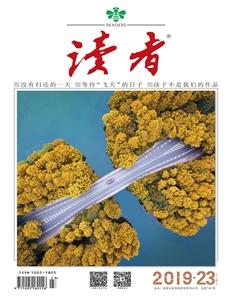意林

覺醒
〔印度〕安東尼·德·梅勒 夏建清 譯
“大師,我該做些什么使自己覺醒呢?”
“如同清晨使太陽(yáng)升起,你無(wú)能為力。”大師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您所說的精神修煉又有何意義呢?”
大師答:“意義便在于太陽(yáng)升起時(shí)確保你醒來。”
(李 江摘自新浪網(wǎng)譯者的博客)
漸入佳境
劉墉
唐代名畫家閻立本,在荊州看到梁朝大師張僧繇的作品,初見時(shí)頗為鄙視地說:“張僧繇只是徒具虛名而已。”第二天去看則改口講:“還算是近代畫壇的好手。”第三天再去看,卻驚嘆地說:“真是名不虛傳哪!”從此睡在張僧繇的畫下,朝夕參法,十多日才離去。
由此可知,我們對(duì)一件藝術(shù)作品不能一見就下定論,而當(dāng)觀之、游之、居之,深入玩味,才能得個(gè)中奧妙。為人交友不也是如此嗎?
(田龍華摘自北京聯(lián)合出版有限公司《螢窗小語(yǔ)》一書)
蘇章斷案
李宏
漢順帝某年,蘇章被任命為冀州刺史。他在審理積案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大貪污犯清河太守,正是他以前最要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蘇章備下酒菜,請(qǐng)來那位老朋友。二人一邊喝酒,一邊暢敘舊情,十分快樂。這位清河太守的心里,原來是十五個(gè)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摸不透蘇章對(duì)自己的罪行采取什么態(tài)度,這下好像石頭落了地。他長(zhǎng)吁一口氣,得意地說:“人家頭上只有一頂青天,唯獨(dú)我頭上有兩頂青天啊!”蘇章正色道:“今晚我請(qǐng)你喝酒,是聊盡私人舊誼;明天冀州刺史開堂審案,卻是執(zhí)行公理王法。”
第二天,蘇章正式開堂,對(duì)這個(gè)清河太守判刑定罪。
此之謂:“先盡私情,再了公事。”朋友之情固然重要,但國(guó)家法律更為神圣!
(聶 勇摘自遼海出版社《料事如神》一書)
煙火
〔荷蘭〕文森特·凡·高 平野譯
每個(gè)人的心里都有一團(tuán)火,路過的人只看到煙。但是總有一個(gè)人,能看到這團(tuán)火,然后走過來,陪我一起。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他的火,然后快步走過去,生怕慢一點(diǎn)他就會(huì)被淹沒在歲月的塵埃里。我?guī)е业臒崆椤⑽业睦淠⑽业目癖⑽业臏睾停约皩?duì)愛情毫無(wú)理由的相信,走得上氣不接下氣。
我結(jié)結(jié)巴巴地對(duì)他說:“你叫什么名字?”從你叫什么名字開始,后來,有了一切。
(嘉 良摘自南海出版公司《親愛的提奧》一書)
距離
張宗子
《哈扎爾辭典》這樣形容作者和讀者的關(guān)系:兩個(gè)男人各扯緊繩子的一頭,繩子中間拴一頭獅子。他們倆若想靠近,松掉繩子,就會(huì)被獅子咬傷。所以,只好一直拉緊繩子,使獅子和他們保持同等的距離。這兩個(gè)人,一個(gè)是作者,一個(gè)是讀者,獅子就是那本書。
(夕夢(mèng)若林摘自商務(wù)印書館《梵高的咖啡館》一書)
與誰(shuí)為鄰
周振國(guó)
蘇州拙政園中有一座別致的扇形小亭,名“與誰(shuí)同坐軒”,取意蘇東坡《點(diǎn)絳唇·閑倚胡床》中的句子:“與誰(shuí)同坐?”旅游景區(qū)的一座休閑亭子,坐與不坐,與誰(shuí)同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即便是一次出行,與誰(shuí)一起,好與不好,說到底就是一次短暫經(jīng)歷而已。但人生路上,與誰(shuí)同行,或與誰(shuí)同坐,恐怕就得琢磨琢磨了,想必這也是“與誰(shuí)同坐軒”的巧妙用意吧?
(鶴 鳴摘自《鄭州日?qǐng)?bào)》2019年5月17日,123RF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