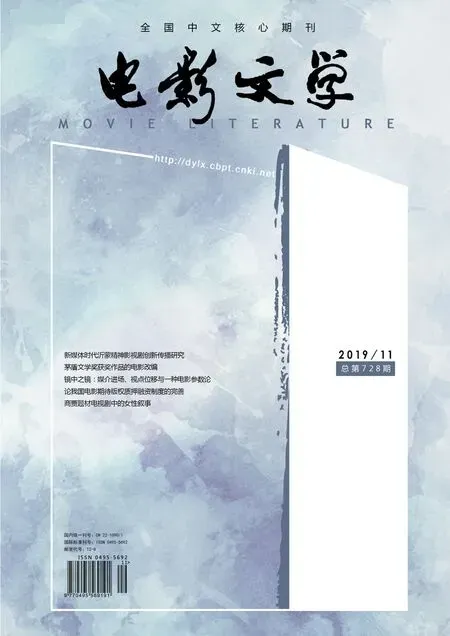《搖擺狂潮》舞蹈與意識形態(tài)象征
關(guān) 冠 (長春師范大學(xué) 音樂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000)
藝術(shù)的緣起往往與社會結(jié)構(gòu)向前進(jìn)步緊密相關(guān),不論是政治形式的革新,還是科技手段的進(jìn)步,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藝術(shù)內(nèi)容的表達(dá)、形式的變化起到深刻的變化。或者說,藝術(shù)的本質(zhì)雖然是對情感的表露形式,是一種個人精神的審美再現(xiàn),但是當(dāng)人類文明社會初步建立之后,這些藝術(shù)手段,也同樣適用于對社會整體觀念的傳播,對個人的思想觀念的轉(zhuǎn)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藝術(shù)本身也因此具有了意識形態(tài)的傳播作用。這種傳播使得特定的藝術(shù)形式與相對應(yīng)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1],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藝術(shù)也就具有了意識形態(tài)屬性,成為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象征物。
具體來說,在很多文本中,藝術(shù)形式的展現(xiàn)都與政治的關(guān)系演變結(jié)合在一起。在《搖擺狂潮》這部電影文本中,舞蹈就成為政治關(guān)系的主要隱喻與矛盾展現(xiàn)的核心。這部電影將文本的時代背景設(shè)定在了一個政治關(guān)系相對敏感和對立的時期,雖然在文本表達(dá)上,因為政治立場的原因,創(chuàng)作者帶有非常明確的主觀因素,使電影文本的表達(dá)不能夠充分展現(xiàn)出應(yīng)有的價值。但是電影文本中對于舞蹈和政治關(guān)系的表達(dá)卻獨具新意,從舞蹈活動確立的主觀政治意圖到舞蹈藝術(shù)跨越意識形態(tài)的溝壑為個人的自由意志進(jìn)行解放,都進(jìn)行了相對深刻的表達(dá)和完整的敘述。因此從意識形態(tài)與藝術(shù)的,尤其是與人的關(guān)系的角度進(jìn)入這部電影文本,實際上具有非常正面的意義,也必然會對理解相關(guān)題材的電影文本提供有益的幫助。
一、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與舞蹈藝術(shù)活動
《搖擺狂潮》這部電影文本的時間背景設(shè)定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由美軍建立的戰(zhàn)俘營當(dāng)中,發(fā)生在美軍與各種勢力戰(zhàn)俘之間的斗爭與博弈,在這場政治博弈當(dāng)中,主人公的舞蹈表演身份成為最重要的矛盾之處。
如果按照故事時間的順序,可以發(fā)現(xiàn)在電影敘事剛剛開始的部分就已經(jīng)表達(dá)了意識形態(tài)與舞蹈藝術(shù)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美軍為了國際聲譽(yù),策劃了一場專門展示戰(zhàn)俘與美軍友好關(guān)系的演出,為了這場演出的政治效果,美軍指揮官要求必須有朝鮮的戰(zhàn)俘共同參與,尤其是舞蹈表演的環(huán)節(jié),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的朝鮮戰(zhàn)爭英雄的弟弟,也是本部電影的主人公的參與成為最重要的爭取對象。換言之,這場舞蹈活動在開辦之前就被賦予了非常明確的政治立場,舞蹈成為為意識形態(tài)政治服務(wù)的工具。但是從表演活動招募的過程中,抑或是隊員之間相互磨合的過程中,政治的因素實際上被排除在外,這次舞蹈活動反而成為一種逃避政治規(guī)訓(xùn)的隱蔽空間。因此舞蹈活動就成為具有二律背反的概念:它既是政治號召的產(chǎn)物,同時也是回避政治約束的庇護(hù)所。
在這種矛盾的概念之下,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就日漸突出。在舞蹈活動中,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是先驗存在的,什么形式的舞蹈決定了欣賞舞蹈的對象,而舞蹈服務(wù)的對象就成為意識形態(tài)最主要關(guān)注的問題。在電影文本中,舞蹈服務(wù)的主體從不同的立場上看具有不同的意義,蘇聯(lián)式的舞蹈被視為革命式的藝術(shù)形式,相應(yīng)地,踢踏舞等西方舞蹈形式則被視為從屬于資本主義政治的產(chǎn)物。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政治話語的內(nèi)部,這種舞蹈同樣被視為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表現(xiàn),而被重新賦予意義。電影文本中的踢踏舞者,是一名曾經(jīng)在日本服役的黑人士兵,他的族裔身份同樣被視為資本主義內(nèi)部的他者,或者說從這一個角度上看,舞蹈本身并沒有在本質(zhì)上具有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而是因為不同的立場與參與舞蹈活動的主體的身份,重新使這一藝術(shù)活動具有了立場上的差異。
這種差異當(dāng)然不能簡單按照左翼工具化藝術(shù)形式的角度來理解,而是需要關(guān)注到在任何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內(nèi)部,藝術(shù)勢必會成為表達(dá)的工具。這種成為工具的過程,又同時具有辯證的意義。首先,這一過程難免會出現(xiàn)忽視藝術(shù)發(fā)展的內(nèi)部規(guī)律,使藝術(shù)表達(dá)的內(nèi)容超越了藝術(shù)存在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消減了藝術(shù)表達(dá)的審美意義。但是同時需要注意的是,藝術(shù)的功能因為這個變化的過程而具有了更高層次的拓展,從而對藝術(shù)發(fā)展本身產(chǎn)生積極的促進(jìn)作用。不論是何種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藝術(shù)本身的魅力都不會減弱。比如在電影文本中,被視為敵對陣營的舞蹈形式,同樣吸引了許多戰(zhàn)俘的歡迎。但是或許因為創(chuàng)作者的立場,電影中對其他形式的舞蹈刻畫還不夠充分,存在著輕慢的姿態(tài),這或許和這些舞蹈者本身的舞蹈技巧有關(guān),但是作為文本敘事的內(nèi)在邏輯,這種設(shè)置顯示出了文本創(chuàng)作者視野狹隘的問題,這也使得電影在借助舞蹈實現(xiàn)不同政治立場群體因為藝術(shù)而與自我和解的敘述不夠深刻,由于視野的缺失,導(dǎo)致前后關(guān)系之間的對比不夠突出,甚至有流于表面與程式化的傾向[2],實在是這部電影文本的遺憾。
二、個人借助舞蹈在意識形態(tài)當(dāng)中的反叛實現(xiàn)
在電影文本中,舞蹈在表現(xiàn)形式上的特征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按照參與舞蹈表演的表演者的數(shù)量劃分,可以分為群舞和獨舞兩種形式;在這種類型下,最為突出的是文本最后在圣誕節(jié)進(jìn)行的舞蹈表演,這場表演可以看作是參與舞蹈者對自我身份達(dá)成和解之后進(jìn)行的表演,在這場表演中也同時存在著群舞與獨舞兩種形式。因此也可以說這場表演本身雖然不一定別具深意,但是在這場表演過程中通過群舞與獨舞的表現(xiàn),可以觀察到這場表演當(dāng)中意識形態(tài)與個人的關(guān)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3]。在演出之前,兩種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將這場表演視為矛盾集中爆發(fā)的關(guān)鍵節(jié)點。而在表演過程中,通過群舞的形式,舞蹈藝術(shù)的感染力達(dá)到了高峰,不同意識形態(tài)在這場表演中達(dá)成了一致,但是實際上的根本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這是因為雙方的政治意圖沒有實現(xiàn),甚至在雙方領(lǐng)導(dǎo)者的心中,這種心態(tài)沒有真正意識到問題的核心,對于他們而言,舞蹈依舊僅僅停留在工具的層面,因為缺少真正互相的理解,群舞僅僅解決了真正愿意理解這種藝術(shù)感染力的觀眾。相對而言,在正式的表演結(jié)束之后,主人公進(jìn)行了一段獨舞,究其原因,或許是主人公想實施暗殺計劃,但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也有可能是主人公想通過這段獨舞,實現(xiàn)自己在舞蹈方面的價值,通過舞蹈真正放棄了不能解決問題的暴力身份。
第二種是按照舞蹈表演的場所進(jìn)行劃分,可以分為日常化的舞蹈練習(xí)和正式的舞蹈表演。日常化的舞蹈練習(xí)一方面是通過場景結(jié)構(gòu)本身實現(xiàn)的,另一方面則是在練習(xí)舞蹈時,通過日常的練習(xí)活動表達(dá)出來的,值得玩味的是主人公練習(xí)舞蹈的場所與之后發(fā)生政治暗殺的場所基本一致,實際上是暗示著政治環(huán)境的壓抑與對舞蹈活動的漠視,但同樣是由于創(chuàng)作者的立場的原因,這部電影在展現(xiàn)這個問題時過度扭曲了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形象,忽視了另一個角度上,美軍同樣對這一藝術(shù)活動的漠視。另一種類型,同時也是更加主要的方面,則是正式的舞蹈表演當(dāng)中舞蹈極大的感染力與舞蹈之后對于現(xiàn)實干預(yù)的無力感之間的強(qiáng)烈對比,這種對比營造出了整部電影的悲劇性意義,為這部電影奠定了意蘊(yùn)豐富的文本內(nèi)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