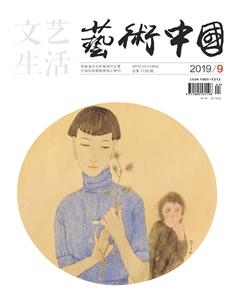信稿人六題
周有光
那天(2001年5月份),突然收到了他的稿子,我大吃一驚。因為在此之前,考慮到他年紀太大,怕打擾他,確實沒給他寄過雜志,也沒向他約過稿子。他的來稿一開始也是這樣說的,說他看的《書屋》雜志是朋友借給他的:
不久前,一位朋友借給我看一本《書屋》雜志。一看之下,我就愛上了它,因為它有清新的氣息。前天,這位朋友又借給我看《書屋》新的一期(2001年第2期)。我首先翻看王若水先生的《試談漢字的優點》,因為我一向喜歡看王先生的文章。
王先生的文章不長,談到好多個語言學和文字學的論點,很有趣。有的論點我完全贊同,有的論點我不能完全贊同。這里對不能完全贊同的論點之一,談談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王先生和《書屋》雜志的編者和讀者。
王先生說:“漢族之所以沒有采用拼音文字而采用了方塊字,這是由漢語的語音決定的。”“西方的多音節語言注定了必須采用拼音,而漢族語言注定了只能用方塊字,這不是誰聰明誰不聰明的問題。”
去年我在另一種雜志上看到一位作家說:“漢語音節分明,沒有詞尾變化,因此創造了漢字;英語音節復雜,有詞尾變化,因此采用字母。”這個說法跟王先生基本相同。從比較文字學來看,這就是所謂“語言類型決定文字類型說”。這個說法今天在知識分子中間相當流行。
可是,在比較文字學的研究中,發現許多相反的事例:類型不同的語言使用類型相同的文字,而類型相同的語言使用類型不同的文字。例如:中國、朝鮮和日本,語言類型迥然不同,可是共同使用漢字。漢族和藏族,語言類型同屬漢藏語系,“漢藏語系”這個名詞就是以漢語和藏語為代表而稱說的,可是漢族使用漢字而藏族使用字母。這不是跟“語言類型決定文字類型”的說法正好相反嗎?
世界上有一百多種語言使用羅馬字母。它們都屬于同一個語系嗎?當然不是。這些語言千差萬別,為什么沒有各自按照自己的特點創造文字呢?比較文字學告訴我們:文化的傳播,同時傳播了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承載體,承載體跟著承載物一同傳播到接受文化的國家和民族。文字跟著文化走,文字類型決定于文化傳播,不決定于語言特點。
在東亞,中國文化發展比較早。中國文化以漢字為承載體,中國文化和漢字一同傳播到近鄰國家,形成一個漢字文化圈。近鄰國家接受中國文化,同時接受漢字,雖然漢字跟他們的語言格格不入,學習和使用漢字十分困難。
印度文化較早就在南亞和東南亞傳播,形成印度文化圈。西藏語言跟印度語言的語系不同,可是早期接受印度文化,屬于印度文化圈,因此西藏采用印度字母,發展成為拼音的藏文。藏文拼寫法脫離語音,那是后來語音變化的結果。云南的傣族有四種傣文,他們的語言也跟印度不同,可是都從印度學習文化和字母,變化成今天的文字形式。
人們的認識是逐步發展的。從“語言類型決定文字類型”,到“文化傳播決定文字類型”,是一次超直覺的認識發展。這很像地球跟太陽的關系。東方日出,西方日落,大家看見太陽繞地球旋轉,這曾經認為是無可爭辯的事實。誰提出相反的說法,認為地球繞太陽旋轉,那是擾亂視聽的邪教,要受到火刑處分。可是,天文學家經過深入觀察,終于認定地球繞太陽旋轉才是真理,今天成為大家的常識了。這不是直覺得來的知識,而是從科學實證得來的超直覺的知識。
西方人常說,“字母跟著宗教走”。宗教是一種文化,字母跟著“宗教”走,就是字母跟著“文化”的傳播走。歐洲中部從北到南有一條字母分界線,線西信天主教的新教用羅馬字母,線東信東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同樣是斯拉夫語言,俄羅斯和保加利亞等國信東正教,用斯拉夫字母,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信天主教,羅馬字母。在前南斯拉夫境內,由于宗教不同,同一種語言寫成兩種文字:塞爾維亞信東正教,用斯拉夫字母,克羅地亞信天主教,用羅馬字母。
印度的印地語和巴基斯坦的烏爾都語實際是同一種語言,叫做印度斯坦語,可是由于印度信印度教,用印度字母,巴基斯坦信伊斯蘭教,用阿拉伯字母,形成印地文和烏爾都文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
文字有“自源”和“借源”的分別。自己創造的文字稱“自源”文字。外界傳來的文字稱“借源”文字。英語的文字,最早采用原始的魯納字母,后來采用愛爾蘭變體羅馬字,最后采用近代羅馬字。這不是語音的變化使英語的文字變化,而是文化的變化使英語的文字變化。日文是“借源”文字,“借源”于中國,經過四步變化:第一步,學習漢語漢字;第二步,借用漢字書寫日語;第三步,模仿漢字創造倭字;第四步,簡化漢字創造假名。借用方法有三種:一、訓讀,借字義、讀日語;二、音讀,借字音、記日語;三、借詞,日本沒有的事物,字義字音兼借。假名的創造,在形體上沒有離開漢字,只是簡化了筆畫,在原理上學習印度。假名的排列方法,“伊呂波歌”是一節佛經,“五十音圖”傳說是空海和尚的設計。這說明日本除中國文化之外,又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
在漢字文化圈中,有的民族借漢字的部件,疊成自己的新字。例如越南的“喃”字和壯族的“壯”字,這是“孳乳”仿造。有的民族借漢字的原理,另造自己的字形,很像漢字,不是漢字。例如契丹字和女真字,這是“變異”仿造。不論“孳乳”還是“變異”,都沒有離開漢字文化的影響。
歷史上許多民族創造過原始文字,只有極少幾個民族的文字達到完備地記錄語言的成熟程度,成為嚴格意義的“自源”文字。它們是:五千五百年前的丁頭字和圣書字,三千三百年前的漢字,一千七百年前的馬亞字,五百年前的彝字(年代是最早文字遺跡的時期)。此外的文字都是有意無意借入原理而自造形體,或者原理和形體一同借入……(《談談語言和文字的類型關系》,《書屋》2001年第7期)
怎么樣?說得條條是道吧?不但條條是道,而且簡明扼要。我還從來沒有看見誰能在這樣簡短的篇幅里把文字的來源和發展說得如此清楚的。他就這樣不急不忙一句一句地說下去,說到最后總結道:“以上的例子都說明,文字類型不是由語言類型決定的,而是由文化、特別是宗教的傳播而形成的。這個認識已經成為比較文字學的基本認識之一。”說罷,他還補充道,“我今年(2001)九十六歲,耄耋之年,知識老化,所談一定有不妥當的地方,敬請多多指正。”真是滴水不漏呀。你不能不佩服他。
他身上的標簽很多:作家沈從文的連襟、才女張允和的丈夫、經濟學家、語言學家。他一輩子活出了好多人的幾輩子。他的一生可分為這么幾個鮮明的階段:五十歲以前是銀行家;五十歲到八十五歲,是語言文字學家;八十五歲以后,是思想家。
若挑部分年度來看,評價基本是這樣的:1969年至1971年,他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社會渣滓”。1972年,他被稱為“沒有了用的”“專家專家,專門在家”。1985年在參與中美文化合作時,他的連襟沈從文送他“周百科”的外號。2006年,他百歲壽辰時,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認為他“是一百年來無數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征。”2008,《晶報》稱他“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具有“高明的處事哲學和積極達觀的心態”。201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介紹他是“卓越的語言文字學家”“具有……完美的人格品質”。2013年,臺灣作家彭小明則認為“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分子。”2015年,他110歲壽辰時,詩人邵燕祥說“他是當代難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東方早報》稱他是“一位通達、樂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評網稱他具有“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以及寧靜淡泊、生活清貧簡樸、思想無比富有的生活態度。
周有光,本名周耀平(1906-2017),生于江蘇常州,中國著名語言學家。早年研讀經濟學,1955年調到北京,進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有著作《漢字改革概論》《世界文字發展史》《中國語文的現代化》等。
程千帆
1991年,傅璇琮先生在給程千帆先生的一封信中,曾向程先生提出過一個建議,他說:“在文史學界,先生實是承前啟后,對辛亥以后至二三十年代學術界有親身接觸。如能以回憶錄的形式,或以自傳的體裁,寫數十年來社會、人生及學界情況,其本身價值即非一般所能代替。”(《程千帆友朋詩札輯存》第二冊,藏南京大學檔案館)
這是肯定的,毫無疑義的。我向他約稿,他即回了信:
周實先生:
收到刊物大函,是個極富個性和風格的刊物。感謝。我年八十五,耳極聾,眼又近瞎,稿大概寫不成了。寄上新出一本書,請無事翻翻。
祝
冬安
千帆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
新書是《程千帆沈祖棻學記》。那年十月第一版,只印了三千冊。現在想來,我真蠢,當時為何就沒想到可從其中摘一篇呢?比如他的《閑堂自述》。下面,我就摘一段:
我原名逢會,改名會昌,字伯吳,四十以后,別號閑堂,千帆系我曾用諸筆名之一,現在通用此名。祖籍湖南寧鄉,老家在土蛟湖竹山灣(現改屬望城縣),但上代已遷居長沙。1913年9月21日(農歷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長沙清福巷本宅。
我家境清貧,但數代以來就有文學傳統:曾祖父名霖壽,字雨蒼,有《湖天曉角詞》;伯祖父名頌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遺集》;叔祖父名頌萬,字子大,有《十發居士全集》;父親名康,字穆庵,有《顧廬詩鈔》。母親姓車,名詩,字慕蘊,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賡,字伯夔,僑居湖南,以書法知名當時。我三歲時,母親就去世了,我的兒童時代是在外家度過的。1923年左右,因軍閥混戰,在長沙不易謀生,我家遷居湖北武昌,我也回到自己家里。在武昌住了五年,短期進過武昌圣約瑟中學附屬小學和漢口振華中學,但大部分時間是隨堂伯父君碩先生學習的。伯父名士經,是子大叔祖的長子,以早慧知名,二十歲以前,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集《曼殊沙館初集》,他是我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啟蒙老師。1928年秋,我赴南京,考入金陵中學初中三年級,從此接受了八年正規的現代教育,1936年畢業于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
大學畢業后,我先在金陵中學任教一年。抗日戰爭爆發,避難安徽屯溪,在安徽中學任教,就在那里和沈祖棻結婚。1938年春,輾轉回到長沙,在益陽龍洲師范學校教了一個多月書,又因生病離開。其后,為了逃避日寇及糊口,曾流轉于武漢、重慶、康定等地,在國民黨西康省政府中任一小職員,直到1940年才重回教育界,在四川樂山技藝專科學校擔任國文教員,生活稍為安定,可是因種種關系,工作單位仍屢次變遷。1941年到1945年,先后任教于當時在樂山的武漢大學,在成都的金陵大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立成都中學。1945年抗戰勝利后,才又回到武漢大學,一直延續了三十二年。
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直到1975年才摘掉帽子,而得到徹底改正,又是幾年之后的事了。摘帽后,我就奉命“自愿退休,安度晚年”。1977年,沈祖棻在一次車禍中逝世,又給我一次極大的打擊。在劃為右派分子的十八年中,參加過各種繁重的勞動,承受著難堪的侮辱。這些,我并不怎么在意。所感到惋惜的,乃是在我年富力強、學問稍有基礎的時候,工作機會卻長期被剝奪了,以致一生成就很少;否則,也許能為祖國和人民多做出一些貢獻。
1978年夏,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先生聘請我這已經六十五歲的街道居民為南京大學教授,從而開始了我新的學術生涯。翌年,和陶蕓結婚。在初到南大時,我就暗下決心,要努力工作,奪回失去了的時間。十二年來,我帶出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著作、編輯、整理了十多部書籍。在還想繼續前進的時候,年齡已達七十七歲,心臟病更使我精力日衰,便在1990年5月退休了。對于沒有能全部奪回被浪費了的時間,我始終感到很深的遺憾……
歲月易逝,人事多乖,赤子之心,令人傷懷。
至于他的夫人,江南才女、著名的詩人詞人沈祖棻先生,就更非我輩能說的了。我最記得的是常任俠先生的一首詩:
一代詞人憶沈娘,土星筆會寫瑤章。背人歌哭臨江樹,黃鶴千帆下夕陽。
還有朱光潛先生的兩首詩:
易安而后見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身經離亂多憂患,古今一例以詩鳴。
獨愛長篇題《早早》,深衷淺語見童心。誰說舊瓶忌新酒,此論未公吾不憑。
程千帆(1913-2000),我國著名的古代文史學家、教育家,在校讎學、歷史學、古代文學、古代文學批評領域均有杰出成就,有著作《校讎廣義》《史通箋記》《文論十箋》《兩宋文學史》等。
周一良
我向他約稿,他給我回信:“周實同志:來信及刊物均收到,多謝之至。程巢父先生亦曾來電話推薦你刊,惜‘雜記及‘三杰兩文皆有前約,不便翻悔,抱歉之至。關于吳宓先生的文章須待十本日記讀完之后始知有無足夠材料。目前只讀完一冊。如能成文,定當寄呈,供審閱也。即請著安!周一良2001.1.21。”從這回信來看,一時是拿不到他的稿了。不想四月二十六號又突然接到了他的來信,而且是掛號的:“周實先生:茲寄上稿件,想在《書屋》雜志發表。請考慮是否可行。即頌 日祺 周一良四月廿四日 另:因敝寓尚未通郵,請寄歷史系轉。”寄來的是什么稿子呢?是他看了謝泳的《楊聯陞為什么生氣》后所寫的一點質疑,或者說是他為楊聯陞所作的一點解釋。我當即就發排了。發排后,五月十七日,突然又收到他的來信:“周實同志:上次美國電話說得太簡單(周實注:文中所寫的內容),以后又請他把楊的日記逐字念聞,因此文章改寫,今寄上,前稿請作廢。多謝。敬禮 周一良。”于是,我又將此稿重排。此后,五月二十三日,突然又收到他的來信:“周實同志:我考慮楊的病情原因是遺傳,最好文中不提,以免影響他的家人。現將修改稿寄上,并將前稿毀去。如能讓我看校樣更好,麻煩你,多謝之至。請務必用此改訂稿。敬禮 周一良2001.5.18。”于是,我又將稿重排,并將校樣寄他校訂。這篇稿子很短,只有一千五百多字,是他口授,由歷史系研究生筆錄而成,文后他特地表示了感謝。下面就是他這篇短文:
謝泳同志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的遭遇,掌握豐富的資料,分析深入透徹,且富于同情,我讀后常常深為感動。但這篇《楊聯陞為什么生氣》(載《書屋》雜志2000年第10期),我卻有不同看法。
此文根據趙儷生先生的書,似乎楊聯陞是一個毫無禮貌、不近人情、甚至自命為美國人的“高等華人”,我想這中間是有誤會。大概趙先生和謝泳同志都不知道楊聯陞是個有病的人。一九五八年,他開始患精神病——抑郁癥,犯病后腦子活動無法控制,煩躁不安,沒有一刻安寧,身體虛弱無力。嚴重時甚至立下遺囑想自殺,必須進醫院進行電療。一九五八年犯病后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份才開始好轉。以后每一兩年病一次,一般少則三五個月以后好轉,長則經年,大體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
楊聯陞是很好客的,差不多每周都有兩三次招待客人來吃飯,來客的留言簿三十年中就有十六本之多。但是,當他生病的時候就絕對不會請客人來。據道申同志(周實注:楊聯陞的兒子)所抄錄的留言簿來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留言簿全是空白,這恰是趙先生訪美的時間。以后的五月、六月、八月、十二月共只有四次來過客人吃飯。道申同志從日記中查他父親的詩詞,一九八六年有詩十三首,直到一九八七年七月五日,才又有一首,中間全是空白。這些情況都說明一九八七年四月趙儷生先生去美時,楊聯陞很可能尚在病中,或者大病初愈。
今年四月中旬,恰巧道申同志的兒子華岳赴美留學,于是叫他到祖母那里查閱他祖父的日記。華岳電話報告說,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這一天的日記是:“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館來電(71歲,可能認識蔣浮萃),不能吃外國飯,旅館七十五元一天太貴,應來三個月,已去(華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華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認識山東大學某公□□□□□□(華岳注:有半句看不清),氣一女士照應不力。”日記一側有“愛莫能助”四字,字體、墨跡與當日日記不同,顯然是日后加上去的。
楊聯陞的日記,不像李慈銘那樣是預備給后人看的,可信程度應該較高。首先,他似乎不知道來者就是山東大學的趙儷生;其次,兩人那一段極不愉快的對話不見于日記中,這有幾種可能:或者楊故意不記,或者楊因病中,神經不健全,因而沒有記,而事后追記的“愛莫能助”四個字和趙儷生書中所說又似乎有矛盾。總而言之,楊聯陞當時是不是這樣生氣恐怕還是個問題吧。
謝泳同志懷疑楊聯陞那一席話,是他回想起清華做學生時期,左派學生和右派學生之情況而引起的,這種解釋我也有所懷疑。
據我所知,楊聯陞作學生時,政治傾向是中間偏右。到美多年以后于政治更不關心。在他心目中,業務高于一切,他一九七三年回國主要是因為總理對回國探親的趙元任夫人說:“楊聯陞、毛子水(兩人都是胡適指定為其整理遺稿的人)我都知道,我們歡迎他們回國看看嘛!”楊聯陞當時很小心,很多親戚、朋友都不敢去看,怕連累他們,只有周一良因為是“梁效”成員,不會受到影響,所以要求見周。從這種心態看來,說他還斤斤于幾十年前清華同學中左右派之爭,似乎無此必要吧。
總之,楊聯陞是否如此生氣,如果生氣是為什么原因,恐怕還是個謎。
關于楊聯陞去美,并非公派。經過是這樣的:我經洪煨蓮先生介紹,給當時在北京的哈佛大學教授賈德納先生搜羅并翻譯日文資料。三十九年前我獲得哈佛獎學金,將去美國,賈德納很愿意我再推薦一人幫他,我當時初識聯陞,對他極為佩服,但不知他日文如何,所以征詢了錢稻孫的意見。錢認為可以勝任,我就把他推薦給賈德納先生。后來賈回到劍橋,想讓我繼續幫他閱讀日文雜志,而我那時已領取哈佛的全時獎學金,不得再兼職業,因此賈德納先生自費邀請聯陞來美一年幫他工作(賈家里比較富裕,故有此能力)。聯陞到美后,在賈家吃住,以后因受知于趙元任先生遂領取哈——燕京獎學金,成為正式研究生。謝泳同志文中說:“楊到美國去是正常的留學生,初期還是公派。”不夠確切。
此稿發表在《書屋》雜志2001年7月號上。此稿雖短,但情意不短,尤其是如何實事求是看待過去的是非人事令人提醒自己謹慎。此稿發表后兩個多月,不到三個月,也就是十月二十三號,他就去世了。
周一良(1913-2001),安徽建德人,即今東至人,北京大學教授,有著作《亞洲各國古代史》《中日文化關系史論集》《周一良學術論著自選集》《周一良學術文化隨筆集》《畢竟是書生》《鉆石婚雜憶》《郊叟曝言》等。
顧學頡
周實先生:
您好!
大札誦悉,謝謝。承蒙黃先生的盛意,向您社推介文稿,他常來訪。惟因年老多病纏身,不能經常執筆,誠為憾事。
四十年代,我曾執教于貴省兩省高校,猶有舊情,故于貴社征稿,亦屬義不容辭。昔年曾擬撰白居易八考,已完成并發表其中數篇。惟思想考為中心問題之一,雖有腹稿多年,迄今尚未著筆。但內容豐富,非短箋尺幅所能容納;亦非限期可就。故于貴刊性質,恐有未合,或當另作考慮也。
專此,順頌
編祺
顧學頡
1997.12.12
我也和他一樣,也是承“黃先生”即《隨筆》的老主編黃偉經先生的“盛意”介紹才知道了他的一些情況:他1938年畢業于北平師范大學,1939年后歷任國立西北大學、西北師范學院、湖北師范學院、湖南師范學院、私立民國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譯所高級編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1957年因直言犯忌被劃為“右派”,是我國元代戲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的專家。他編選、校注的作品和著作有《元人雜劇選》(1956年)、《醒世恒言》(1956年)、《今古奇觀》(1957年)、《隨園詩話》(1960年)、《白居易詩選》(與周汝昌合著,1963年)、《白居易集》(全四冊,中華書局1979年,國內第一部白居易全集白話注釋本)、《元曲釋詞》(全四冊,與王學奇合著,1983-1990年)等十幾種。
我當然立即向他約稿。稿雖未約到,我并不灰心,繼續向他寄送刊物,他的信稿終于來了:
周實同志:
您好!
承您寄來貴刊多份,開卷有益,謝謝!
看到貴刊載有八股文談一則,頗有意義。因憶及舊時聽到的趣事,也寫了一篇小文,寄上,殊不如文正義先生之引經據典也(周實注:《話說八股文》,作者文正義,發表于《書屋》1998年第5期)。
如有可取,請發表,可以湊湊熱鬧。祝
編祺
顧學頡
1998.5.18
我的父親(顧復周)是清末的廩貢生(秀才中最高一級),我幼年曾看見他當年考試的卷子(白宣紙裱成的折頁,有些卷子,發還給本人),還有試官加上的圈圈點點,和卷面上批的獎金(×百文)數目。我也看不懂,只覺得很好玩。那時,八股文早已廢除多年了,僅僅聽到別人談論的一些話。
又及
當然可取,當然發表,這還用說?且看他說的兩件趣事(《“八股文”趣談》,《書屋》1998年第6期):
一個老師出題叫學生作文,題目是“三十而立”(《論語》中的話)。一個學生很快寫出:“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焉。”二乘十五是三十,是破“三十”二字的。下句有椅子板凳不敢坐,只能“站”著,是破“立”字的。他把立字誤解為站立的立。老師看了大笑。
某地修建一所二郎廟,請一位老學究做一篇“二郎廟記”。老學究習慣了做八股文,就用八股文的筆調來了一個“破題”式的開頭:“夫二郎者,老郎之子,大郎之弟,而三郎之兄也。”(這是緊扣“二郎”兩字的)。接著說:“廟前有二樹,或曰:廟在樹后耳。”廢話一大堆,實在讓人看了發笑。
那時諸如此類的文字,觸目皆是。即如應用文體中的書信(八行書),第一頁滿篇全是恭維對方的話,千篇一律,毫無內容。所以接信人從第二頁看起。其根源也與八股文有關。五四時期提倡新文化運動時,我的老師錢玄同先生就著文談到這個問題。直到近代,有的人寫文章,作報告,起承轉合,引經據典,一片華而不實、千篇一律、毫無內容的言詞,被人諷稱為洋八股、黨八股,實際也是受了“八股文”的流毒,所以我們對它的毒害性不可低估。
這篇文章發表后,也就是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情況真的是“年老多病纏身”呀。
他的父親顧復周,我亦做了一點功課:顧復周(1874—1935),字我,別號於如道人、帶涢閣人。曾創辦湖北隨縣模范小學,任過應城第一高等小學校長、隨縣商會主席等職。攻理學、佛學,擅長書畫金石。民國初,于城外東南隅營“曉園”,嘯傲其間,以詩酒著述、書畫篆刻自娛,尤以書法馳名,篆、隸、行、草各體,均為世所重,縣城商號大多為其書寫,縣內外求其手墨者每日皆有。苦于鴉片之毒害,專撰《勸戒洋煙賦》,亦莊亦諧,宜俗宜雅,并以楷體自書長卷,頗為現當代著名學者所珍賞,黃苗子、顧廷龍、夏承燾、王季思等諸多名家在卷后題詩作跋。六十歲時曾自壽撰聯:五百年涢水鐘靈,東山品望西山學;六十載梅花索笑,南枝挺勁北枝高。1935年病逝,葬城東北梁家橋之原,不封不樹,以遂返古歸原之初旨。他去世后,著名學者高步嬴親撰墓志銘,深贊其學行。著有《書法輯要》三卷、《於如道人詩萃、文萃》及印譜、印存、石譜等各若干卷。
顧學頡(1913-1999),有著作《顧學頡文學論集》《坎齋詩詞錄》《海峽兩岸著名學者:師友錄》《說古道今》《元明雜劇概說》等。
徐中玉
從《書屋》創刊開始,我就一直給他寄贈雜志,向他約稿。為什么?因為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的初期,他曾與南京大學的匡亞明先生攜手組編并重新開設了《大學語文》這門公共課。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后,這門公共課也就停止了,從此中斷了三十年,導致高校的人文教育幾乎成為一片荒漠。為此,我特敬重他可惜的是,他來稿時,我卻正辦理調離手續。
周實先生:
一直承贈閱貴刊,十分感謝。這是我仔細必讀的刊物之一。佩服。
寄此短文,只是為了表示一點支持的謝意。是為“文藝爭鳴”(長春)提出的四個問題直抒己見的。他們大概想編成一本書,分題輯出。年內未必能出來。匆此祝
健
徐中玉
2001.6.26
我立即給他回了信,他也立即回了信。
周實同志:
信收。想不到“書屋”如此好的刊物會有較大的變化。大作(周實注:在《芙蓉》和《創作》上發的短篇系列《刀俎之間》)一口氣讀完,現實意義可佩,怵目驚心,文情都屬上乘。這方面也是深具傳統,有時還于今為烈的。千字短文,原只為表示一點謝忱,多不盡欲言也。社會進步,不可逆轉,但望不只有一點迷人的文字功夫而已。自當一如既往,盼能讀到大作。匆此祝
健
徐中玉
(2001)7.10
我也很是喜歡聽他的這些“不盡欲言”:
沒出息的人才千百遍地象念經一般盲從別人的結論,私心太重的人才不敢堅持正確的東西而隨風俯仰。多年風狂浪險,值得“自以為是”的人太少,而不必要地“自以為非”的人卻太多了。這對學者來說,決非好現象,實在很可悲的。(《為學必須實事求是》)
學術研究工作,特別需要能于勇于堅持獨立思考品格的人才。現在講創新的很多,講需要能于勇于獨立思考,質疑問題的卻不多。要善于引導,再不能總喜歡馴服工具了。曹禺晚年自悔所以沒再創作出早期那些好作品,就因為自己“太聽話”了。“太聽話”就不能突破自己,有所創新,甚至還會滑下去。(《“和而不同”與“殊途同歸”》)
我從不迷信文學流域內五光十色的主義,中間也或有一些亮點可以注意。開始時有些新意,到了成為主義,便以為可以解決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這把鑰匙可以開通所有的鎖了。主義容易變成陷阱。(《“和而不同”與“殊途同歸”》)
我喜讀中國古代的文藝評論文字,篇幅短,文字簡要,往往非常精彩,而且具體生動。讀古人這些文字,很輕松、愉快,又有所得。他們不是為名利而寫,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現代論文,洋洋灑灑,一兩萬文章,拍拍頭腦,搖筆即來,沒有保留價值。(《“和而不同”與“殊途同歸”》)
他說出了很多人心中沒有說出來的。
徐中玉 ,1915年生,江蘇江陰人,華東師大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理論研究》主編,上海作協第五屆主席,有著作《魯迅遺產探索》《古代文藝創作論》《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自選集》《美國印象》等。
甘惜分
我已經不記得是誰囑咐我給他寄《書屋》雜志了。
我只知道他是搞新聞研究的,是人民大學的老教授。
后來,我上網查了一下,才知他有如下經歷:
1938年2月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奉調到八路軍一二○師任高級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員,后擔任過前線記者。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簽字后轉為新華社綏蒙分社記者,是《綏蒙日報》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47年奉調擔任新華社晉綏總分社編輯,后隨劉鄧部隊前往解放大西南,1949年11月重慶解放后,任新華社西南總分社采編部主任。1954年奉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教,1958年隨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并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4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生導師。1998年離休。200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教授稱號,2009年被授予中國人民大學首批榮譽一級教授稱號。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等職。
他從事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四十年,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理論。出版有《新聞理論基礎》《新聞學原理綱要》《新聞論爭三十年》和《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等著作。《新聞理論基礎》是新中國建立后公開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闡述新聞傳播規律及新聞事業性質、特點、功能的專著。1993年,他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出版,這部辭典由國內一百多位新聞學者和研究者共同編著,是新中國第一部詳細、全面的新聞學辭書。此外,他還撰有大量學術論文。他創建的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是中國內地第一家專門從事民意測驗和調查的學術機構。在他的指導下,中國人民大學開設了“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輿論學原理”等課程。他一直強調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掩蓋事實是新聞的陷阱,制造假象無異于自殺,并由此提出了他的“新聞三角理論”。他的新聞思想首先強調要尊重新聞的客觀規律,新聞規律是第一性的,新聞政策和編輯方針是第二性的。他認為應當是按新聞自身的規律制定新聞政策和編輯方針,而不是相反。這一思想具有針對性。因為長久以來,領導部門常以個人意志發號施令,而不顧新聞工作的自身規律,甚至根本否認新聞工作規律的存在,不承認新聞學。
我喜歡他這樣的學者。我向他約稿。他沒有來稿。但是,在我離開《書屋》之時,他給我來了信:
周實同志:
早聞貴刊改組,近得先生來信。夫復何言。《書屋》是我國高質量的刊物之一……當向前看,不必泄氣……數年來無償看書,感甚感甚,如有新訊,盼告。
……祝安好。
甘惜分
(二○○一年)七月七日
接到他的信后,我給他回了信,告訴了我調動的新情況,給了他我的新地址,還寄了幾本拙著給他,他馬上又來了信:
周實同志:
大作二包均已收到,興甚感甚,我要讀的書太多,興趣又廣,而又年邁,只能慢慢來。《刀俎》讀了二三篇,只一個“酷”字了得,心為之顫。這是祖傳,以至于今。李白生于碎葉,記得是郭老(周實注:郭沫若)傳此,今寫成演義(周實注:指拙著《李白》三部曲),功不可沒。
我搞的是新聞,一出手就是敏感問題,想得多寫得少,出書極難。有一本已寫好六年,走了十七家出版社……走錯了路,無可奈何!
你我年齡可能相差不少(我生于一九一六年),你的寫作成就遠在我之上,可欽可敬。申奧成功,中國新聞出版業可能不能不有所前進。我并不悲觀。天氣酷熱,望保重!
甘惜分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他生于1916年,我生于1954年,確確實實,“相差不少”。
信是寫在宣紙上的,感覺那手字,寫得真的好,不但有力,而且瀟灑。
甘惜分(1916-2016),四川鄰水人,有著作《新聞理論基礎》《新聞學原理綱要》《新聞論爭三十年》和《一個新聞學者的自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