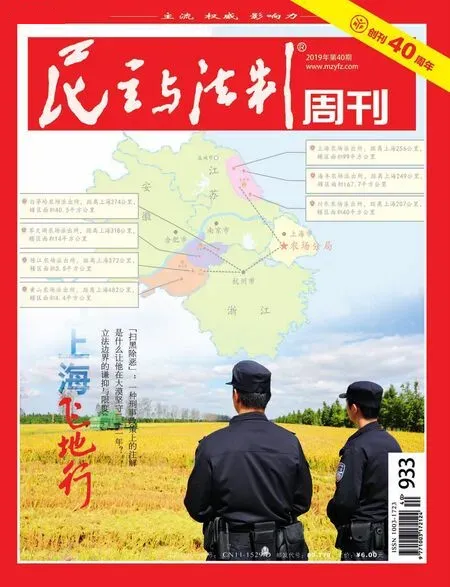一架老120照相機
使用多年的老物件上面有曾經使用的痕跡,而這些痕跡又讓人免不了想到老物件陪伴度過的那些歲月和老物件上曾經寄托過的那些情感。即便它也許已經不能再使用了,也讓人不那么愿意直接丟棄……
說起120老照相機,如今的很多年輕人都沒見過或者沒有聽說過。其實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乃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120照相機可是一件奢侈品。這不,妻子在家整理物品時,翻出了一架我曾經使用了多年的老120照相機,雖然外面的黃皮外套磨爛了,背帶也斷了,但仍然顯得十分親切……
上世紀80年代,我在甘肅省甘南藏區的一個小縣城上班。由于那時文化娛樂少,業余時間我愛上了新聞寫作,并經常在一些報刊上發表些“豆腐塊”。一次,我去州政府所在地出差,順便去經常投稿的州報社送一篇新聞稿。編輯告訴我說,報紙現在嚴重缺新聞照片,能不能多提供些新聞照片?我說我不會拍新聞照片。這個編輯立即領我來到該報的專職攝影記者辦公室,叫對方教我如何拍新聞照片。由于經常在該報發文章,這個專職攝影記者也知道我,立即當起我的老師來,并領我來到他的洗相暗室,指著那些掛在墻上剛沖洗出來的各類黑白照片。于是,我一下子喜歡上了拍新聞照片。
可拍新聞照片要有相機,那個年代這可是普通家庭的大件物品呀。剛結婚成家且有了孩子的我,哪里有錢呀?有道是:“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一天,我路過縣城街頭時,看見一個人在墻上掛了一塊白帆布,脖子上掛了一架120照相機來回走動。這叫“流動照相館”,那個年代非常普遍。我立即上前與他攀談起來,問對方有沒有備用相機,我想臨時租用,按小時付費,所拍新聞照片由他沖洗另外付費。交談之后,雙方一拍即合。
那時拍新聞照片是個燒錢的事兒,不像今天,拍多少都行,存在電腦或手機里。那時還要買膠卷、沖洗膠卷、放大洗印,還要投寄到報刊,最后采用不采用還是未知數。此外,使用過120相機的人都知道,這種機型一盒膠卷只能拍12張長方型照片。由于租用相機,成本較大,我設置了16張正方型,每次多出來4張。新聞照片洗好后我再一張張粘貼在稿紙上,寫上具體內容,投寄給各報刊。我拍的很多新聞照片不斷刊發在省內外報刊上,這一租就是好幾年。
一次我又去州報社送稿時,攝影記者聽說我租相機拍照片的情況后,非常感動。他當即拿出一架大半新的120照相機對我說,因工作調動,他不久將離開報社,這架相機半價賣給我。他告訴我,有了相機后,必須有自己的洗相室。他教了我如何沖洗相片、設暗室,還送了我顯影液、相紙和定影液。回來后,我用小木箱和燈泡,做了一個曝光箱,在天黑后關上門拉上簾,開始自己沖照片。在紅色燈光下,看著泡在液體中的相紙出現了畫面,一種成就感油然而生,還有點從事“地下工作”的感覺。
經常出差的我每次出門,都將笨重的120相機裝進背包里,隨走隨拍,隨拍隨地沖洗。120相機陪伴我的歲月里,我一共在全國各類報刊刊登新聞照片500多幅,有20多幅新聞照片獲獎。如今120相機拍下的那些沖洗后的厚底片,裝滿了幾大文件袋放在家里留作紀念呢。
前幾天,聽見小區內有一個外地收老件物品的,妻子興沖沖地拿著這個老120相機跑下去問能賣多少錢。對方給價500元,妻子問我賣不,我直搖頭。
別說五百了,五千、五萬也不賣,不是為了錢,而是人生的一種情懷和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