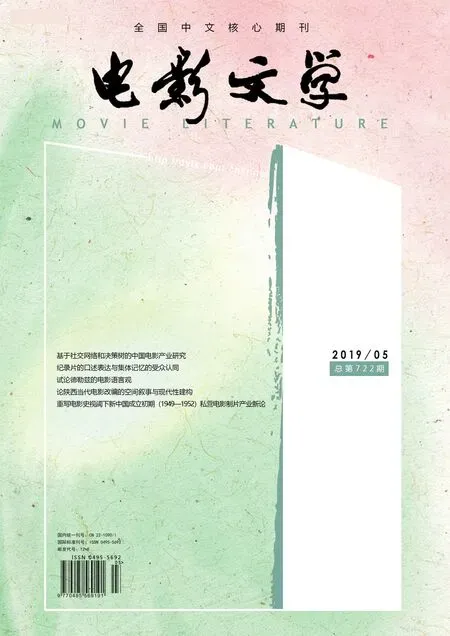論陜西當代電影改編的空間敘事與現代性建構
郭 萌 (西安科技大學 人文與外國語學院,陜西 西安 710600)
以往對于現代性的界定,更多地來源于傳統觀念中以時間為審視角度,從歷史維度上做出縱向的歷時性分析。因為,現代就意味著“我們時代的、新的、當前的,與之相對的是老的、古的、舊的,由此引申出現代就意味著進步的意思”[1]。然而,“歷時態”和“共時態”是現代性研究的兩重基本向度,后者通常是就空間維度而言的。[2]也即是說,現代性不僅體現于時間維度上的變化,同時亦體現于空間維度上的變化。“空間在以往被當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辯證的和靜止的東西。”[3]然而,“空間不可能是社會運行期間的靜止的‘平臺’,反之它蘊含著變化的無限可能性”[4]。由文學文本改編而來的電影所采用的敘事形態——影像,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它將文學文本對于現代性的敘述由間接想象的時間形態轉化為直接可視的空間形態,實現了對現代性的另一維度的建構,進而創造出了無限豐富的可能性。
一、從鄉村到省城:生存空間的現代轉換
在電影《野山》(改編自賈平凹的小說《雞窩洼人家》)中,作為一個“充滿青春活力、熱情、對新鮮事物壓抑不住好奇心的青年農婦”[5],桂蘭對不同于鄉村空間的城鎮空間充滿了強烈的向往之情。這里除了具有琳瑯滿目的商品,更富有足以顛覆傳統思想觀念與生存方式的現代事物,諸如摩托車,電視機,女性的燙發、連衣裙等,新興的現代空間激發起主體對于既定鄉村空間的大膽突圍。這一突圍既表現為對現代物質的極大興趣,亦表現為對現代思想觀念的大膽追求。與桂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城鎮極為排斥的灰灰。對于灰灰而言,城鎮顯然迥異于其所處的傳統的鄉村生存空間與生活經驗,對它的排斥在本質上是對現代文明的排斥,是其固執地堅守傳統農耕文化陣地的表征。如此,在桂蘭與灰灰之間便產生了針鋒相對的由空間敘事所引發的揚棄現代性的藝術張力。
電影《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從一開始便“意識到傳統鄉村生活的單調、孤寂和無知,開始流動、進取,尋求空間的拓展”[6]。影片借助高加林去縣城南關集市上賣饃的所見所聞,諸如耍猴的、敲鑼打鼓吹嗩吶的、賣吃食的、賣時興衣服的等,營造出一個喧鬧繁華的縣城空間,從而與其所處的偏遠僻靜的鄉村空間形成鮮明的對比,進而傳遞出主體對于城市空間所代表的現代文明的強烈的生命體驗。加之高加林在縣文化館的雜志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工廠、礦山、機場,尤其是城市的高樓大廈、寬闊的街道、擁擠的人群等,這些以傳統的紙媒形式呈現的現代性空間,無疑激發高加林做出一番對自我置身于現代空間當中的生存方式與存在狀態的現代性想象,在本質上是其對現代性的自我確證與自覺追求。加之在擔任了縣委通訊員之后,女友黃亞萍帶給他遠走南京的可能性,更進一步開拓了其對于真正的大城市而不僅僅局限于小縣城的更為闊大的現代性的空間想象與建構。
電影《高興》借助初到省城的劉高興、五富的視角,通過縱橫交錯的立交橋、隨處可見的高樓大廈、繁華的街道、擁擠的人群等空間形態的展現,營構了一個遠離鄉村空間、亦遠離縣城空間的具有真正現代性意義的都市空間。然而,“劉高興們的根是連著土的,一旦其脫離土地進入城市,他們將始終處于漂泊流浪、動蕩不定的狀態”[7]。一方面,在市民的歧視、地痞的欺辱、生存的威脅等各種重壓之下,處于都市的五富在心理上、情感上轉而求助于鄉村,以鄉村空間及所處其中的空間感受作為參照來審視處于現代都市空間的尷尬位置,進而引發其強烈的遠離都市、回歸鄉村的特定空間情結。另一方面,現代都市又始終牽拽著他堅持留下來,尤其是對于金錢的病態迷戀,令其無法擺脫都市空間的巨大誘惑。
二、從土地堅守者到進城打工者:個體空間位置的現代轉變
《野山》中的禾禾與桂蘭,盡管對于縣城空間具有強烈的向往與期望,但仍然以土地堅守者的姿態立足于傳統的鄉村空間。他們對于現代性的追求,并非通過個體對既定生存空間的疏離與擺脫,而是通過個體對既定生存空間的改造與變革得以實現。禾禾養過魚,燒過窯,做過豆腐,養過柞蠶和鼯鼠,外出跑過運輸,通過自己的不懈嘗試與努力,最后終于給家鄉通上了電,裝上了電燈,還買來了電磨機,結束了偏僻落后的雞窩洼千百年來世世代代人工磨面的歷史。盡管禾禾、桂蘭對于現代性的追求仍以土地堅守者的姿態為前提,個體的空間環境與生存位置并未發生根本性轉變,但個體的自覺意識與自主行動卻促使其所處的空間環境與生存位置發生了局部的、一定程度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對鄉村空間的現代性營構。因此,其所處的空間環境與生存位置顯然已非之前普遍意義上的既定鄉村的空間環境與生存位置,而是打上了對于現代性的空間想象與審美建構的深刻烙印。
《人生》中的“知識分子高加林才華橫溢卻不得施展”[8],因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而不甘于既定的個人生存位置而向往更為優越的生存位置,以求得更為寬闊的個人發展空間。然而,存在于不同空間之間的一系列諸如戶籍制度、固定工作等的客觀限制,嚴重地阻礙了高加林向現代空間的流動與個人生存位置的轉變。于是,游走于鄉村與縣城之間的高加林,不可避免地陷入由客觀存在的空間限制所導致的兩難境地:既具有強烈的擺脫落后生存空間的束縛而徹底逃離其中的主體意識與堅定信念,又無力沖破橫亙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空間位置轉變的巨大障礙,以及由所處傳統鄉村空間的局限性而導致的難以在思想觀念上突破正統社會身份對自身空間位置的限制。顯然,高加林不再以土地堅守者的姿態試圖通過對鄉村空間的改造與變革,而是試圖通過對既定生存空間的疏離與掙脫和對縣城生存空間的貼近與融入,以縣城“公家人”的正統社會身份實現個體自身生存空間的位置轉變。
《高興》中的劉高興、五富等人,既徹底地拒絕處于傳統鄉村中土地堅守者的空間位置,亦完全地放棄向縣城空間位移以取得正統社會身份“公家人”的空間位置,而是拋卻一切客觀限制直接闖入省城這一現代都市空間。從空間位置而言,他們是城市的邊緣人,始終“處于不鄉也不城的邊緣狀態”[9];從空間感受而言,他們是城市的孤獨者,必然在現代都市空間當中獲得不同于以往的頻遭歧視與侮辱的強烈空間感受。表面上看,他們實現了對傳統鄉村空間的突圍與對個體生存空間的位置轉變;但在本質上,卻因無法徹底地擺脫鄉村空間在其心理上、情感上留下的難以磨滅的印記而難以完全融入都市空間,從而引發個體在都市生存空間當中所處位置的模糊與曖昧,進而導致其始終處于一種尷尬游離于都市空間之外卻又無法回歸鄉村空間的懸浮狀態。
三、從“重組”到“不自主”:由空間位置限定的現代愛情
《野山》中禾禾、桂蘭對城鎮頻繁涉足,逐漸樹立起現代意識,并激發起強烈的對既定生存空間進行改造與變革的愿望;而灰灰、秋絨所處的單一而封閉的鄉村,導致其現代意識的嚴重缺乏,僅僅滿足于既定的鄉村生存空間與生存狀態。禾禾作為禮物送給桂蘭的鏡子是其對日常生活審美化追求的重要表征,在桂蘭的喜愛與灰灰的不屑的鮮明對比之下,充分體現了前者具有與禾禾趨同的對于缺乏審美情趣的鄉村日常家庭生活進行大膽突破的審美訴求。因此,禾禾與桂蘭、灰灰與秋絨之間婚姻關系的重新組合,根源于受空間位置限定的由個體對現代追求的差異、對審美追求的差異所引發的巨大疏離力量。盡管在其婚姻重組的過程中,由雞窩洼的民眾所構成的巨大的空間環境力量起到了不容忽視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根本上仍是由于受到空間位置限定的個體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產生的巨大差異,才最終促成了婚姻的重組。
《人生》中處于鄉村的農民高加林,別無選擇地只能與處于同一空間當中的劉巧珍戀愛;而進入縣城的高加林,在由一個鄉村農民變為一個縣城“公家人”之后,成功地實現了個體生存空間的轉換與位移,進而引發了空間感知的變化:整日沉浸在國際政治、高科技、理想、書籍、詩歌等現代話語氛圍當中的高加林,是決然無法接受劉巧珍關于一只母豬下了多少只豬娃的鄉村空間的特定話語的。于是,獲得正統社會身份的“公家人”高加林對于同一空間當中具有同等社會身份的“公家人”黃亞萍的選擇,便具有必然性。高加林“在劉巧珍出嫁后被城市驅逐”[10],其個體的生存空間又一次發生了轉換與位移,從而失去了能夠與黃亞萍對等相處的空間位置與對等交流的空間資格,“黃亞萍只愛城市戶口的高加林”[11]。盡管對未來婚姻生活的預設充滿了高加林對現代性的空間想象與審美追求,然而,對既定鄉村空間突圍的失敗最終還是限制了他對于愛情的選擇。
《高興》中促使劉高興進城的直接原因,便是受限于空間位置的失敗愛情——戀愛對象嫁給了城里人。表面上看,更為廣闊而開放的現代都市空間賦予個體以更大的生存空間與對愛情的自主選擇權,然而,個體既定的空間位置卻極大地限制了其在這一廣闊生存空間當中的生存范圍與對愛情自主選擇的可能性。處于都市最底層的劉高興,盡管在主觀上對愛情充滿了美好的希冀,但在客觀上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來自現代都市空間的特定因素,包括金錢、地位、身份等的極大限制,而其自身低微的空間位置必然導致其愛情選擇范圍的有限性和對愛情自主選擇權的喪失。因此,由個體有限的生存空間與既定的空間位置所引發的巨大限定力量,決定了劉高興在愛情面前的不自主。“劉、孟二人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浪漫愛情故事,最終把電影推向皆大歡喜的結局……用喜劇歡樂的光輝遮蔽進城農民工以至整個底層民眾艱難的生存圖景。”[12]
總之,從《野山》到《人生》再到《高興》,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條從鄉村到縣城再到省城的向現代性推進的空間敘事軌跡。個體的空間位置也隨之實現了從土地堅守者到試圖獲得正統社會身份的縣城“公家人”,再到完全拋卻正統社會身份的進城打工者的現代轉變,而個體的愛情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所處特定空間位置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