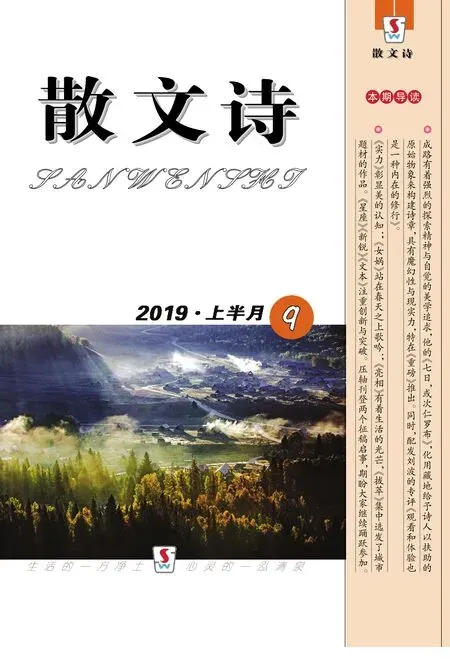于無聲處
山西◎李需
晉祠
晉祠,在三千年的遠方,一泉潺湲。稻黍和夢。遙遠的星光。
一個叫唐叔虞的長者。一手摟定懸甕山,一手摟定迤邐的歲月。
還有,黎民粗獷的喘息。
以禮,以儀,以古樸的風。
以愛,以溫暖,以山脈之起伏的秩序。
讓千年萬代之天下,始有晉。
晉祠之內,周柏蒼翠,唐槐蔥郁,延伸著時間的寥廓。亭臺樓閣,雕龍畫鳳,演繹著歷史的恢宏。
魚沼飛梁,是遠古穿越至現代的見證。圣母仕女,泥彩釉光,跳蕩著創造的光芒。
宋朝的露滴,還在閃爍。
元代的小令,還在彌漫。
宛如一種日久彌新的鋪排,宛如巖層上的燈盞。一邊是儀態萬方的皇家園林,一邊是一衣帶水的田園風光。
黃河撫琴,素絹拂袖。
太行舞墨,氤氳渺渺。
晉祠,在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如三晉文化之沸點。
用一種騰挪、跳蕩的優雅,入云,入霄漢。
抑或,只是用一種沉默和簡約,靜水流深,花紅柳綠。
平遙古城
高聳的城墻,如同王朝的屏障。無論是隸屬于晉于趙,還是秦漢與明清。更迭和轉換,都無法阻礙它的波瀾和壯闊。
土字型的街衢,平放著是民心,立起來也是民心。
票號、商鋪、鏢局、客棧,以及“日升昌”的榮耀,匯通天下。
歷史最濃墨重彩的就是:民強則國強,邦興則國定。
我在平遙古城彳亍。
一座距今已六百年的平遙衙門,以一種“公生明、廉生威”的氣度,深深感染著我。
一座文廟,仍然是殿宇軒昂,仿佛一座文化的山峰。
“霞疊樓”“棲月樓”“瑞靄樓”“凝秀樓”,如同一種詩意的標識,依然在時間的隧道里閃爍,綻放光彩。
我在平遙古城溯源,追尋晉商崛起的奧秘。
我透過歷史的間隙,依稀看到的是一種包容。
兼山河,兼家國,兼天下。
或者,是一種氛圍。王朝的氛圍。文化的氛圍。歷史的氛圍。
還有,此起彼伏的民俗:旱船、高蹺、龍燈、竹馬、地秧歌。
歷史有許許多多的原型。在平遙古城,它最直接的原型就是,農耕文明日益勃發之后的那一絲絲萌動,和最后的爆發。
貨與幣的流淌和聚齊。
走西口的小調,闖關東的豪邁。
最終都不只是讓我們來還原一種久遠的自豪,而是要讓我們用歲月隧道里的光環,繼續砥礪前行,發揚光大。
云岡石窟
一種文化的興起,總有它的理由。佛文化,亦如此。
云岡石窟,裹歷史之長風,依武周山之勁健。至北魏,歷數朝風云,一路飄逸,彪炳青史。
何故?
何由?
沿著歷史的脈絡,以一種頂禮膜拜的虔誠,我在45個洞窟中,或仰望,或凝視;我在51000尊石雕下,或感嘆,或追索。
我在尋一種交織的文化源起。
而此時,時間卻如同一只巨大的篩子。它到底會向我過濾些什么?
皇權和江山。慈悲和信奉。佛法和民心。藝術和智慧。甚或是長河落日,落日渾圓,蒼山碧翠,大漠如煙。
還有——平等、因果、輪回。眾生、因緣、靈魂。
遠處的目光,近處的色彩。
路與橋。
我信奉,一種文化的長久不衰。那是因為任何的一種肅穆和莊重,都有著它既接近現實的熟悉又深藏內斂的陌生,讓我們靠近,卻又無法參透。
我信奉,一語成讖。我更信奉,人性的荒唐,人性的善良,人性的泯和滅,人性的返璞歸真。
悟性與道。
在一條河流里,翻卷著浪花。
感念像時間深處的花朵,點綴來時的路程。一半是盛開,一半是凋謝和無奈。
其實,在云岡石窟,歷史就是一柄旋轉著日月的鏡子。
一面照著的是佛光無限,大愛無邊;一面照著的是栩栩如生的藝術再造的真實和虛渺;
一面照著的是朝代變遷,歷史的深邃;一面照著的是山河依舊的奧妙和久遠。
一面照著的是佛文化的深厚和磅礴;一面照著的是草葉上滾動的露珠,來世和今生。
司馬光墓
鳴條岡上,涑水河畔。有風之蕭瑟兮,有雁之鳴啾兮。
我想用觸摸,再次感知一個少年婦孺皆知的故事。
或者,再次感知大宋王朝一位官員、一位史學家睿智的目光。
而在我的面前,卻只有:塋地、碑樓、碑亭,還有一座靜穆的余慶禪寺。
這些,仿佛還都在敘說著一些久遠的陳年往事。
雖然,在我剛一踏進司馬光墓地,它所映現給我的確實有幾分衰敗和蒼涼。但是,我還是不自覺地正了正自己的衣冠。
因為,對于這位彪炳史冊的先祖,我依然感到一種巨大的光環,在環繞著我,包圍著我。
因為,對于一位古代的高官,他本身所具有的那種文化的光芒,的確至今還讓人深思和欽羨。
更因為,只有最賢達的官員,才是天下之幸、黎民之福!
司馬光墓,就歷史而言,它和許許多多的古陵墓一樣,已然早就成為一種時間的記憶。
但是,時間的亙久,并沒有磨滅它無與倫比的偉大。
一部《資治通鑒》,如同人類歷史天空的一道虹翼,既照著朝代的更迭,也照著人類歷史的興盛和衰敗。
歷史不會重寫。但歷史往往最能夠與更遠的歷史達成一種最后的默契。
——此時,我依然站在那條叫鳴條岡的丘陵上。
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時間的邈闊,歷史的恢宏,文化的偉岸。
而一部煌煌史冊,至今,還仍在被無數的人翻著、翻著——
翻出生命的風聲。
翻出黃河一瀉千里的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