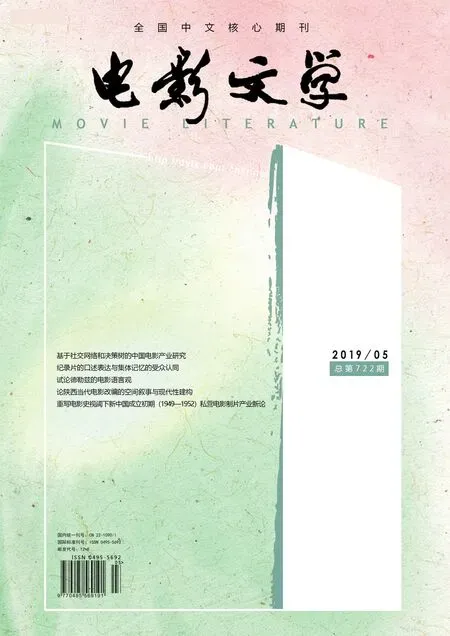張藝謀《影》中的“墨色文化”
李 萍 楊柏嶺(安徽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電影《影》將墨色從頭至尾地貫徹使用,使得影片呈現出極致的東方美學意味。墨色承擔著《影》中視覺元素符號的外顯和隱喻功能,又因其本身系統包含著與中國文化的深層聯系,其在《影》中的主導性結構運用就變得饒有趣味。作為中國傳統色彩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墨色所展示出來的色感和學理內涵,都印刻出區別于西方的本土文化審美特征。在西方,“酷似原物”為色彩最早的理論標準。古希臘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說過“繪畫混合白色與黑色、黃色與紅色的顏料,描繪出酷似原形原物的形象”。[1]而約在我國同時期,色彩就已開始結合“禮”的規范,從“玄”的理論闡釋。至唐朝中后期,又趨向表現社會“心”理。東西色彩觀念的形成完全分處于兩個不同的文化起點,思維本源的差異也是各自藝術向寫實主義和寫意風格兩條道路發展的成因之一。黑色是古代中國的眾長之色,長久的黑色崇拜歷史挖掘出了墨色藝術,且將黑與白并于墨之中。墨色以墨為材料,溶于清水后大致分化出焦、濃、重、淡、清五色。運墨者不再隨類賦彩、以色貌色,而是利用墨的獨特色征將自己的內在情思進行外在意化。唐人張彥遠曾述:“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而亡,神工獨運……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2]可以說,“運墨而五色具”的墨色哲學蘊含著中國源遠流長的認知理論圖式,是中國古典色彩美學的典型要素。導演張藝謀高度強化墨色的形式感于《影》的色調運用,舍棄了高純度顏色象征,用黑、灰、白的低飽和度色相勾畫出乾坤萬物,在黑、白的對立統一中訴說著真身與替身、虛與實、善與惡的陰陽變化交織。
一、墨色于“禮”:《影》之人物身份敘事
影片故事的最初原型來源于《三國》,但《影》架空了時代文化背景。講述的是替身境州作為大都督子虞的影子,在真身受傷后替其行走朝堂戰場,陷入貴族權謀游戲的種種命運掙扎。影片塑造的整體水墨畫風剝離了三國時期的歷史感,又以墨中黑、白兩色的精巧設計嚴明了虛構場景里的真實性。儒學中,色彩按“禮”的標準被劃分等級,《禮記·玉藻》卷二十九“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3]張藝謀把古人以色明“禮”的傳統根植于《影》的敘事之中,用黑、白色間的對比暗示來表現君民、夫婦、文臣武將的掣肘倫理地位關系。
《影》中有一個境州服飾由“黑”轉“白”的情節處理:以假亂真的境州在朝堂上要辭去自己假扮的都督之職,則被主公宣告革去職位爵俸,收繳劍印,降為白身。境州便被脫去一身黑衣,只剩白服。《日知錄》記載“白衣條”稱“白衣”為“庶民之服”,故平民謂之“白民”。通過服飾色彩的更替,從“禮”的角度符合角色身份變化,形成兩組合“禮”等級的色彩關系對照:假扮子虞的境州自身的社會地位對照,著焦墨濃黑之服的重臣與被貶之后一身素白樸衣的平民之間的君民之“禮”;境州與主公的社會地位對照:穿一身正黑長袍的主公與無權無勢的白衣境州之間的君民之“禮”。“以黑為上”的色彩觀念存于中華幾千年之久,《韓非子·十過》記載“作為食器,斬山而材之,削鉅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為食器……舜禪天下而傳之禹,禹作為祭器,墨涂其外朱畫其內”。[4]《禮記·檀弓》又謂“夏后氏尚黑”。至秦統一,“易服色和旗色為黑”。(《史記·封禪書》)在子虞、境州出現的同一畫面中亦有“尚黑”意識顯現。身受重傷的子虞形象枯槁嶙峋、披頭散發,手持竹棍與境州在被困的斗室間研習破解楊蒼刀法,雖衣著簡陋襤褸卻用重墨潑于其服飾之上。對戰的影子境州發鬢整潔、身姿卓越颯爽,但著的卻是無墨白衣。兩人體形氣力裝扮明眼懸殊,而黑白的服飾色彩比較依然能規制出子虞與境州之間的君民等級差異。除君臣關系之外,夫妻間的等級關系在《影》中服飾也依古制尊“禮”施色。“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禮緯·含文嘉》)小艾作為“婦”的女性形象,衣裳多偏白,雖有些許墨彩點綴其上但大體不會色暗于真假兩位“夫君”之衣冠。在影片的開頭和高潮,小艾與境州、子虞分有琴瑟和鳴。平靜的都督府內,小艾、境州盤坐在榻前左、右兩側,衣色一淺一深、一白一黑將畫面均勻分割。境州彈正調、緊五弦、穿墨色都顯示出其作為“夫”重于“婦”的地位。小艾與子虞琴音廝殺部分則采用正反鏡頭快速切換,小艾依舊著白裳清墨,子虞身附重黑,在合乎夫婦之“禮”的身份安排下進行博弈較量,白與黑在反復的鏡頭變換中也渲染了對抗的氛圍,色彩視覺與高漲的琴瑟之音共制出情節的高度緊張感。黑、白色彩的人物身份敘事不僅在個體間彰顯,“文”“武”之別也可暗含。影片中從黑白色彩“禮”制運用的細節巧妙展露了故事內容“以武為主”,交代出“武大于文”的時代文化構建。《周禮》中對王及公、侯、子男、卿、大夫之服都有明確的規定。至朝議政,要著正服皂衣,即是黑色的朝服。影片中文臣、武將于朝堂之上分列兩側均黑冠墨服,以示“禮”制。而細微之下,武將服色墨重于文官,文臣上衣潑淡墨暈染色階較低,黑、白色感的清晰強弱又透露著文臣武將的朝中地位高低。
張藝謀把黑、白色彩不顧于物理而追蹤人理的中國人文精神內涵融于電影,編織一個符合邏輯存在的封建等級世界。黑、白能夠去顯示職秩、貴賤是其色感可以超越對物質自然色的仿真復現,是人的觀念意志所恰合投射的對象,所以黑、白兩色被賦予地位等級的象征是導演結合了中國人主觀民族色彩概念的運用,并會知“禮”就是色彩這種人為意識的思想指導。《影》將黑、白色帶來的“禮”在畫面中進行微妙處理,用墨色本身帶“禮”的豐富意味去抽象表達影片的內容關系,更好地延長了影片的審美效果。
二、墨色于“玄”:《影》之審美藝術創作
《影》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表現技法都滲透著“玄”的思想,“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觀點被導演或深或淺、或有意或無意地融入電影當中。視覺畫面水墨色感清淡,故事內容悲愴濃烈,一“淡”一“濃”的相對相合可謂是太極分陰陽、陰陽合太極。張藝謀曾表達過,影子境州作為一個平民孤兒想要在殘酷的貴族斗爭中合理存活下來,就必須被設計成一個非常濃烈、連續翻盤的故事。在情感如此之濃的戲劇核心下,選擇“淡”的水墨作為表現色彩,用“淡”“濃”拉開天地,就成了中國人說的“文武之道”“陰陽之道”。[5]太極陰陽觀對中國藝術影響深遠,《影》中墨色的運用無論從大的格局設定還是具象的元素設計都有著兩極歸一的“玄”味古典藝術追求。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的太極圖是“玄”之意象的集聚符號。太極圖以S形線條分出黑白、陰陽兩面,在“易”學中,陽為白,陰為黑,將極具“陰陽之辯”的太極意象參與到《影》的創作之中,對其主題、情節轉為抽象化處理,是契“玄”之妙法。影片伊始,小艾與青萍在大殿之內用太極圖盤占卦,“這卦至陽至剛……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這一卦是乾”。此時卦象落在太極圖的陰面,且偏向整個大殿的西方。五色、五行、五方相應,黑、白按五行之源分屬水和金,是北、西兩方之色。白色與方位親緣相合,又因“乾”在《易經》中為陽卦且是“天”,從小艾算出的卦象便得知影片主線是男人們對統天之權的爭奪。在影子境州與楊蒼對戰的畫面中,太極仍被設置成為重要的隱喻符號。兩人各站陰陽一方,境州站于黑色,利用陰柔綿長的武器沛傘,以柔克剛得以抵抗住楊蒼的剛烈刀法。太極圖黑白兩儀的站位已經預示了境州可能獲勝的反轉結果。玄之又玄的太極圖將導演不便言說、難以言說的想法假以黑、白兩極同構思辯的暗示予以微妙表達,通過畫面典型陰陽符號的體證將自己的創作意圖潛移于觀眾。
《影》中極簡克制的水墨色彩仿佛讓影片彌散在氤氳的“玄”界之內。黑、白色征附陰、陽二元思想,孕有“玄”理。而水墨色感的“樸”“素”又為影片籠罩上“玄”感。狹小黑暗的朝堂之外是水墨渲染般的煙云山水畫卷,極具玄妙古樸之意。陰雨增添了明凈搖落、昏霾翳塞的秋冬山水空蒙之感。墨色雖只有黑、白兩色色調卻內在蘊含層層流動變化。影片廟堂之外虛實結合的山水景象構建就是利用了墨趣的巧變。畫面中的云、氣、煙、霧、嵐、靄等虛景用淡墨清墨處理,焦墨表現山的倒影,濃墨顯實山,“取其繁章,采其大要”地在虛實空間結構上用重墨突出湖面小船,聚焦整幅影像的審美中心。在樸素的黑白色調之下抽離物質本來的色彩限制,以墨的復雜暈染誘發畫面生出虛、無、靜、默、寂的玄妙之感。與此相似意境營造的水墨畫景貫穿全片,在影子境州戰后余生逃返于家的路途之中,出現近景濃墨的松樹石橋與清墨的遠山山霧之間虛實呼應的畫面,騎馬的境州成為自然景中的一點焦墨。墨色雖表面上看似消色之論,實則是讓謬心之色“不蕩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莊子·庚桑楚》)[6]張藝謀將這“絢爛之極歸于淡”的中國古典色彩規律從文人畫中提取,落實到電影屏幕上來,為中華民族文化執守不變的墨色追求增添了新的時代表現形式。墨色在影像中的連軸動態呈現所產生出的審美意境,能夠使得“玄”感持續更迭于受眾的審美心理過程。
相比于紙質媒介的文人畫,電影銀幕更能讓墨之氣韻直接刺激于審美者的視覺敏感。《影》的墨色呈像手段是在前期的拍攝過程中對物象色彩選擇控制,影片中出現的所有服裝、場景、道具等都盡可能實行實體黑白化。服裝設計陳正敏說,他們差不多做了近千張的水拓畫,用來作為服裝上面的一些肌理和文案的一些圖形。為了營造江南雨天的氛圍,影片中的實拍戲份也幾乎都是在真正的陰雨天氣里完成。前期物理上直接嚴格控制色彩后,后期再用電腦把畫面中的其他多余顏色進行褪色處理,調好影調,轉為黑白,有些畫面中的高光和暗部加一定黃、青色,有些則可以直接轉換灰度再調整畫面中的各個單一色彩明度。通過影像制作科技的再加工使墨色的暈染層次基本不失本真地展現出其“玄”妙。導演精心雕琢全片的每一個水墨細節質感,將“運墨而五色具”的古典藝術精神注入現代的電影藝術創作中。導演自身的藝術色彩追求和民族傳統文化的強大馭控力,使《影》伴隨著相玄相通的水墨色調出現。
三、墨色于“心”:《影》之復雜人性思考
《影》用黑白冷色調打造出了陰冷灰蒙的空間,朝堂之上偌大的白色屏風層層間隔,壓抑的氣息來自朝野人心的冷酷。導演張藝謀用低調的水墨色彩來表現就奠定了影片講述故事的基本調性是冷感的,也側面表述了影片虛構社會的黑暗無光。帶有悲涼色彩藝術情節的創作背后隱藏的是導演的悲憫之心,“以黑白為象”的水墨藝術是色與心的同質趨向選擇。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張藝謀曾說過:“替身這個職業的命運吸引著我,他們是很獨特的,關注他們的命運,探討他們的人性部分,是我創作的沖動。”境州在水墨殺場中的漫長等待和蟄伏,也是導演對自身心路歷程的思維投射。“有用是我們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價值觀”,替身是“有用”的,如同“工具”。張藝謀在工廠學習攝影期間,就常感到自己是“工具”,境州其實也是張藝謀自身的影子。水墨這種用色的壓制感與影子境州內心長久的克制呼應,也是導演早年間壓抑心情的代入。心境與色彩的相通是張藝謀在創作電影《影》時自我沉浸式的內外結合,心與色是藝術表現的內與外。
在《影》的水墨色感構建起的極簡古意之下,暗涌著的是真真假假的復雜人心斗爭。境州是子虞的影子,真身從來忌諱莫深,影子在主公和都督的權術爭奪中苦苦求生,最后反殺真身。主公不是淫亂懦弱的主公,而是運籌帷幄的陰險君主。子虞也不是忠心耿耿的子虞,是癡迷權術的狠辣重臣。境州更不是一味隱忍的境州,是個人意識不斷覺醒的王者。故事人物悄然變化的微妙心理:恐懼與僥幸、幸福與不安、暢快與追悔都深厚幽遠地像墨色渲染一樣道不清、說不明。墨溶于清水呈五色變化,墨線起伏又有剛、柔、曲、直、輕、重、長,墨就如百般人心虛虛實實、難以捉摸。黑白兩色二極對立,黑完全吸收光線,白完全反射光線,兩者至陰至陽,但墨色的樣貌精妙多變,從不只是單純的非黑即白。人性有惡有善,也絕不只是非善即惡,而是善惡交織、黑白交融。善、惡之法用黑白以喻在佛經中多見,《俱舍論》卷十六將業果報應分為四種:“惡所引起的果報,曰‘黑’或者‘黑黑業’;善所引起的果報,曰‘白’,或曰‘白白業’;業與報善惡相混,曰‘黑白業’。”[7]沛王工于心計、籌謀布局地想要除去心中所惡的子虞,此為人心之“黑”。但對相依為命的妹妹青萍卻寵愛有加,當青萍失去性命,沛王對天怒吼、追悔莫及,這又是人心之“白”。境州一心想要回到自己老母親的身邊,從戰場僥幸存活后立即奔赴回鄉尋找母親。這也是人心的“白”。但發現母親被殺自己又被刺客奪命,境州決心回歸朝堂反殺成“王”,逼出人性中的“惡”,此又為人心之“黑”。影片中所有的善惡、黑白、真假卻又都仿佛淌于墨色的流變中與之渾然為一體,靜息在詩意的水墨之境。
電影《影》將這種水墨色與復雜人性主題結合的影像呈現方式,受到了一些不同的見解。王一川先生就曾發文“假如單看這些中式水墨構圖和景觀布置,可能會以為影片講述古代士人淡泊明志的歸隱山林故事,或古代俠士的‘劍氣動徹九重天’之類義薄云天的英雄傳奇。然而出人意料地,編導所孜孜以求的卻是其中充滿血腥味的權力轉換故事。這多少有點美學上的‘擰巴’味道”。[8]“水墨”之路自中唐以來風行一千數百年,擇墨而作經久不衰,水墨色彩以往給人帶來的傳統中式故事想象也的確是“淡泊明志”“義薄云天”,這是古人結合自身所處的時代特征對應墨色整體低調色感帶來的現實對象聯想。但就墨色本身的色彩性格特性而言,水墨形式的風格和所表現的人性復雜游戲之間的意義構造還是具有相互匹配的現代要素。當下觀眾的審美沉淀著對于暴力形式感的欲求,殺戮、血腥、人性的罪惡痛苦等都有著很大的電影市場價值。張藝謀的影片又通常集聚著強烈的生命感,當生命的制高點投擲在武俠江湖就必然不能從戲劇構造上“歸隱山林”,把江湖的詩意部分通過墨色的色彩形式表達,也不失為一種當代策略。
像《影》這樣使用水墨色彩的大制作院線電影是首次出現的。水墨樣式罩于影片之上,水墨元素嵌于影片之中,水墨文化融于影片之下,電影從視覺、內容至思想都由內而外地發揮了墨色元素的敘事、審美、思考力量,是一次電影色彩美學的創新和拓延。墨色蘊含的中國文化思想和其極致的審美視覺感受,對中國電影創作中民族性格的塑造有著重要意義。如何挖掘墨色的內在潛力,將之與電影的現代表達手法結合,并做出彰顯中國美學的世界影片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墨色這樣具有典型中國意象的色彩藝術應該在電影當中全面綻放它的異彩,讓中國的傳統藝術元素在電影行業中煥發生機,找到真正體現中國味道的電影創作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