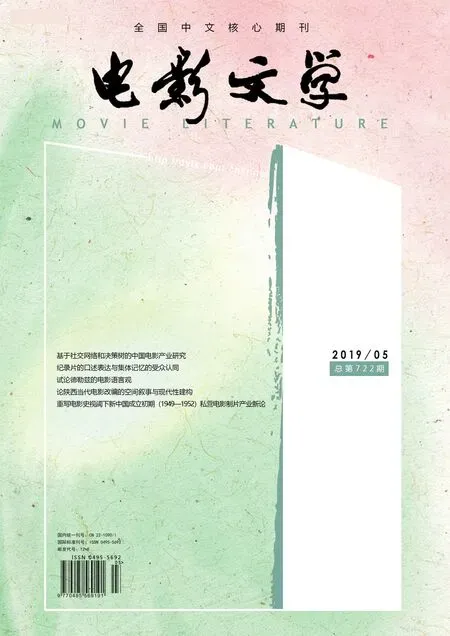“前任”系列電影的性別文化研究
張 強(北京電影學院,北京 100088)
處于快速變革中的社會,人們的戀愛觀念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城市化進程打破了性別關系的穩定性,每個人都可能有多段戀愛經歷,曾經相伴相隨的人在某一節點就會變成“前任”,而人們也在不斷尋求處理這種關系的方式。“前任”系列電影一共有三部,包括:《前任攻略》《前任2:備胎反擊戰》《前任3:再見前任》。這三部電影在上映時都獲得了不錯的票房,有必要使我們重新審視“前任”所體現的文化內涵。當我們以“性別文化”的角度切入,很明顯地能夠感受到它給我們帶來的文化體驗同以往的中國電影有明顯的區別。
“前任”系列電影的出現既是當代人們生活的折射,也是觀眾對自身戀愛經歷的想象性滿足。從《前任攻略》到《前任3:再見前任》,孟云和余飛不斷處理著前任給自己帶來的種種困擾,愛與仇恨、寬恕、報復等相互交織,影片用喜劇化的方式處理現代都市的情感危機,延宕了“分”與“合”的中間狀態,給予觀眾前婚姻狀態下的兩性交往體驗。“前任”系列電影所指向的是中產階級的情感困境,他們已然從物質消費過渡到了精神消費階段,情感變成一種奢侈品和易耗品:持久的感情變得越來越困難。我們看到了新的兩性關系的形成和審美體驗的變遷,對傳統銀幕的性別敘述形成了挑戰。本文試圖探討“前任”系列電影體現的現代都市文化內涵,并分析影片如何將性別文化包裝成大眾文化需求。
一、性別關系:從個人到社會
三部電影中都有一個明顯的設定:男人和女人在處理前任問題時采用不同的方式。這樣的話題本身就吸引年輕觀眾,他們希望在銀幕上看到與自身貼切的生活,一方面回味自己過去的美好和痛苦,另一方面在喜劇化的處理中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三部“前任”系列電影盡管都有以男性作為敘述主體的嫌疑,但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品,而是具有“愛”與“不愛”的權利,可以選擇“去道德化”的方式建立一種新秩序——與男性對抗的秩序。這與以往的性別關系有很大不同,“男性統治將女人變成象征客體,其存在(esse)是一種被感知的存在(percipi),所以男性統治的作用是將女人置于一種永久的身體不安全狀態”[1]。女性因為男性的存在才顯得有價值,成為男性的想象性主體,即使像《紅色娘子軍》這樣標榜女性覺醒的電影中,吳瓊花依然要靠著洪常青所代表的男性力量才能完成主體建構。顯然,“前任”系列電影中的女性和傳統女性有了很大區別,是具有現代都市身體特征的女性。
從《前任攻略》開始,感情生活中的性別對抗就開始出現,孟云和夏露在面對自己的前任時都流露了懷念和感恩之情,卻對對方的前任采取各種策略,使原本穩定的感情出現了裂縫。在《前任2:備胎反擊戰》中,節目編導伊澤和明星余飛發生一夜情之后,認為他們之間已經具備了戀人關系,便迅速陷入了對余飛的愛戀之中。但在余飛看來,一夜情并不能說明雙方具備了正式的戀愛關系。伊澤改變了自己的形象,使自己更具備都市女性的氣質,經過一番波折,重新贏得了余飛的心。伊澤所做的事正是從“備胎”到正式戀人的轉換,去贏得起初對自己并不在乎的余飛。從這兩部的作品中明顯可以看出戀愛中的女性不再是“單純”“不成熟”“傻乎乎”的形象,而是掌握了一套在戀愛過程中對抗前任或者贏得愛情的技巧,雙方的結合是去“物質化”和“世俗化”的,他們之間的聯系在于異性之間的情感因素。到了《前任3:再見前任》那里,男性與女性的對抗則成為敘事的主體,他們所在意的是在矛盾產生后到底誰應該主動認錯。三部電影都打著“前任”的標簽,呈現的是感情異化的狀態,雙方都在不停地處理問題、解決危機,愛情的美好多數是被回憶出來的。
痛苦的延宕指向的是都市生活的焦慮。該系列既不是才子佳人式的愛情片套路,也不是苦求愛情終獲成功的模式,而是對準了都市中大多數年輕人面臨的愛情困境:如何對待前任。前任的敘事價值在于他/她存在許多個人記憶,而這種記憶在當下是無法延續的,因為雙方已不具備傳統的愛情關系。用情感受虐作為敘事內核,比起轟轟烈烈的愛情,最能直接刺痛觀眾的內心,這在今天的中國電影中很少被表現。孟云和余飛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酒吧和KTV,也只有在這種場所才能擺脫令人苦惱的感情問題,宣泄著自身痛苦的情感體驗。有趣的一點是,《前任3:再見前任》中孟云和林佳的感情狀態屬于“一個以為不會走,一個以為會挽留”,余飛和丁點則屬于“借著吵架的殼撒著思念的嬌”。當他們的關系變得十分微妙的時候,孟云和余飛雇人用微信社交的方式檢驗林佳和丁點的情感狀態,而林佳和丁點也在用微信朋友圈觀察孟云和余飛的獨身生活。這種感情的不確定因素使得觀眾獲得都市生活的焦慮感和恐懼感,以至于最后孟云扮演至尊寶在街上旁若無人地大喊“林佳,我愛你”,林佳邊哭邊吃使自己過敏的芒果,喚起觀眾的情感認同。
兩性關系敏感地反映了當代社會變遷的深度,電影中也在表現新的愛情倫理觀。盡管我們在“前任”系列中看到兩性斗爭,但是他們無一例外都在小心翼翼地處理愛情關系。面對各種可能的都市生活,男性處在戀愛狀態時都是忠貞不貳的形象,從不會做出越軌的行為。片中雖然以表現愛情關系為主,但是從事業的角度來看,不論是公司老板、職員,還是演員的形象,他們都能保持責任與擔當的精神。所以,我們在“前任”系列電影里同時也看到了一種“都市男性”的塑造,他們接近現代社會的男性想象:有自己的事業、形象氣質佳、對伴侶忠誠。一方面,這種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是對等的,強調平等化、消除符號等級、遮蔽歷史感,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完成審美呈現;另一方面,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已經發生了混淆,不再視作生理性別的附屬。與其說影片中建立了一種性別關系,倒不如說塑造了一個社會結構的切面。“我們意識到社會性別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自然決定的,那我們也必然意識到它不是由性別決定的。在最簡單的層面上,這意味著承認男性和女性都有‘男性氣質’(masculine)和‘女性氣質’(feminine),或者說‘男性氣質’和‘男性’(male)的含義有區別。”[2]現代都市演繹著一種和諧的男女關系,在社會分工上消弭傳統工農業建立的性別秩序。男性為了表示對女性的尊重和女性氣質的重要性,開始建立具有女性氣質的男性身份;而女性在試圖證明自己作為“社會人”的意義,也在背負著同男性一樣的精神壓力。
有趣的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了一種建立在都市空間上的性別文化圖景。生活在現代都市的人面臨著不同的身份認同焦慮,要么是“異鄉人”,要么是不斷融入“異鄉人”中的人,前者則是大多數。這些遠離家鄉、離開父母來到大都市生活的“異鄉人”需要用新的生活方式標志自身,以彰顯主體意識,同時也意味著對傳統倫理價值觀的剝離。使用各種各樣的社交平臺,可以讓都市年輕人迅速聚合,脫離單身狀態找到新伴侶并不困難。同樣值得反思的是,“前任”系列電影所塑造的人物或是都市中的一群人,既無法代表都市的全部,也無法與非都市文化建立共通性。更準確地說,該系列是“新圣堂”所代表的80后創作群體的都市想象。
二、女性身體與婚戀觀
“前任”系列電影中的女性形象更貼近都市生活的審美需求,新的銀幕女性在近些年的演變中漸趨成熟,所展示的身體特征更為現代。當我們已經熟知中產階級不再局限于滿足物質需求的時候,更感興趣的是他們能夠創造出怎樣的審美空間,以符合社會的消費需求。無疑,我們看到了女性力量的崛起,具備了和男性較量的沖動和能力。影片中,一直深愛著孟云的羅茜在訂婚宴上竟然不顧未婚夫在場勇敢地向孟云吐露真心,導致孟云與現任女友分手;伊澤面對發生一夜情又隨即對自己不感興趣的余飛,通過改穿包臀裙、改變發型、健身美體等外表的重塑后立即征服了他,并讓余飛愛得死心塌地;林佳在與孟云鬧矛盾的時候,即使面對徹底分手的代價也不愿意主動和孟云和好。傳統銀幕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位置有了很大改變。
女性身體從米歇爾·福科所描述的“權力的身體”走向消費文化中的身體,更突出的是自由和欲望的暗合。銀幕中的女性展現的是其符號價值,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觀念的載體和象征,切合了人們對銀幕新女性的心理召喚。“在消費文化中,人們宣稱身體是快樂的載體:它悅人心意又充滿欲望,真真切切的身體越是接近年輕、健康、美麗、結實的理想化形象,它就越具有交換價值。消費文化允許毫無羞恥地表現身體。”[3]當伊澤重塑身體(發型、衣著、姿態)的時候,就和商場櫥窗展示的琳瑯滿目的商品沒什么兩樣。在電影中,她贏得的是余飛的愛情,而對于觀眾則是具有新鮮感的可消費的文化符號。“文化中身體的自我意識被過度地導向于如何將身體容貌修飾得符合固定的社會標準,又如何按照這些模式把身體修飾得更加吸引人。”[4]電影中以這樣的方式展現了真正的女性氣質,滿足觀眾對女性氣質的想象,也是以這樣的方式完成兩性關系中權力地位的轉換:男性(余飛)成為可供擺布的對象。伊澤與余飛發生一夜情后,伊澤乖巧地為余飛準備了豐富的早餐,而到影片最后,變成了余飛乖巧地為伊澤做早餐,完成了角色互換。更為有趣的是,因為在情感關系中占有了主動權,從而導致了伊澤工作地位的上升(從副導演到導演)。銀幕中的當代女性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變兩性關系的從屬關系,也有能力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對年輕女性觀眾和女性主義者同樣具有誘惑力。作為外表的身體,是通過化妝、美容、健身、著裝等一系列方式來實現,而作為當代社會實踐的身體,則是通過思想的獨立、自由的戀愛、閑適的生活、出入娛樂場所(酒吧、KTV等)來建構一種能夠進入較高精神層次和生活狀態的女性。
《文匯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表述新世紀的婚姻關系:“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開放,那種‘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婚姻家庭觀念,受到了人們的摒棄,城市男女正在探尋一種或多種互相恩愛、平等相待、沒有強迫、沒有過多束縛的兩性組合方式。”[5]大多數城市女性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不錯的經濟能力,讓她們更加注重生活的質量,傳統的婚戀模式對她們的吸引力在降低。《前任攻略》中,夏露和孟云經歷眾多前任的騷擾,最終還是結婚了,但卻因為孟云在羅茜的訂婚宴上坦言內心的感情,導致兩位癡男怨女還是互相變為前任。對于羅茜而言,她是在自己的訂婚宴上對傾慕已久的孟云表達愛意,這本身就是一個現代社會的悖論,誠如她所說,“趙明,謝謝你對我的好,我愿意嫁給你。但是,我最愛的人不是你”。婚姻和愛情沒有必然的聯系,婚姻只是社會權力機制的運作方式,不是心理和生理的自然屬性決定的,期待著用婚姻來維系愛情的時代已經過去,無法兌現“結了婚就能獲得永久的愛情”。“要驗證是否真愛的最好方法就是分開,分開后如果痛苦并思念就是真愛,真愛一定會讓兩個人相遇”,這是當下愛情觀最好的寫照。某種意義上來說,“前任”系列電影的女性身體和婚戀觀隨著時代和社會的改變而呈現出新的特征,她們是傳統社會的離經叛道者,是男權社會價值標準的顛覆者,同時也是銀幕新女性的開端。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丁點的同事有一個愛談戀愛并多次結婚的母親,大家聽聞后對此只是淡然一笑。
這種婚戀模式主要體現在“去道德化”傾向以及傳統家庭的不可見。“婚姻問題”在“前任”系列電影中雖不是重點表現對象,但我們依然能夠發現被遮蔽的社會文化內涵。用婚姻來束縛具有現代意識的男女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意義的。中產階級的戀愛觀使得男女雙方在擇偶中的自主性越來越強,要求越來越挑剔,因為他們具備了經濟獨立的能力,不再為物質生活而擔憂。“在處于不利地位的階層中,婚姻成了——超越了可以讓它變得重要的各種經濟原因——一種關系形式,它的價值就在于建立和維護了強有力的個人關系,包括共享生活、互相幫助和道德支持。”[6]如今,男女雙方之間的依賴關系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弱,單身生活對他們來說并不是一個值得在乎的事情。《前任攻略》中孟云有句臺詞,“那天老趙跟我說,他們那代人覺得東西壞了是可以修的,而對于我們來說,東西壞了就應該換,這就是老趙眼中的我們這一輩人”。這種觀念在今天不具備批判的可能性,很難說它違背了某種倫理觀,因為它來自現實生活的映射。分手、離婚無須背負沉重的精神負擔,而被看作是一種解脫,也是一種幸福,其本質是現代性身體去權力化的結果。
從身體的去深度化到當代婚戀觀的價值宣告了銀幕性別姿態的凸顯,將傳統電影的宏大命題消解在現代都市的文化消費之中。身體與婚姻的解放,既體現了個體對社會規訓的反抗,同時人們在對控制其他事物無能為力的時候,至少還可以塑造我們的身體,與個人價值聯系在一起。利用現代的生存經驗,表述當代生活某種暗藏的文化符號,熱衷于對社會慣例的破壞,“前任”系列電影以此完成了對當代身體的銀幕塑造。
三、性文化的消費
關于性的解釋,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認為性的本質是由社會建構起來的,可以表現為多種多樣的文化形式和意義。“性是歷史和文化的變量。在人類生活領域中,同許多其他行為相比,性是最受社會文化影響的一種行為。社會建構主義將性視為可塑性(malleable,plastic,mouldable)很強的東西。”[7]這就把性和人類的繁殖行為做了區分,兩性之間的相互吸引并非僅僅是出于繁衍后代的沖動。人類關于性的實踐、欲望不是自然而然的生理本質,而是依據現存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改變。因為性來自社會的建構,社會也在不斷地改變,就不存在規范化、合理化的性,但我們可以通過差異發現其中的含義。當性作為一種銀幕實踐的時候,也契合了當下社會的某種價值指向。
性不再具備儀式感,而是一種開放的、消費的文化。電影《紅高粱》中“野合”場景用的大全景俯拍鏡頭,余占鰲跪在“我奶奶”的腳下,鼓聲和嗩吶聲的響起使性的實踐更加莊重神秘。“野合”是一種儀式,是對性的解放與贊揚,是對傳統觀念的一次反叛實踐。如今,性已經喪失了它宏大的命題,更像是一種快餐式、可被消費的文化。當人們感受不到性行為的道德障礙時,就會習慣性地把性和愛區分開來,僅用于滿足本能的沖動。《前任攻略》孟云和夏露第一次在婚禮上認識就開始了同居生活,《前任2》中余飛和伊澤也是在劇組首次見面后便發生了一夜情,《前任3》余飛和丁點雖然分手,但還是借著各種方式曖昧不清。對于他們而言,從兩人相互認識到一夜情或同居都在一天之內發生,以往戀愛關系中相互結識了解的漫長過程被省略,直接開始“婚姻”式的生活方式。這對于劇中人物以及觀眾都是可以接受的方式,并不認為有什么不妥。這種對兩性關系的玩味體現的恰恰是后現代文化的繁衍與滋生。“后現代主義反對美學對生活的證明,結果便是它對本能的完全依賴。對它來說,只有沖動和樂趣才是真實的和肯定的生活,其余無非是精神病和死亡。”[8]它不再需要觀眾對含義模糊的意象進行破譯和理解,而是直接地表現本能的欲望快感,滿足的是無深度性的都市消費趣味。但其實我們做一個簡要的回顧,恐怕這種開放的性文化呈現方式在“前任”系列這里到了一個新階段。同時期出現的“小時代”這種極具荷爾蒙的系列電影中也未曾像“前任”一樣裸露地將性文化帶進大眾消費的視野,標榜“青春”題材的電影也未如此坦然完成性消費。這種悄然的變化使得我們不得不思考一些問題,是否展示了性與社會多樣性的圖景?是否我們已經默認了這種新的“社會時尚”?
“前任”系列電影不僅將性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而且還參與了影片的敘事。一夜情模式成為兩性關系的潤滑劑,是促進故事發展的必要手段。第一部的孟云和夏露、第二部的余飛和伊澤,他們的感情的發展就是基于發生了性關系之后才有了故事發展的可能。尤其在第三部中,余飛和丁點已經分手,而丁點借著“了斷局”“坦白局”的方式不斷約余飛,才使兩人意識到誰也離不開誰。性的實踐從私密話語走向了媒介空間,被銀幕用各種方式加以利用,取消了性在藝術傳統中的崇高感,凸顯了一種新的實踐:生理需求和大眾消費文化達成一致。“流行以前的一切藝術都是建立在某種‘深刻’世界觀基礎上的,而流行,則希望自己與符號的這種內在秩序同質:與它們的工業性和系列性生產同質,因而與周圍一切人造事物的特點同質,與廣延上的完備性同質,同時與這一新的事物秩序的文化修養抽象作用同質。”[9]104-105讓·鮑德里亞是站在日常物品的藝術性話語上來分析當代藝術的策略。這對我們理解關于性的銀幕呈現有很大幫助。觀眾看到性從私下被熱衷的討論對象變成了被放大的絕對現實,我們成功把性運作成平庸的(日常的、大眾的)藝術,但是平庸只是崇高這個范疇的當代版本,也是一種超驗(transcendent)的范疇。“物品只有在它的用途方面、在使用它時才是平庸的。物品從它開始指涉時就不再平庸了。”[9]108對于“前任”系列電影,最直接的力量是我們看到了被束縛的身體如何得到解放。
性文化的消費和階層特征有很大關系。三部影片的主要人物中,孟云是一家小公司的老板,余飛的身份是明星和白領,丁點經營一家奶茶店,夏露、羅茜、伊澤、林佳都是公司白領,基本上都屬于城市中產階層的行列。他們在影片中的活動空間除了公司外,常出沒的就是酒吧、KTV包廂、臥室和客廳,最重要的情節基本上在此空間中完成。這是一組都市青年和都市場景的組合方式。他們從事腦力勞動,有較強的消費能力,追求較高的生活質量,有大量的閑暇時間。基于這樣的條件,“前任”系列電影才有展示都市生活的可能——以性的方式滿足自身的都市感。據此,我們還看到了一種虐戀(sadomasochism)文化的傾向:夏露離開孟云一年后,之前經常換女友的孟云則清教徒式地繼續堅守對她的感情;余飛把感情的失敗轉嫁到自己的演唱會上,發泄自己的痛苦;孟云和林佳分開后,各自遵守承諾,孟云扮演至尊寶在大街上大喊“林佳,我愛你”,林佳則一邊痛哭一邊吞咽使自己過敏的芒果,作為徹底的告別。這些情節都在影片情感高潮處出現,還有前文所論述的“性別對抗”本身就是施虐與受虐的實踐。“虐戀者中多有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人士,可能來自一種補償心理:那些在社會中有權有勢的人才會產生對喪失權利的幻想,也才能將無能為力的狀況性感化。”[10]只有具有較高的經濟能力的人才有時間和精力頻繁享受這種文化消費。對于觀眾而言,會默認這種既定的社會狀態,也會沉溺于劇中人物所傳遞的情感力量。
四、結語:溫柔的陷阱
消費邏輯不應該主宰藝術創作的規律。從“小時代”到“前任”,我們看到了現代都市想象和二十年前的《愛情麻辣燙》(張揚導演)的都市文化已經天差地別,如果說后者契合都市生活的現狀,是“詩意”的,那前者則是“時尚”的,因為它代表了消費社會的轉型。看似“愛情”的表象則隱藏著一種滿足自身都市青年的虛榮和假象,建立了“都市”與“非都市”的對立觀,誠如孟云開頭所說,“要是我大學畢業就回家鄉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那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已經當爹三年了”,前提便是影片所呈現的都市生活導致的異化:晚婚和不斷地約會、泡吧。不禁要問道,“前任”中所展示的情節究竟在多大范疇內代表了都市青年?代表了多少都市青年?
顯然,按照消費文化的邏輯,它將“堅守”“浪漫”“珍惜”等愛情觀念融入兩性文化之中,將性和現代都市混雜起來,讓觀眾能夠在觀賞過程中體驗到“日常生活審美化”。觀眾已然難以區分真實和幻境了,很容易將少數人的生活用來體認自身。不經過思想的過濾和理性的認知,日常審美化的開放性視覺體驗會變成溫柔的陷阱,用消費時代的欲望滿足代替真實生活,或者說,它們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影片中隨處可見的對性感身體(包括男性)的呈現,和美食、酒吧、泳衣一樣,都成為缺乏藝術美感、缺乏情感認同的“物”,造成了審美疲勞的局面。而且,這種按照消費邏輯生產的東西還在不斷地生產和復制。我們既看到了兩性文化視覺解放的可能,又目睹了藝術倫理(藝術主體的深刻體認和擔當)和大眾文化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