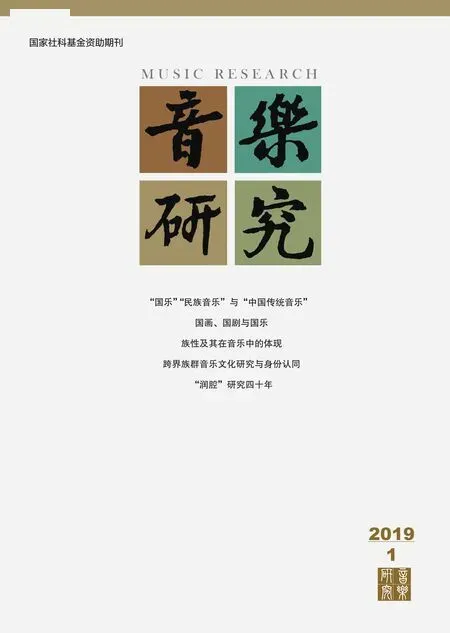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與身份認同
——以中國西南與周邊跨界族群的比較研究為例
文◎楊民康
在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界,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和音樂與身份認同之間關(guān)系的研究,都是已經(jīng)在學(xué)界醞釀了很長時間,但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學(xué)術(shù)話題。如今,兩個學(xué)術(shù)話題在自身范圍內(nèi)都已經(jīng)有了不少初步的課題和成果積累,并且進入到必須深化學(xué)術(shù)議題和展開進一步的學(xué)科“跨界”研究新階段。而將兩個學(xué)術(shù)話題結(jié)合起來討論,如今也水到渠成,成為借他山之石,以微視和濃描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的必然之舉。本文將結(jié)合筆者近年來在云南西雙版納與境外周邊國家和地區(qū)進行田野考察和課題研究的實例,對之進行延伸和展衍性質(zhì)的討論。
一、從社會分層角度看音樂文化層、文化流與認同網(wǎng)絡(luò)的關(guān)系
(一)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是一張文化身份認同之網(wǎng)
中國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隸屬于國家、民族社會文化體系。有學(xué)者提出:“眾所周知,社會文化體系好比一盤棋,或一張巨網(wǎng),在每一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個人必然要與世界、與他人建立認同關(guān)系,并遵循文化編碼程序,逐步確定自己在這一社會文化秩序中的個體角色。”①陶家俊《身份認同導(dǎo)論》,《外國文學(xué)》2004年第2期,第37—44頁。作為國家、民族社會文化體系的子項之一,中國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亦呈現(xiàn)為一張文化身份認同之網(wǎng),并且攜帶著自己的編碼程序和表述方式。一方面,該認同之網(wǎng)上存在著按文化圈、文化層的歷史性規(guī)律而發(fā)展、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認同階段和層次序列,其中的不同認同類型,是自族群和地域內(nèi)部傳承向跨地域、族群、文化傳播的方向,前后依序,順著時針,由小漸大,由點到面,滾雪球般地自然增長,最后形成一張認同階序之網(wǎng)。比如,由族群認同、區(qū)域認同、信仰認同到國族認同,就是一個規(guī)模大小不一,文化同質(zhì)程度有異,帶有歷史形成和層次區(qū)分特征的認同階序。另一方面,在現(xiàn)實生活里,文化個體攜帶著自身的(音樂)文化標(biāo)識,如同網(wǎng)眼、網(wǎng)點、網(wǎng)點群落(后文簡稱“網(wǎng)群”)和網(wǎng)線,分布于整個認同之網(wǎng)上面。并且,這些網(wǎng)線、網(wǎng)眼、網(wǎng)點是隨著人群的流動,在自然形成的地理環(huán)境中線性地漫游和流動,呈不規(guī)則狀排列和組合的。相應(yīng)的是,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中每一層面、種類的音樂文化及其內(nèi)文化持有者,都身處于文化層或社會分層階序之網(wǎng)上的某一個位置,并且按照文化身份認同的規(guī)律和目的,由“自我”向“他者”,依上下左右各方關(guān)系來認識、調(diào)整自己的角色關(guān)系。而相應(yīng)課題的研究者,則有必要通過對自身目的意義的認識和表述過程,將我們的微觀、定點個案研究和線索、多點比較研究同該音樂類型及其文化持有者在身份認同之網(wǎng)上的定位和關(guān)系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把握好主位認同與客位辨析兩方面互補、互滲的關(guān)系,以真正達致音樂與身份認同研究的深層意義和學(xué)術(shù)目的。
(二)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圈、文化層與身份認同階序之間的關(guān)系
廣義的音樂文化圈,兼有理論和實踐層面,其對象包括文化圈、文化層、文化叢;從中國跨界族群音樂文化角度看狹義的音樂文化圈,多與宗教文化為基礎(chǔ)形成的少數(shù)民族文化圈相關(guān)。一般情況下,在前者意義上較少涉及文化認同問題,但在關(guān)乎后者的研究中,文化身份認同的討論則必不可少。在以往的多篇論文中,筆者基于長期、持續(xù)的觀察和研究,曾經(jīng)提出了在云南與周邊傣仂亞佛教音樂文化圈內(nèi)包含了下述三個基本的文化演生層次的觀點。
1.地域性——原生性民間音樂文化層:有關(guān)“前現(xiàn)代”背景下形成的,同一條邊境兩側(cè)呈定居狀態(tài)的跨界族群傳統(tǒng)民間音樂文化的研究。
2.區(qū)域性——次生性佛教音樂文化層:因傳統(tǒng)的國家政治、人為宗教、經(jīng)濟等橫向傳播交流影響而形成的跨界族群佛教音樂文化的研究。
3.整體性——再生性雜糅音樂文化層:指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背景下,通過原生、次生文化層與分布、環(huán)繞其上、其側(cè)的主(流)文化層——具現(xiàn)代民族國家及其現(xiàn)代政權(quán)特征的各國政治、社會、經(jīng)濟文化上層因素的并存合力,且受到外來的移民文化與本土文化互融現(xiàn)象的影響而形成的雜糅音樂文化的研究。②參見楊民康《跨界族群音樂探析:云南與周邊南傳佛教音樂文化圈論綱》,《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1期,第45—51、111頁。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看,以往在云南與周邊南傳佛教文化圈內(nèi)外關(guān)系脈絡(luò)中,族群認同居于地域性——原生層次,亦是圈內(nèi)外諸族群(尤其是部分不信仰三大宗教的族群)內(nèi)部最早生發(fā)的、最根本的文化認同因素。而在相對顯性的文化層面上,跨界族群與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文化圈相互交織,所生發(fā)的信仰認同便居于區(qū)域性——次生層次。其中,以南傳佛教為代表的信仰認同一直是東南亞不同跨界信仰文化圈內(nèi)外較具整合性和穩(wěn)定性的要素之一,起到維系不同地區(qū)、族群之間文化交往及情感和諧關(guān)系的重要的紐帶作用。如今,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里,居于底層的族群認同和中層的信仰認同、區(qū)域認同已經(jīng)逐漸讓位于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等其他文化認同因素,諸多同音樂與文化認同相關(guān)的實際問題也伴隨而生,從而為我們的專題性考察和研究創(chuàng)下了較大的空間。從前期的相關(guān)研究看,我們較多關(guān)注到上述三個基本層的第一、二個層面,尤其是在近年來的研究中,對于南方和北方地區(qū)跨界族群文化中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含音樂文化)所起到的傳播、交融作用給予了較大的重視和考察研究。但對第三個層面的研究相對較薄弱。因此,在下文的討論里,將對涉及該層次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給予較多的關(guān)注。
二、從身份認同角度看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分層和屬性
在當(dāng)今中國學(xué)界,由費孝通先生提出的,由漢族和55個少數(shù)民族共同組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學(xué)術(shù)理論框架里,國家認同可視為中華民族意義上的整體文化認同,然后才是各單一民族的民族認同。這個問題或許涉及我們必須進一步從概念到實體去認識和討論國家建構(gòu)(state—building)和民族建構(gòu)(nation—building)的性質(zhì)和特征。對此,一種可藉以參考的說法是:“‘國家建構(gòu)’(state—building),在具體層面是指國家獲得其特征(國家是一個活動主體;國家是制度建構(gòu)和公共權(quán)力代表的主體)的過程;在抽象層面,‘國家構(gòu)建’(state—building)指的是政治權(quán)力的產(chǎn)生、存在、使用和更替的合理化過程。”關(guān)于民族,“許多學(xué)者認為‘民族’(nation)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構(gòu)建的,是在政治權(quán)力的推動和保障下構(gòu)建的。在某種程度上,沒有國家就沒有民族。③參見嚴(yán)慶《民族、民族國家及其建構(gòu)》,《廣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第9—14頁。可見,在跨界族群音樂的文化認同研究里,“國家建構(gòu)”“民族建構(gòu)”和“族群”(ethnic group)“宗教”“區(qū)域”等,是涉及基本分析思維和身份認同階序的幾個比較重要的概念。“民族”與“族群”是兩個有必要加以明確區(qū)分和加強認識的重要概念。一般認為,“民族”指的是一個文化——政治共同體,成員們分享共同的文化和領(lǐng)土。它可以是由單一“族群”(ethnic group)構(gòu)成的,也可以是由多“族群”結(jié)合而成的。也有學(xué)者指出,在1908年之前,民族的意義跟所謂族群單位幾乎是重合的,不過之后則愈來愈強調(diào)民族“作為一政治實體及獨立主權(quán)的涵義”——民族最重要的涵義,是它在政治上所彰顯的意義。族群通常是指移民群體和在政治上沒有被動員起來的少數(shù)群體。族群產(chǎn)生于個人和家庭移民,他們往往都希望并入更大的社會,并希望被接受為該社會的完全成員。④同注③。由此而論,目前國境線兩側(cè)擁有共同族源的居民人口,其共有的身份認同基礎(chǔ)和相應(yīng)的概念表述,應(yīng)該是先在于(建構(gòu)意義上的)國家和民族的“族群”,而非后來才建構(gòu)產(chǎn)生的“民族”或“國族”。同理,“跨界族群”相比“跨界民族”而言,也是一個更為合適的概念表述。
此外,鑒于研究對象具有的多樣性和復(fù)雜性背景,在跨界族群音樂與文化認同的關(guān)系上,僅只提及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族群認同還遠遠不夠,還有必要提及宗教認同、區(qū)域認同與地域認同等不同的認同因素。倘若結(jié)合音樂認同網(wǎng)絡(luò)與不同認同類型之間的關(guān)系看,將上述諸項文化認同因素按其社會文化內(nèi)部關(guān)系予以排列和定位,就形成了一個規(guī)模大小不一(由小到大),文化同質(zhì)程度有異,帶有歷史形成過程(由下而上,區(qū)分先后)和歸屬層次區(qū)分(由上而下,逐層統(tǒng)屬)的認同階序網(wǎng)絡(luò)。現(xiàn)以云南西雙版納與周邊國家跨界族群的音樂與認同階序及其層次劃分關(guān)系為例列表于下:

表1 音樂與認同階序與層次劃分關(guān)系圖表
根據(jù)表1,每一文化層及音樂認同層級均同時向上具有隸屬性或依附性,向下具有統(tǒng)領(lǐng)性或管攝性。并且,對外、向上時,通常凸顯自身的個性和標(biāo)識性特征;對內(nèi)、向下時則強調(diào)共性和認同性特征。進一步講,對外、向上時,重在通過客位的辨析、歸并和描寫,突出和區(qū)分文化(音樂)形態(tài)、地(區(qū))域風(fēng)格的差異性;對內(nèi)、向下時,重在通過主位意識的觀察和歸納,突出和強調(diào)文化的同一性及其社會調(diào)適作用。舉例來說,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開展民族識別期間,語言學(xué)、人類學(xué)及音樂學(xué)不同學(xué)科學(xué)者,便按照馬克思主義民族學(xué)及斯大林的相關(guān)論述,為民族識別定下了“四個共同”(語言、地域、經(jīng)濟生活、心理素質(zhì))的理論基調(diào),都從各自的不同角度,一齊為辨析、區(qū)分、歸并和描述各民族的文化特質(zhì)做了大量的基礎(chǔ)工作。其結(jié)果便是通過大家的努力,一方面就此凸顯了不同民族文化外部身份標(biāo)識的差異性特征,另一方面規(guī)范了各民族內(nèi)部文化認同的尺度和標(biāo)準(zhǔn),并且最終達成了民族內(nèi)部多數(shù)成員之間的一致性認可。可以說,在這項工作中,外部身份標(biāo)識與內(nèi)部文化認同乃是一種內(nèi)外交合,一體兩面的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還同樣反映在我國各民族的節(jié)慶儀式(音樂)之中。比如,在傣族和孟高棉語諸民族的潑水節(jié)、彝語支各民族的火把節(jié)、瑤族的盤王節(jié)等許多民族節(jié)日里,如今往往形成了兩種(或多種)節(jié)期,兩套(或多套)程序,同一種音樂舞蹈也往往準(zhǔn)備了多套表演曲目,以應(yīng)付對內(nèi)(祭祀、自娛)、對外(旅游、展演、公務(wù)),向下(族群、村社)、向上(民族、國家)的不同層面需求。它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語境下,傳統(tǒng)節(jié)慶儀式和民間表演藝術(shù)都普遍具備了面臨不同活動對象和環(huán)境要求而必需的潛在適應(yīng)能力。在不同民族自治區(qū)域,上述內(nèi)外、上下功能作用及適應(yīng)能力的發(fā)揮,皆依其所處級別而有相應(yīng)的表現(xiàn)。以下簡略論述音樂民族志方法適應(yīng)于文化認同階序研究的幾種基本類型。
三、定點、多點音樂民族志研究與族群、地域文化認同
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究其實質(zhì),乃是一種聚焦于族群文化層面的研究性課題。對此,可用廣義和狹義加以區(qū)分。
廣義的跨界族群音樂研究,即指跨地域性(區(qū)域性)歷史族群的研究,屬次生文化層。比如,當(dāng)我們對云南與周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qū)進行內(nèi)圈(含云南與周邊泰、緬、老、柬、越等陸路國家和地區(qū))和外圈(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等海島國家)的區(qū)分時,便可以看到自古以來孟高棉、壯侗、漢藏和苗瑤等四大歷史語言族群便一直居住在整個內(nèi)圈,其分布狀況是:
a.孟高棉語族諸族群,主要居住在國境線兩側(cè),境外如柬埔寨高棉族和緬、泰等國的孟族,境內(nèi)主要是布朗、德昂和佤等民族,為云南與周邊東南亞國家最早的世居族群,其分布狀況除了在柬埔寨為聚居狀態(tài)外,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均為自然鋪開,非均勻散布。
b.壯侗語族諸族群,主要居住在國境線兩側(cè),以撣傣族群為主,由內(nèi)向外,自然鋪開,均勻分布。
c.苗瑤語族諸族群,跨國境線分布,由內(nèi)向外,國內(nèi)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區(qū)的廣西、湖南及西南地區(qū)的貴州、云南等省,國外則由內(nèi)向外,呈啞鈴狀,兩頭相對密集聚居,中間較為稀疏狹窄。
d.藏緬語族諸族群,西南地區(qū)的白、納西、藏、彝等少數(shù)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國境內(nèi),部分民族(如藏、彝、拉祜、傈僳、景頗等)在境外也有分布。
從此意義上看,筆者曾經(jīng)做過的一項有關(guān)西雙版納景洪傣族(屬傣仂支系)與緬甸景棟撣族(屬傣艮支系)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因為涉及了同一歷史語言族群中兩個不同支系(族群)之間的音樂文化關(guān)系,便屬于相對廣義性層面的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課題。⑤楊民康《跨界族群音樂探析:叩問最難詢訪的近鄰——云南景洪與緬甸景棟潑水節(jié)儀式音樂比較研究》,《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6期。
而狹義的跨界族群比較研究,則主要涉及現(xiàn)今于同一廣義族群內(nèi)部,按山區(qū)、平壩、河流等地理條件自然分布的,較小規(guī)模和體量的跨國境地域性族群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相比而言,筆者在上述課題中,同時也涉及了中國傣族的傣仂支系與緬甸撣族的傣艮支系在周邊國家地區(qū)跨境分布以及布朗族與居于景棟地區(qū)的同源族群傣婁人⑥泰婁人,又稱洛人,屬孟高棉語族。今天,景棟的這些人被稱為“泰婁”,被劃歸撣族;在清邁稱之為“洛”或“拉佤”,在中國的云南省西雙版納則被認定為布朗族。的關(guān)系,便是狹義的地域性跨界族群(音樂)文化關(guān)系的例子。并且,與文化認同階序中“民族認同不跨國境”的情況有所不同,這里所提到的廣義或狹義的“族群認同”或“族群音樂文化認同”,其歷史上與當(dāng)代時期的分布和傳播,都是不受國境所區(qū)隔和阻攔的,同時也是諸音樂認同層面中形成時間最早的一種認同層面。
20世紀(jì)末葉,通過對中緬邊境中方一側(cè)的布朗、傣、佤、德昂、瑤、傈僳等民族不同地區(qū)分支的傳統(tǒng)儀式音樂所做的較細致的考察和研究,筆者在定點個案的課題研究上積累了一定的經(jīng)驗。但同時也認識到,若從跨地域性(區(qū)域性)比較研究的角度看,僅針對跨界族群的國內(nèi)部分展開考察研究是存在明顯問題的。比如,國內(nèi)的布朗族的三個分支主要分布在西雙版納勐海縣的巴達、西定和布朗山以及臨滄市的雙江等地;傣族的三個最大分支分布在西雙版納、德宏和臨滄三地;瑤族的兩個主要支系盤瑤和藍靛瑤主要分布在廣西、云南兩個地區(qū)。這些通過民族識別而產(chǎn)生的少數(shù)民族,其國內(nèi)各分支(族群)彼此過去并沒有太多直接的聯(lián)系,而各分支自身卻由于是跨界族群的原因,其歷史上聯(lián)系最密切的往往是分布在國境線外方一側(cè)的同族群村寨居民。因此,要想真正對之展開跨地域性(區(qū)域性)比較研究或多點音樂民族志研究,必須把學(xué)術(shù)觸角展延到境外同族群及有共同信仰生活的其他地區(qū)。比如,傳統(tǒng)居住在云南省西雙版納的傣仂人,目前也有部分居住在泰國、老撾、緬甸等周邊國家地區(qū),在與其周邊族群(壯侗語族其他族群及布朗族)共享南傳佛教信仰(為前述“廣義族群”的共同信仰)的同時,還以“祭勐”“祭寨”儀式及相應(yīng)的自然宗教崇拜作為自己的“亞信仰”,并以其中民間歌手贊哈的演唱活動作為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和傳載方式,共同構(gòu)成區(qū)別于廣義族群信仰及大傳統(tǒng)(或主文化)層面的,專屬于狹義族群和小傳統(tǒng)(或亞文化)的另一種音樂與文化認同層面。與贊哈歌手類似的情況,還發(fā)生在緬甸撣邦的傣艮人與中國云南省孟連縣孟阿鄉(xiāng)的傣艮移民中,也同樣流傳著共有的“森”“拽”等敘事性民歌,如今乃是作為兩地傣艮人及孟高棉語族群(如景棟的傣婁人)之間形成族群認同或雖未形成族群認同,但形成文化交融紐帶(如緬甸傣艮人、傣婁人與中國布朗族之間)的一張張重要“名片”存世。
四、跨界族群音樂比較研究與國族音樂文化認同
從跨界族群音樂的角度看,歷史形成的跨國界族群(音樂)文化分布以及族群認同,產(chǎn)生并形成了邊疆少數(shù)民族(音樂)文化與境外同族群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諸多交融性和同質(zhì)性因素,這類因素同已經(jīng)包容、滋生了許多政治、社會問題的跨境宗教文化圈因素一樣,與主要通過文化建構(gòu)途徑形成的當(dāng)代國家、民族及其國族文化認同關(guān)系之間存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矛盾問題。而要想解決這些矛盾問題,若像以往那樣僅只通過對歷史形成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形態(tài)及其族群屬性和族群認同層面加以區(qū)分和分析還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有必要結(jié)合21世紀(jì)以來中國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發(fā)展變遷與文化認同狀況,著眼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語境下,因種種社會音樂文化實踐活動中產(chǎn)生的復(fù)雜矛盾狀況而導(dǎo)致的各種文化認同問題展開相關(guān)研究,才能據(jù)此提出相對合理的解決方案。
以云南景洪的傣族與緬甸景棟撣族的比較為例,兩地的民族認同,都聚焦于潑水節(jié)于一身。不同的是,在景洪一側(cè),以傣族為主體的潑水節(jié)慶祝活動有了國家在場(國家認同)作為支撐,布朗族還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希望設(shè)立本民族“桑刊節(jié)”(為潑水節(jié)的別稱)的呼吁,由此便都具有較為強烈的民族文化建構(gòu)的意向。而在景棟一側(cè),這種國家在場(國家認同)的力度大為減弱,乃至其中包含了甚多的族群認同因素。而這個族群認同的因素又與撣族(傣艮人)與傣婁人的長期交往歷史糾結(jié)在一起,⑦在撣族人乃至東南亞的其他撣傣族群中,一直有認為孟高棉人是這里最早的主人,應(yīng)該給予特殊尊重的看法。從而出現(xiàn)了每年以傣艮人為主舉行潑水節(jié)慶祝活動時,必須出現(xiàn)以40位傣婁人通宵擊大鼓“守歲”的特殊場景。而在民族設(shè)立的問題上,由于緬甸政府一直沒有將婁人視為單一民族,而是按“傣”的分類,將之歸入后一民族,稱為“傣婁”,以致在潑水節(jié)活動中,婁人的擊鼓守歲,也就習(xí)慣性被看做是撣族慶典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在西雙版納地區(qū),除了上述為彰顯民族文化身份而提出的“桑刊節(jié)”呼吁外,由傳統(tǒng)民歌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來的“布朗彈唱”也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并且作為布朗族的一張重要的文化名片,出現(xiàn)在幾乎所有布朗族人出沒的社會公眾場合,以此彰顯出布朗人著力建構(gòu)自己族群文化標(biāo)識,以凝聚自身民族文化認同的強烈意愿。⑧參見楊民康《一維兩閾——布朗族音樂文化志》,中央音樂學(xué)院出版社2012年版。與此類似的立足于民族區(qū)域文化標(biāo)識及身份建構(gòu)的思路和做法,還可以舉出今天中國南方彝語支民族的火把節(jié)、苗族的三月三,北方蒙古族的那達慕、藏族的藏歷年等,都有從以往的宗教或民俗節(jié)慶泛化為民族節(jié)日的傾向。還有,各少數(shù)民族的許多傳統(tǒng)音樂品種,如今已借助國家或省市級“非遺”評審而成為著名的民族或地方文化品牌。而一些國產(chǎn)少數(shù)民族題材電影如《五朵金花》《阿詩瑪》《蘆笙戀歌》《劉三姐》《冰山上的來客》中的插曲,則借助于大眾媒體傳播手段聲名遠揚,被冠上了“族歌”“省(市)歌”的名銜,既導(dǎo)致種種新的“族性音樂”由此而生,也形塑出一批與“民族”“國家”政治實體相匹相依的族性文化標(biāo)識。因此,從本文的視角,并結(jié)合相關(guān)民族學(xué)理論來看,上述在民族、國家及其文化意識形態(tài)建構(gòu)過程中產(chǎn)生、形成的諸多音樂文化類型,無論其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密切、深厚程度與否,都已經(jīng)成為帶有新的政治、社會象征意義,包含國族認同的隱喻、標(biāo)識和文化認同印記,擁有了與“國家在場”相互匹配、彼此支撐的藝術(shù)功能和社會作用,并以此區(qū)別于族群層面的象征、隱喻和認同意義的其他藝術(shù)產(chǎn)品。
此外,凡是帶有國族文化標(biāo)識與認同特征的節(jié)慶儀式音樂藝術(shù)產(chǎn)品,其相關(guān)展演或展示活動主要是以國境線中方區(qū)域為基本界限和范圍,并且在具有國家公民及民族成員身份者中間產(chǎn)生、發(fā)揮其文化認同效應(yīng),并以此擁有了可區(qū)別于族群性音樂產(chǎn)品的跨界族群文化標(biāo)識與認同范圍,及其境內(nèi)外貫通的社會性傳承與傳播功能。反之亦然,境外于“民族”“國家”層面產(chǎn)生的音樂文化產(chǎn)品,其社會流通及文化認同也一樣受制于這個同“國家”“國境”相關(guān)的文化規(guī)律。所以,在音樂與文化認同的研究中,有效地區(qū)分出民族認同與族群認同的階序性關(guān)系,明確建立起“民族不跨界、跨界乃族群”的文化意識,不僅可以讓我們?nèi)フ_地認識跨界族群文化的基本性質(zhì),同時也有助于我們較準(zhǔn)確地去辨識國境兩側(cè)不同衍生性樂種、舞種的社會性質(zhì)、流通范圍及其文化變異過程。
五、跨界族群音樂文化圈研究與信仰認同
文化圈研究是來自于人類學(xué)的一種比較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在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中,文化圈方法的應(yīng)用往往是與宗教研究及信仰認同研究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在此類研究中,怎樣才能正確地認識傳統(tǒng)宗教文化對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所起到的作用?如何處理好信仰認同與國族文化認同的關(guān)系?是至關(guān)重要的兩個問題。
中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傳統(tǒng)節(jié)慶,有許多原本就與傳統(tǒng)宗教儀式活動相關(guān)。在云南與周邊地區(qū),當(dāng)20世紀(jì)中葉以來“宮廷與寺院為中心”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gòu)紛紛遭致解體時,南傳佛教節(jié)慶儀式及其吟唱活動在境外地區(qū)被奇跡般地保留下來,而在境內(nèi)地區(qū)則經(jīng)過了歷次政治運動的洗禮,在許多年銷聲匿跡之后,也得以迅速的復(fù)活和還原。可以說,南傳佛教節(jié)慶及其吟誦藝術(shù)所包含的文化大傳統(tǒng)基因及其所擁有的“跨族群——地域——文化”傳播能力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維護和紐帶作用。今天,中緬、中老等國境線兩側(cè)的節(jié)慶儀式活動都可為三類:1.各族群民間節(jié)日;2.以潑水節(jié)、安居節(jié)為代表的佛教節(jié)慶;3.以國慶節(jié)為主的各種現(xiàn)代國家節(jié)慶。它們分別對應(yīng)于前述云南與周邊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的原生、次生、再生三個文化演生層面。其中,南傳佛教節(jié)慶儀式居于中層,是維系國境兩側(cè)南傳佛教文化圈各族群文化歸屬感和認同感的最穩(wěn)定的紐帶之一。
從文化與族群的關(guān)系看,三類節(jié)慶或三個層次中,原生層次里,傳統(tǒng)民間音樂文化對族群本身有著明顯的依附性;次生層次里,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文化相對具有較多的獨立性、自主性和導(dǎo)向性;再生層次里,顯性的旅游文化、官方節(jié)慶(如定為民族節(jié)日的官方潑水節(jié))等因素則對隱性的佛教大傳統(tǒng)及政治文化具有依附性。
因此,從文化認同的情況看,在跨界族群文化三層次中,在各人為宗教文化圈里,位于中層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潑水節(jié)、安居節(jié)以及北方民族的同類節(jié)日,如藏族的祈禱節(jié)和雪頓節(jié)、維吾爾族的肉孜節(jié)(即開齋節(jié))和古爾邦節(jié)以及存在于南方多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基督教圣誕節(jié)等,在文化的自身獨立性、自主性及國境兩側(cè)的文化認同感、歸屬感等要素上居于比較顯著的地位,在諸對象層次中據(jù)有相對重要的文化意義和學(xué)術(shù)性意義。比之而言,處于原生、再生層次的諸文化形態(tài)則不同程度體現(xiàn)出孤立性或局部性的認同狀況。例如,原生形態(tài)中,傳統(tǒng)民間音樂較多為縱向傳承為主的地域性樂種、樂器;再生形態(tài)中,各國的國慶節(jié)均具有特定的時間、空間屬性和相異的政治文化色彩。此外,像潑水節(jié)這樣的傳統(tǒng)節(jié)日被定為民族節(jié)日后,也被賦予了國家慶典及國族認同的新的象征意義,并有相異于民間傳統(tǒng)節(jié)日的較固定的舉辦時間。像新生的布朗族桑刊節(jié),也是在此意義上被重新提上了議事日程。
信仰認同的情感因素,往往通過傳統(tǒng)節(jié)慶及節(jié)慶儀式音樂來予以體現(xiàn)。俗話說,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這里比喻的是一種鄉(xiāng)土文化情緣或(廣義的)族群、地域文化認同情感。在信仰南傳佛教的不同國家和廣大區(qū)域內(nèi),來自四面八方信眾的類似的情感交流和信仰認同,可以通過《南無經(jīng)》里的一句十八字巴利語偈言來予以實現(xiàn)。當(dāng)然,偈言必須配上與不同語言的音調(diào)、語調(diào)相適應(yīng)的曲調(diào)旋律。在同一族群或相同教派內(nèi)部,僅憑曲調(diào)旋律的一致性,便可以獲得很好的溝通效果。而在不同地域來源的信眾之間,由于存在著異文化語言引起的溝通障礙和陌生的音調(diào)、語調(diào)帶來的種種心理、審美隔閡,當(dāng)雙方同時使用巴利語(而非梵文)的偈言作為相互溝通的信號符碼時,便立即達到了彼此接受和認同的效果。同樣,在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和地區(qū),無論有多么復(fù)雜的民族雜居區(qū)域背景,來自任何族群的外來客人,一進教堂,聽到贊美詩的吟唱,馬上就能夠進入彼此認同和樂于交往的情景。應(yīng)該說,這眾多的日常生活事例就充分體現(xiàn)了音樂認同在各種傳統(tǒng)人為宗教文化圈內(nèi)所具有的傳播能量和社會效應(yīng)。此中,除了南傳佛教經(jīng)腔外,諸多的道教、伊斯蘭教經(jīng)腔及少數(shù)民族基督教贊美詩,都是一張張亮眼的文化名片,在各族群、民族群眾的跨地域性交往中,起到顯示自己的外部身份標(biāo)識和促進彼此文化認同的重要作用。
六、區(qū)域音樂文化比較研究與區(qū)域文化認同
21世紀(jì)以來,區(qū)域音樂研究在中國民族音樂學(xué)界受到日益廣泛的重視,其研究過程從當(dāng)初的音樂色彩區(qū)研究、音樂地理學(xué)起步,如今已在理論視野和學(xué)術(shù)空間上有了較大的拓展,成為可以從不同的學(xué)科和學(xué)術(shù)層面加以比較、綜合、互滲的、包容性較強的學(xué)術(shù)話題。從此意義上看,筆者多年來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領(lǐng)域所提倡和奉行的多種研究方法中,文化圈——文化層分析觀念及方法,既與區(qū)域音樂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意義范疇有所關(guān)聯(lián),又在方法論上存在一定的差異。
區(qū)域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有多種多樣的表現(xiàn),本文在此主要涉及與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相關(guān)的兩個對象層面:一是傳統(tǒng)的跨界族群宗教文化圈(南傳佛教、基督教)內(nèi)部,曾經(jīng)分布在國境兩側(cè),歷史上形成并依托當(dāng)?shù)刈迦翰柯浼暗胤秸?quán)存在的、具有可比較研究意義的不同族群音樂文化區(qū)域。比如20世紀(jì)50年代以前分別存在于西雙版納以傣仂為主體族群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區(qū)和緬甸景棟以傣艮為主體族群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區(qū),⑨相關(guān)研究成果可參見楊民康《云南景洪與緬甸景棟潑水節(jié)儀式音樂比較研究》《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6期,第46—55頁。還有德宏地區(qū)以景頗族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樂文化區(qū)和境外以緬甸克欽邦克欽人為主建立的基督教音樂文化區(qū),⑩相關(guān)研究成果可參見徐天祥《緬甸克欽族基督教音樂的本土化研究》,中國音樂學(xué)院2016年博士學(xué)位論文。都是該領(lǐng)域有一定典型區(qū)域劃分意義的研究對象。二是建立在前者基礎(chǔ)上,于當(dāng)代歷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區(qū)域性音樂文化區(qū)和以次級“主文化——亞文化”結(jié)構(gòu)呈現(xiàn)的文化層。其中,尤其讓人注目的是一些當(dāng)代國族文化語境下民族自治區(qū)域(音樂)文化體系建構(gòu)的例子。?參見張林《建構(gòu)的傳統(tǒng)——新賓“滿族傳統(tǒng)儀式音樂”與文化認同》,中央音樂學(xué)院2017年中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方向博士學(xué)位論文;苗金海《鄂溫克族音樂文化建構(gòu)與認同——以巴彥呼碩敖包祭祀為例》,《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2017年第1期,第19—29頁。比起前一類文化區(qū)來說,該類文化區(qū)因同時顯現(xiàn)了族群認同、地域認同、國族認同(在國境兩側(cè),各自的族群認同已經(jīng)多半分別演化并體現(xiàn)為國族認同關(guān)系)與信仰認同等各類認同因素,以致更顯現(xiàn)出多層性、立體性、復(fù)雜性和對比鮮明性等特點。
七、離散族群音樂與族裔散居身份認同
族裔散居及其身份認同是跨界族群及族群認同的一種變體形式,也是跨界族群區(qū)域音樂文化比較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由此看云南與周邊東南亞地區(qū),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同族群人員中,有不少是以族裔散居的方式在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分布。從外遷的環(huán)境及方式看,鑒于整個西南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交通是以陸路為主,海路為輔。其中,云南與周邊緊鄰國家,亦即東南亞內(nèi)圈諸國的關(guān)系,則更多是陸路的特點。云南少數(shù)民族的離散族群也是沿著陸路的山地、平壩向境外遷徙和散居。若將此推及整個中國與周邊的跨界族群音樂文化研究,可以說也是一個共性特點,并且,與西方學(xué)者以海路為主要對象及相關(guān)方法相比較,這也是顯得非常不同的一個重要特點。此外,這些離散族群在遷徙和居住方式上存在著點性散居和線性散居的區(qū)別。其中的單點性散居族群,可舉云南西南部少數(shù)民族與現(xiàn)居緬甸景棟的各民族之間關(guān)系為例。20世紀(jì)50——80年代,景棟以其具有的境外城市地位和條件,曾經(jīng)作為解放戰(zhàn)爭之后流緬國民黨軍隊暫住基地而存在,此間還接受了大量外流的各族移民。至數(shù)年前筆者訪問該地時,在景棟這方圓幾十里土地和幾十萬人口中,就包含了本土各族原住民,來自前述云南沿邊各地各族的自然、政治移民以及半個世紀(jì)以前遷來的戰(zhàn)爭移民、軍人眷屬等不同成分來源。縣城內(nèi)外傣族、漢族及其他族群移民社區(qū)鱗次櫛比,互鄰互市,交錯而居;城邊街道上,佛寺、教堂、清真寺、道觀密密麻麻,傳道誦經(jīng),聲聞數(shù)里。從身份認同角度看,每個移民社區(qū)、寺觀教堂,都是一個帶有清晰的社會、政治身份的族群單位,都有自己包括音樂文化(經(jīng)腔、佛韻、贊美詩等)在內(nèi)的、鮮明的文化標(biāo)識和不同的認同訴求。這樣強烈、鮮明的對比,可以說完全顛覆了我們數(shù)十年來因偏居中方西南一隅而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的民族(音樂)居處文化觀念和認識。?參見楊民康《云南景洪與緬甸景棟潑水節(jié)儀式音樂比較研究》,《民族藝術(shù)》2014年第6期,第46—55頁。多點散居的例子,如原居于中國西雙版納的傣族傣仂支系,如今同時以半圓圈狀散居在泰國、老撾、緬甸等周邊國家和地區(qū),他們藉以維護族群認同的一個共同的音樂文化標(biāo)識,就是都非常重視祭寨、祭勐等傳統(tǒng)自然宗教儀式活動及其中贊哈歌手演唱對于凝聚族性情感的重要作用。比之而言,南傳佛教儀式及其儀式音樂這樣已經(jīng)泛化至云南與周邊東南亞國家的信仰認同因素,對于境外傣仂人這樣的地域性——離散性族群來說,顯然由于已經(jīng)超出了該族群共同體文化歸屬及認同情感的具體范圍的原因,而被歸之于認同階序中較次一級的位置。線性散居的情況,可舉瑤族、苗族等,以貴州、廣西和湖南等相對靠近內(nèi)地的區(qū)域為主要據(jù)點,一方面與境內(nèi)漢族的傳統(tǒng)(音樂)文化形成密切的交融關(guān)系,另一方面則從很久以前便向東南亞地區(qū)長途遷徙,最后倚助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和國際政治活動的外力,遠徙至歐美和澳洲地區(qū),從而進入遷徙路線最長、歷史和文化跨度最大的跨界(境)族群之列。在這類散居族群中,賴以支撐其族群歸屬情感的一個重要的音樂認同因素,就是通常采用漢字經(jīng)籍及歌書記載,并在度戒、還盤王愿及各種人生儀禮中演唱的傳統(tǒng)瑤(苗)歌。
結(jié) 論
從本文關(guān)于民族學(xué)的討論里,我們產(chǎn)生的一個結(jié)論是,古代四大族群與當(dāng)代自然族群的身份認同以及當(dāng)代國家、民族與自然族群的身份認同,分別從歷時性和共時性兩方面體現(xiàn)了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層結(jié)構(gòu)與表層結(jié)構(gòu),而信仰認同、區(qū)域認同等則是其中起銜接、溝通作用的,大大小小的橋梁和潤滑劑。據(jù)此,我們將面臨著去著手解決如下幾個與之相關(guān)的西南少數(shù)民族暨跨界族群音樂研究的理論與實踐問題。
1.以藏彝走廊為歷史語境,考察和研究在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某些多民族(或單一族群)原生節(jié)慶儀式(如彝族火把節(jié)、白族繞三靈)音樂型態(tài)向次生型態(tài)轉(zhuǎn)型,以及由族群、信仰、區(qū)域認同向民族、國家認同過渡的方式及過程。
2.以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為歷史語境,考察和研究在當(dāng)代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某些節(jié)慶儀式及儀式音樂類型怎樣由多族群、跨區(qū)域宗教音樂與認同(如潑水節(jié)儀式音樂和云南洞經(jīng)音樂)向單一民族、共同區(qū)域民族文化標(biāo)識與認同分化、轉(zhuǎn)型(如潑水節(jié)分化為傣族潑水節(jié)、布朗族桑刊節(jié)、阿昌族澆花水節(jié);洞經(jīng)音樂分化為多民族分別擁有的音樂文化標(biāo)識)的方式及過程。
3.以梅山文化、苗疆走廊等為歷史語境,考察和研究在當(dāng)代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某些節(jié)慶儀式及儀式音樂類型怎樣由單一族群、區(qū)域、信仰認同(瑤族盤王節(jié),苗族苗年節(jié)、三月節(jié),景頗族目腦縱歌等)向民族、國家認同轉(zhuǎn)型的方式及過程。
4.考察和研究在當(dāng)代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某些傳統(tǒng)音樂類型怎樣由單一地域、族群樂(歌)種衍變?yōu)槎嗟赜颉⒆迦海ㄖ担┟褡逦幕瘶?biāo)識(侗族大歌、布朗彈唱),由族群、地域認同上升為民族、國家認同的方式和過程。
5.考察和研究在當(dāng)代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某些少數(shù)民族題材歌曲怎樣由電影、創(chuàng)編作品衍變?yōu)槊褡逦幕瘶?biāo)識(“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五朵金花”“蘆笙戀歌”“阿詩瑪”“劉三姐”)并產(chǎn)生民族及內(nèi)外文化認同的方式及過程。
在分別對以上幾個問題進行詳盡的考察和局部比較研究之后,便能夠結(jié)合西南各民族區(qū)域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民族、國家音樂文化認同的凝聚、形成過程問題去進一步展開“跨地域、族群、文化”的整體性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