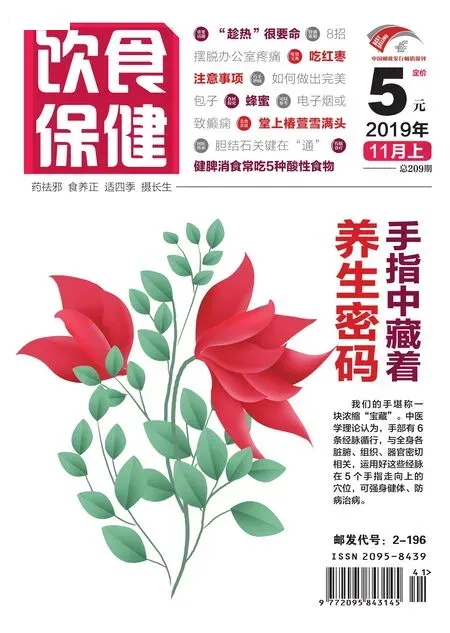說蠔
老饕 文
“蠔油牛肉”為粵菜之名菜,牛肉因與蠔油配伍而魅力大增——牛肉的鮮與蠔油的鮮相互交融后,竟生出非同一般的鮮味來。

蠔是什么?它大名叫牡蠣,屬軟體動物雙殼類。雙殼類通常雙爿大小相同,蠔卻下殼(固著在礁石上)大于上殼。殼灰白而凹凸不平,其貌不揚,肉卻青白如玉。我國沿海各省皆產蠔,大連人稱“海蠣子”,福建人叫“蚵”,廣東人叫“蠔”。有一年我去寧波,在當地一菜市場竟見到蠔肉(當地叫“蠣黃”)被“養”在淘米水當中,據說是為了讓其漲發得大一些。人工養殖長大的蠔,品質遠不如天然的——后者的殼厚,有的一只就可以重達十來斤。世界上蠔的品質以新西蘭的為最佳,澳大利亞產的次之,英法等國出產的再次之。
蠔可生吃,一如三文魚。以前,大連金石灘的漁民左手抓饅頭,右手握鐵鉤,挖出蠔肉就夾入饅頭大嚼起來。大家在海鮮酒家吃生蠔時,蠔肉剛剖出時還能見到它微微蠕動。將其用醋先洗凈,再拌上姜絲、蒜米和香菜,最后澆上醬、醋和香油就做成了佐酒的美味。歐洲人尤愛生吃蠔:常常是點上一盤生蠔,先飲點白葡萄酒,吃蠔時再往蠔肉上擠一點檸檬汁以增香。法國的蠔個體比較大,多是在海邊養殖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曾在巴黎宴請過編輯韋爾第,韋爾第因患胃炎,吃得很少;作家胃口卻很健旺,不但吃了不少羊肉片,還有鴨、鷓鴣、比目魚以及大量的“奧當斯蠔”。此外,法國的“貝隆生蠔”為蠔中佳品,它就像上好的葡萄酒一樣擁有多層次的口味。而另一種“特殊吉拉迪蠔”,入口則微脆有嚼勁,同時還伴有甘甜的滋味。美國西雅圖有一家海鮮餐館,將蠔肉置于碎冰中供食客生吃。日本人吃生蠔是理所當然的,他們還將生蠔分為“白肉”(色雪白,屬淺水蠔)與“赤肉”(色微赤,屬深水蠔)兩種。每年農歷的九月至次年三月吃“白肉”,此時蠔尚未瀉膏(散卵),肉飽滿肥美;進入暑季則食“赤肉”。我國散文大家朱自清曾經說過,吃生蠔的季節是英文字母R 的月份,即每年的9 至12 月。以前,冬日的一大享受是三兩知己圍爐而坐,溫一爐黃酒慢享冷冷的生蠔。而如今,則是吃大閘蟹最好配黃酒,吃生蠔最適合配爽口的白酒。
由于筆者出生在海邊小城,故對吃生蠔一點心理障礙也沒有。它的肉冷冷的,滑滑的,軟軟的,略一咀嚼便直入咽喉,那鮮味就讓人銷魂!香港美食家蔡瀾也認為,“(蠔)熟吃絕對比不上生吃”。
生食蠔固然誘人,但它性微寒,因此,腸胃功能弱者不宜貪嘴,否則可能會腹瀉。
談到蠔的熟吃,讓我回憶起十余年前的一次青島之行。當時我是去見大學的同窗。中午在他家吃飯,他女兒買回了一堆殼厚的蠔。我這位老同學不諳烹調,于是便由我來操勺。我問他蠔是生吃還是熟吃?他說要熟吃。于是就很簡單了,只需將它治凈了放入籠里一蒸了之。吃時扒開外殼取出肉來,蘸以調味汁送入口,感覺它嫩香糯滑,比貽貝(淡菜)更勝一籌。
近日翻閱資料才知,我國的湛江蠔、珠海橫琴蠔與青島蠔都不宜生吃,只適合用來炭烤熟吃。
蠔仔煎,即蠔煎,在閩臺被叫做蚵仔煎,魯迅先生在廈門時就吃過。它既是小吃,也可作為下酒菜。據香港美食家蔡瀾講,做蠔仔煎時與鴨蛋一起爆制,點以魚露就是一道名菜。不過所選用的蠔不能太大,以拇指頭大小最適宜,同時還不能瘦,越肥越好。他指出,日本人多是把蠔沾上面粉后,入鍋炸來吃,這有點暴殄天物——因為蠔入鍋炸過后,鮮味會流失不少,所以最好還是用煎法。而臺灣蚵仔煎的制法是:鍋里油燒熱后,快速下蚵仔煎至微熟,倒入調好的土豆粉漿稍稍凝固后,打入雞蛋并將蛋黃鏟破,撒上青菜段,等到翻面煎至微微焦黃時,出鍋裝盤并澆上番茄醬。整個煎制的過程要一氣呵成才行。廈門人做蚵仔煎時,則先將清水與淀粉調成糊,加青蒜、生蚵、蛋液、蝦油和味精拌勻后,才倒入平底鍋中煎至內熟外焦黃,吃時加蔥花、姜米、香菜與醬料。我數次去福建沿海,在福州和寧德都吃過蚵仔煎,不過吃到的蚵都是小小的。最小的是不久前在上海浦東一次美食節上吃到的,比西瓜子大不了多少,師傅還說這是從臺灣空運來的。
我當時問他那是什么?他告訴是五味醬。再問是哪五味,他趕緊講這個不能說了。不過我回家后查了資料,方知那五味醬為日式,系臺灣人吃生蠔時的常用調料,沒什么秘密可言。
蠔除了用來生食、做蠔仔煎以外,還可用來做蚵仔湯、蚵仔羹、蚵仔面線、粉炸蚵酥等,而閩臺人最愛的還是蚵仔煎。
把蠔肉煮熟后,曬干或烘干便做成了“蠔豉”,即蠔干。煮蠔肉的湯經過濃縮、提煉后,即成蠔油(也稱“牡蠣醬油”),每50 公斤鮮湯可提煉出3 公斤蠔油。
蠔油的創始人是清光緒年間的廣東新會人李錦堂——他早年開了家茶寮。有一次他在煮隔夜蠔時,意外地發現溢出的蠔汁竟然味道十分甘鮮,于是在經過反復試驗后,終于掌握了加工蠔油的絕技,并自創蠔油莊,起名“李錦記”。如今百余年過去了,李錦記的系列調味品也是譽滿全球。
由于鮮蠔含鋅極多,所以有人稱它“鋅元素之王”,再加上它富含硒,故其對致癌物有著抵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