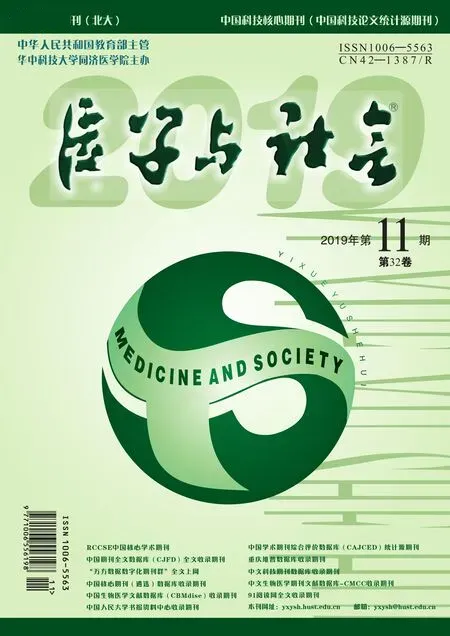溫州市某醫科大學醫學生對臨終關懷服務的態度及其影響因素
葉 星 劉 杰
溫州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溫州,325035
目前,國內臨終關懷服務的研究范圍狹窄,大部分研究對象是一線醫護工作人員。作為衛生事業新生力量的醫學生,對待臨終關懷的態度直接關系到我國臨終關懷的服務質量。因此,本研究調查醫學生臨終關懷服務態度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為構建醫學院校臨終關懷相關課程體系,改善醫護人員臨終關懷服務態度,從而促進醫患關系與醫療事業和諧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法,在溫州市某醫科大學選取650名醫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共發放調查問卷 650份,回收有效問卷 625 份,有效回收率為 96.15% 。
1.2 研究方法
調查問卷包括3部分。①一般調查問卷。對研究對象進行一般情況如專業、年級、性別的記錄,具體調查內容為是否有過至親離世、是否接受過臨終關懷培訓、是否閱讀過死亡相關的人文經典書籍、是否參加過社會實踐服務等相關內容。②臨終關懷知識問卷。對研究對象的臨終關懷知識水平進行認定。問卷內容參考鄭悅平的問卷編制而成[1]。③臨終關懷態度問卷部分。對研究對象的臨終關懷態度進行判定,參考美國護理博士Frommelt研制的佛羅梅爾特臨終關懷態度B量表(Frommelt Attitudes Toward Care of the Dying Scale form B, FATCOD-B)[2],在其基礎上編制中文版的臨終關懷態度B量表,得分越高說明臨終關懷態度越積極。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描述,影響因素通過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進行統計分析,臨終患者態度的影響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歸分析進行探討。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625名醫學生中,男生253人(40.48%),女生372人(59.52%);臨床醫學專業208人(33.28%),兒科專業 71人(11.36% ),八年制臨床專業71人(11.36%),八年制兒科專業71人(11.36%),中醫專業 49人(7.84%),康復專業 106人(16.96%),麻醉專業47人(7.52%)。
2.2 醫學生FATCOD-B量表得分與臨終關懷知識水平情況
醫學生FATCOD-B量表總分為(107.07±15.05)分,各專業臨終關懷態度得分見表1。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最高的3個條目和最低的3個條目見表2。各專業臨終關懷知識水平得分見表3。醫學生臨終關懷態度總體積極,臨床、八年制臨床、麻醉專業的醫學生臨終關懷態度與疼痛等相關臨終關懷知識水平高于其他專業。

表1 各專業臨終關懷態度得分

表2 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最高與最低的3個條目

表3 各專業臨終關懷知識水平得分
2.3 影響醫學生臨終關懷態度的單因素分析
不同年級、不同專業、是否了解臨終關懷知識、有無臨終關懷服務經驗、有無至親離世經歷(半年內)的醫學生對照護臨終患者的態度得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定期實習、有社會實踐經歷、臨終關懷知識較豐富、有閱讀死亡書籍習慣、有意愿加入臨終關懷組織、將臨終關懷作為職業素養的醫學生臨終關懷態度得分更高,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影響臨終關懷態度的單因素分析
2.4 影響醫學生臨終關懷態度的多因素分析
醫學生臨終關懷知識得分與臨終關懷態度得分呈正相關(P=0.000,r=0.403)。針對醫學生臨終關懷服務態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醫學生臨終關懷服務態度總分為因變量,以性別、臨終關懷專業知識、參與相關培訓等影響臨終關懷服務態度的單因素為自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最終得出結果:女生臨終關懷態度得分高于男生,臨終關懷專業知識與臨終關懷態度正相關,閱讀相關死亡書籍能夠擁有正確的生死觀,有參與臨終關懷培訓的經歷可提升臨終關懷意愿,社會實踐常態化與早臨床能夠為臨終關懷態度帶來積極影響。
3 討論
3.1 醫學生臨終關懷知識水平掌握程度較低
需要高度關注70.84%的醫學生對臨終關懷知識掌握程度不高(臨終關懷知識平均分10.54分)。在疼痛相關知識掌握方面,康復、兒科、中醫專業相對臨床、麻醉專業較弱,導致醫學生在提供臨終關懷服務時出現信心不足、臨床關懷志愿服務參與度低的狀況[3-5]。應在醫學生各專業課程體系,特別是非臨床專業中強化疼痛學、臨終護理學等專業課程,為患者提供行之有效的綜合性止痛方案,緩解病患因疼痛而引起的焦慮、恐懼等情緒,阻止病情繼續惡化,從而提升醫學生臨終關懷服務的信心與意愿[6-7]。
3.2 醫學生缺乏正確的死亡倫理認識
55.68%的醫學生不愿跟臨終患者建立親密醫患關系,64.5%的醫學生跟臨終患者談論即將來臨的死亡會感到不適;而臨終關懷態度積極(FATCOD-B量表總分大于120)的醫學生中,61.28%閱讀過死亡相關書籍。結合臨終關懷態度的3個最低分條目分析可知,缺乏正確的死亡倫理認識會對醫學生臨終關懷服務態度產生較大消極影響。這與我國傳統習俗密不可分,公眾對涉及死亡的話題仍然避而不談,即便是追求科學真理的醫科類大學,也僅在倫理學等少數專業課上提及,尚未從醫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多學科角度引導醫學生接受死亡、正視死亡,缺乏系統性的死亡觀教育[8-9]。
因此,將死亡文化與心理、悲傷輔導、死亡習俗、病情告知等心理知識與技巧納入醫學生死亡教育體系,按照不同年級階段性學習,從而激發學生自主意識,主動開展死亡教育實踐,能夠幫助患者及家屬獲取面對死亡的心理疏導,為臨終患者提供醫學性與社會性的臨終關懷服務[10-11]。
3.3 醫學生“早基層-早臨床”機制的常態化可提高其臨終關懷服務的積極性
FATCOD-B量表總分120及以上的醫學生中,71.84%定期參與社會實踐服務,62.3%定期參與病房實習,說明社會實踐常態化機制與醫學生早期臨床的培養,可以提高其臨終關懷服務的積極性。低年級醫學生可通過為社區老年人提供常態化的基礎診療社會實踐服務增強相關意識,了解社區臨終關懷服務現狀;高年級醫學生可通過臨床實習,參與完整的臨終關懷服務,積累臨終關
懷服務實踐經驗[12]。在“早基層-早臨床”的社會服務與臨床實習中,醫學生的病患溝通能力、同理心意識、人文情懷將有所提升,能夠意識到臨終關懷的迫切需求與作為醫護人員的社會責任,逐步將臨終關懷服務內化為醫學生的職業素養,積極參與其中[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