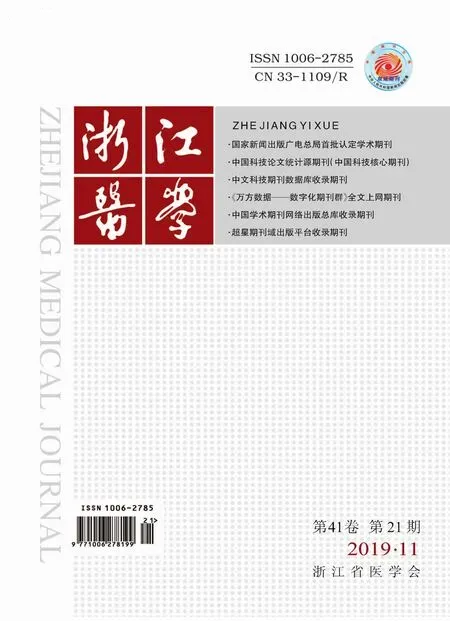中藥聯合化療對晚期胰腺癌的臨床療效及安全性研究
黃霜霜 朱佳敏 趙鵬 沈敏鶴 婁萬爽 楊天興
胰腺癌是一種高度惡性的腫瘤,預后極差,5年生存率低。據最新全球癌癥數據統計,預計美國2019年將新發56 770例胰腺癌患者,而死于胰腺癌患者將達45 750例[1]。我國最新癌癥數據統計顯示,胰腺癌位居我國惡性腫瘤發病率第10位[2]。由于胰腺癌起病隱匿,早期無特異性臨床癥狀及體征,大多數患者診斷時已屬晚期。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藥物進入胰腺癌的臨床試驗,但療效不容樂觀。
晚期胰腺癌首選含吉西他濱為主的化療方案,多數患者因機體免疫功能低下或反復化療不能耐受不良反應,不能完成相應的西醫治療,甚至喪失治療機會。相關研究結果表明,中藥配合化療能減輕后者不良反應并增強療效。因此,本文對中藥聯合化療在晚期胰腺癌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進行了探討,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56例)、浙江省中醫院(32例)住院并接受含吉西他濱方案化療的晚期胰腺癌患者資料88例。納入標準:(1)經病理組織學確診的晚期胰腺癌患者,且影像學有1個及以上可以測量的病灶作為目標病灶;(2)年齡在18~75歲;(3)生存期預計在3個月以上患者;(4)心、肝、腎等功能正常,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制定的體力狀況評分(performance status,PS)0~2 分。排除標準:(1)存在嚴重臟器疾病及相應功能受到嚴重損害者,治療過程中存在心力衰竭、呼吸衰竭、腎功能衰竭等導致不能繼續進行化療者;(2)有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哺乳期女性及孕婦;(3)對藥物曾產生過嚴重的過敏性反應者或過敏性體質的患者。根據患者是否服用中藥分為治療組(44例)和對照組(44例)。兩組間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 1。

表1 兩組患者一般情況比較(例)
1.2 方法 對照組只接受吉西他濱(江蘇豪森藥業股份有限公司,1.0g/支,國藥準字:H20030105,1 000mg/m2,第1天、第8天靜脈滴注)聯合替吉奧(山東新時代藥業有限公司,20mg/粒,國藥準字:H20080802。根據體表面積:<1.25m2,80mg/d;1.25~1.5m2,100mg/d;>1.5m2,120mg/d;服用14d,停7d)或卡培他濱[(上海羅氏制藥有限公司,0.5g/粒,國藥準字:H20073024;1 250mg/(m2·d),服用 14d,停7d)]方案化療,21d為1個周期。治療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配合中藥治療,中醫根據辨證施治,腎虛陽亢型采用天麻鉤藤飲加減,肝胃不和型采用小柴胡湯加減,肝郁脾虛型采用四逆散加減,脾胃虛弱型采用四君子湯加減,并隨癥加減。若腹痛、嘔吐可加枳實、白芍、制半夏、干姜、蘇葉、厚樸等;便秘、腹脹可加六神曲、山楂、麥芽、雞內金、大黃等;發熱可加銀柴胡、知母、黃連等;黃疸、腹水可加茵陳、山梔、茯苓、澤瀉等;1劑/d,水煎,早晚分服,21d為1個周期。兩組均治療4個周期。
1.3 觀察指標及療效評定標準
1.3.1 臨床療效 治療前及4周期治療后行CT掃描評估瘤體大小變化。參照RECIST 1.1實體瘤療效[3]評定標準分為分為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CR)、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PR)、疾病穩定(stable disease,SD)及疾病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PD);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mission rate,ORR)指腫瘤縮小達到一定量并且保持一定時間的患者的比例,為CR+PR的病例數占可評價例數的百分比;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DCR)指經治療后獲得緩解(PR+CR)和SD的病例數占可評價例數的百分比。對患者進行生存期隨訪,記錄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及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
1.3.2 卡氏功能狀態(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評分 采用ECOG制定的KPS評分法,兩組患者在治療前及4周期治療后各評定1次。得分越高,表明健康狀況越好,越能耐受化療所帶來的不良反應。得分越低,則健康狀況越差,如<60分,則無法行化療。好轉:和治療前相比,KPS評分能提高≥10分;穩定:和治療前相比KPS評分未見明顯差異;惡化:和治療前相比KPS評分下降≥10分。
1.3.3 不良反應 參照世界衛生組織抗癌藥物毒性反應分度標準進行判斷分級記錄,不良反應分為Ⅰ~Ⅳ級,觀察兩組治療過程中Ⅲ/Ⅳ級不良反應反生例數,主要包括骨髓抑制、胃腸道反應、肝腎功能損害、皮疹。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24.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采用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或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比較 見表2。
由表2可見,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CR、PR、SD、PD所占比例)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Z=0.606,P>0.05),兩組ORR和DCR比較,差異亦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
2.2 兩組患者的PFS和OS比較 治療組和對照組的中位 PFS分別為 6.7個月(95%CI:5.5~7.9)和 5.6個月(95%CI:3.3~7.9),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和對照組的中位OS分別為10.9個月(95%CI:9.2~12.6)和 10.2 個月(95%CI:9.6~10.8),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圖1、2。

表2 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比較(例)

圖1 兩組患者的P F S比較

圖2 兩組患者的O S比較
2.3 兩組患者的KPS評分比較 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K P S評分比較[例(%)]
由表3可見,治療組KPS評分好轉例數明顯多于對照組(P<0.05)。
2.4 兩組患者Ⅲ/Ⅳ級不良反應比較 見表4。

表4 兩組之間Ⅲ/Ⅳ級不良反應比較(例)
由表4可見,治療組粒細胞減少、胃腸道反應、皮疹的發生率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均P<0.05)。
3 討論
當前西醫治療晚期胰腺癌的方法仍不理想,盡管近年來免疫治療、靶向治療等成為熱門,但尚未取得可觀的療效,因此,化療仍是晚期胰腺癌的主要選擇。晚期胰腺癌的化療方案以吉西他濱單藥,吉西他濱聯合替吉奧或白蛋白紫衫、卡培他濱等為主[4]。一項隨機對照Ⅲ期臨床研究表明,吉西他濱聯合替吉奧組的OS為10.1個月,吉西他濱組為 8.8個月[5]。另一項三期臨床研究將533例晚期胰腺癌患者隨機分為吉西他濱單藥組和吉西他濱聯合卡培他濱組,聯合組顯著提高了ORR(19.1%比 12.4%,P<0.05)和 PFS(HR=0.78,P<0.01),OS也有延長趨勢[6]。本研究納入病例選用含吉西他濱的方案聯合化療,對比吉西他濱單藥能提高患者PFS和ORR。化療雖能提高患者的PFS,或延長OS,但同時帶來的不良反應也不容小覷。一項研究納入342例患者,分別采用奧沙利鉑、伊立替康加氟尿嘧啶三藥方案對比吉西他濱單藥方案化療,三藥組的OS為11.1個月、PFS為6.4個月、ORR 31.6%,吉西他濱組OS為6.8個月、PFS為3.3個月、ORR 9.4%(均P<0.01)[7]。但三藥組出現更多不良事件,患者的生活質量下降明顯。因此臨床醫生期待出現全面綜合的治療,最大程度地控制腫瘤進展,使晚期胰腺癌患者得到最大的臨床獲益。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的研究結果表明,在胰腺癌患者的治療中,中醫藥表現出明顯的優勢。鞏天曉等[8]采用吉西他濱聯合白蛋白紫杉醇化療方案聯合“抑癌散結湯”治療66例胰腺癌患者,結果發現聯合組KPS評分改善情況較對照組提高21.21%,且能減少化療不良反應,降低腫瘤標志物水平(均P<0.05)。韓俊等[9]以“清胰化積湯”聯合動脈灌注化療治療106例中晚期胰腺癌,證明聯合組有效率(81.13%)高于對照組的60.38%,聯合組臨床獲益率(64.15%)高于對照組的41.51%(P<0.05)。這也給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88例晚期胰腺癌患者,進一步評估中醫辨證治療晚期胰腺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顯示,中醫辨證治療在改善晚期胰腺癌的臨床療效不明顯,可能由于病例數不足、研究周期過短。治療組中位PFS延長1.1個月,OS延長0.7個月。中醫辨證治療組雖然對晚期胰腺癌的OS改善不明顯,但能顯著改善患者PFS。兩組患者不良反應、嚴重不良事件發生率相近,并未發現中醫辨證組治療相關的死亡事件。統計分析各項不良反應發生例數,治療組Ⅲ/Ⅳ級不良反應包括血小板減少、肝功能損害均少于對照組,但P>0.05,考慮可能與納入病例數不足有關。由此可見,中藥能減輕化療的不良反應,提升患者的耐受性,且療效安全。兩組經治療后通過分析比較KPS評分,前者明顯高于后者(P<0.05),說明治療組在改善晚期胰腺癌患者KPS評分上明顯優于對照組,可見聯合中藥組能減輕化療不良反應,提高化療耐受性,從而改善患者KPS評分。
綜上所述,中藥聯合以吉西他濱為主的化療方案治療晚期胰腺癌,能顯著改善患者KPS評分,減輕化療不良反應,延長PFS,且耐受性好,療效安全,值得臨床進一步推廣。盡管如此,仍存在一些問題:本課題由于時間較短,僅納入88例臨床觀察病例,因此結果極有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在以后的工作中需擴大樣本量,完善研究;再者,本課題由于條件和時間的限制,部分患者未隨訪到研究終點,可能對OS和PFS的分析結果造成一定的差異,且只評估了患者的臨床療效、不良反應等情況,未行合理有效的動物實驗,缺乏分子機制研究。故筆者認為應提高中藥在腫瘤中的治療地位,不應僅限于減輕放化療的不良反應及姑息治療,同時應加強中藥的臨床應用及分子機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