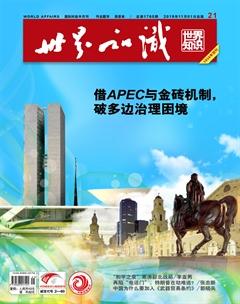新中國俄蘇研究70年:回顧與展望

馮玉軍
今年是中蘇(俄)建交70周年。70年來,中國的俄羅斯—蘇聯問題研究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歷程。幾代學人用自己的艱辛努力為中國的俄蘇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中國對于俄羅斯這樣一個世界大國和重要鄰國的認識日益深化。
70年來的中國俄蘇問題研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末。這基本上是中蘇“蜜月”的十年,也是中國“全盤蘇化”的十年。如果說,這個十年有俄蘇問題研究的話,更多的是介紹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方面的“偉大成就和方法”,全盤學習蘇聯的東西。客觀而論,這十年的研究更多的是單方面的滿腔敬仰和無限熱愛,科學的研究相對很少。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70年代。隨著中蘇關系惡化,特別是兩國進入十年論戰和爆發邊界沖突,中國的俄蘇研究來了個180度大反轉——除了揭批“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全方位威脅之外,對俄國侵華史的研究也全面展開。回頭來看,這一時期的研究有偏頗之處,但也是對前十年“全盤蘇化”的矯枉過程,從另一個側面讓中國對俄蘇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了解。第三階段是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相伴隨的。隨著中蘇關系逐漸正常化以及中國學術研究氛圍的日益好轉,中國的俄蘇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40年來,有關俄蘇問題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研究力量日益壯大,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在歷史研究方面,幾部重要的俄國史、蘇聯史、冷戰史著作的出版,特別是中蘇兩國檔案的解密以及對其的整理和研究,使中國學術界有了自己關于上述重要問題的歷史敘述;在轉型研究方面,中國不僅對蘇(俄)的改革和轉型緊密跟蹤,充分借鑒其社會轉型的經驗教訓,還對中俄兩國不同的轉型路徑進行了充分的比較研究,這對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諸多不足:一是中國的俄蘇研究長時間受到政治氛圍、意識形態以及中蘇關系變化的強烈制約。兩國關系好的時候是一片贊歌,兩國關系惡化時就全盤否定。就此而言,中國的俄蘇研究還缺乏真正的學術精神和健康的學術氛圍。二是學科建設相對滯后。盡管有著70年的積淀,但是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區域國別研究,我們還沒有就俄蘇問題研究的規律、理論、方法、路徑和工具進行過很好的總結。迄今為止,國內還沒有專門的有關俄蘇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論著。三是缺乏宏大的國際視野。往往就俄蘇談俄蘇,沒有把它置于宏大的全球框架下加以深入研究,這就使我們難以確定其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體系中的準確位置。與此相關聯,中國的俄蘇問題研究迄今為止更多還是依賴于俄蘇本身的理論、材料和觀點,缺乏用“第三只眼睛”觀察研究對象的路徑,這就導致我們更多吸納的是研究對象本身的材料、思想和觀點。四是缺乏“大歷史”的縱深。我們的俄蘇研究往往是就事論事,沒有將研究對象放在連綿不斷的歷史長河中加以考察,沒有將歷史研究與政策研究有機結合起來。實際上,無論是對俄蘇本身、還是對中蘇(俄)關系的研究,不僅要看蘇聯解體后這28年、中蘇(俄)建交這70年,更要看俄羅斯的千年歷史和中俄關系的400年歷史。當前,中俄關系正經歷著“400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深刻的歷史巨變面前,俄羅斯的心理狀態如何、將施行怎樣的對華戰略,不能只聽只言片語,更需要從歷史長河中加以看待。五是缺乏真正的本體意識。很多學者“俄羅斯情節”過于濃厚,以“非黑即白”的價值判斷代替了科學嚴謹的實證、歷史和邏輯分析,凡是俄蘇的就是好的,容不得半個“不”字。
未來,中國的俄蘇問題研究應放在一個由三維坐標軸組成的立體空間來加以推進。
一是宏大的歷史觀。俄羅斯千年歷史的發展軌跡是怎樣的?中俄關系400年,俄羅斯對于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對于這些問題,要放在長時段的歷史周期中進行考察。
二是系統性的世界比較。要把俄羅斯置于整個世界體系的框架下加以思考,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它在國際體系中曾經發揮什么作用、現在處于什么樣的地位、未來還會發揮怎樣的影響。
三是要突出本體意識,以中國的國家利益作為研究俄蘇問題的根本出發點。俄羅斯在歷史上對中國產生過什么影響、現在經歷著怎樣的變化、未來又會向哪個方向演進?只有真正把維護和拓展自身國家利益作為起點和歸宿,中國俄蘇研究才能找準方位,也才會更加符合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