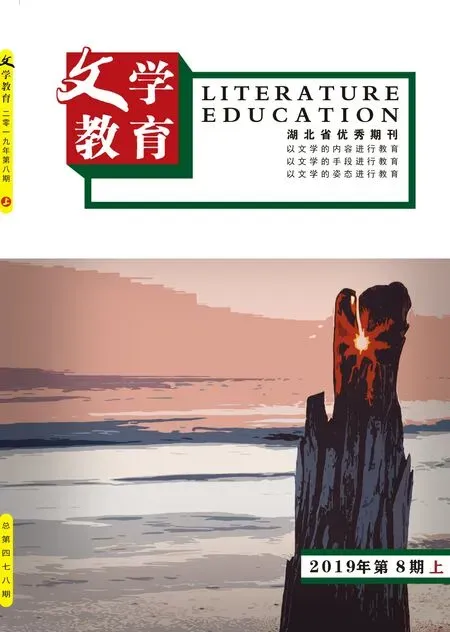試論汪曾祺對晚明小品文創作精神的傳承
王 蕾
說到晚明文學與現當代作家作品之間的聯系,周作人認為“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1]眾所周知,京派的散文小說有許多晚明小品文的印記,京派的代表人物汪曾祺曾說“我的氣質,大概是一個通俗抒情詩人。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品作家。我寫的一切,都是小品。”[2]他還在《自選集·自序》中說:“我的散文大概繼承了一點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傳統”。更確切地說,汪曾祺的文學創作在思想內涵和藝術風格上都與晚明小品有相似之處。
一.強調人的個性自由和個體價值
晚明思想家李贄主張“各從所好,各騁所長”,“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于孔子而后足也。”(《焚書》卷一《答耿中丞》)李贄的思想對晚明文壇有啟蒙作用,如晚明張岱始終將文章著眼點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不再當“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談俳文》)。體現了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對個體價值的重視,這與汪曾祺的人道主義觀不謀而合。
汪曾祺曾說:“我大概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3]“我的人道主義不帶任何理論色彩,很樸素,就是對人的關心,對人的尊重和欣賞。”[3]他將目光投向普通的蕓蕓眾生。在他筆下,有掌握“炕雞”、“趕鴨”絕活的余老五、陸長庚(《雞鴨名家》),有手工精巧能做出琳瑯滿目“滑車”的戴車匠(《戴車匠》),他們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身懷絕技,讓人贊嘆。
二.強調率真性情的表露
晚明的公安派袁宏道推崇“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敘小修詩》),強調真實表現作者個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
汪曾祺說:“作家就是要不斷地拿出自己對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別是感情的那么一種人。”[4]在《序〈雨霧山鄉〉》中他引用了王國維的一句話,“一切文章中,余愛以血寫成者”。“過人的哀樂如實地、不加修飾地寫出來,便極感人”。[5]“散文的大忌是作態”。[6]他作品中對人物風景的品賞也都是他個人本真性情的流露。
三.創作內容趨于生活化,個人化
思想家李贄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焚書》卷一《答鄧石陽》)從正面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晚明小品文創作風格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趨于生活化、個人化……”[7]晚明的文人樂于在小品文中表現游賞生活和市井風情,如張岱的《西湖七月半》,文中寫了官員、優伶、仆役、閨秀、閑僧、作者的好友和佳人等在西湖看月的時不同表現,描繪了一幅世俗風情畫。
汪曾祺曾說:“我是很愛看風俗畫。十六、十七世紀的荷蘭畫派的畫,日本的浮世繪,中國的貨郎圖、踏歌圖……我都愛看。講風俗的書,《荊夢歲時記》、《東京夢華錄》、《一歲貨聲》……我都愛看。我也愛讀竹枝詞……我的小說里有些風俗畫的成分,是很自然的。”[8]“我的相當一部分小說是寫我的家鄉的,寫小城的生活,平常的事,每天都在發生,舉目可見的小小悲歡,這樣,寫進一點風俗,便是很自然的。”[8]
汪曾祺常看關于時令風物民俗的雜書,燈節吃食、民間手藝、山水游樂,書畫鑒賞,街坊鄰里等,皆能入文,不一而足。如小說《皮鳳山楦房子》寫家鄉的風物:“朱雨橋吃了家鄉的卡縫鳊、翹嘴白、檳榔芋、雪花藕、熗活蝦、野鴨燒咸菜。”《花瓶》中寫到景德鎮瓷器等。
四.注重在作品中表現情趣
袁宏道《敘陳正甫會心集》闡述了“世人所難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的見解,對晚明小品文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汪曾祺也說“散文總得有點見識,有點感慨,有點情致,有點幽默感”。[9]這種趣味表現在汪曾祺的創作中有兩點,一是生活中的情趣,二是創作中的意趣。有學者認為汪曾祺“對草木蟲魚的品味態度,同時也說明了他對文人由來已久的“玩物”興趣的喜好。”[9]此外,他寫人物也多有諧趣之筆。如在《鬧市閑人》一文中寫的獨居老人“他平平靜靜,沒有大喜大憂,沒有煩惱,無欲望亦無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條面、撥魚兒,抱膝閑看,帶著笑意,用孩子一樣天真的眼睛。這是一個活莊子。”文末的一句點評給人妙趣橫生之感。在《口味·耳音·興趣》一文中,他寫道“有人不吃辣椒。我們到重慶去體驗生活。有幾個女演員去吃湯圓,進門就嚷嚷‘不要辣椒!’賣湯圓的冷冷地說:‘湯圓沒有放辣椒的!’”讀來讓人忍俊不禁。
五.講求結構的自由隨意,擅用口語
晚明的公安派推崇“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公安派作家不太喜歡在作品中鋪陳道理,刻意雕琢,他們往往根據生活體驗與個人愛好,抒情寫景,賦事狀物,追求一種清新灑脫、輕逸自如,意趣橫生的創作效果……”[10]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創作中實踐這一主張。
汪曾祺多次說:“我的一些小說不大像小說,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素描。”“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不直接寫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動。有時只是一點氣氛。但我以為氣氛即人物。”“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11]在他的《釣魚的孩子》《幽冥鐘》等小說,都體現出這一特色。汪曾祺在《談散文》一文中所說,“喜歡弗吉尼·沃爾芙。喜歡那種如云如水,東一句西一句的既叫人不好捉摸,又不脫離人世生活的意識流的散文。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該是散散漫漫。”汪曾祺散文深受歸有光的影響,他稱贊歸有光的散文“隨事曲折,若無結構”。[12]汪曾祺說:“章太炎論汪中的駢文:‘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這樣的結構,中國人謂之‘化’。蘇東坡說:‘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文章寫到這樣,真是到了‘隨便’的境界。”[13]
在《當代散文大系總序》中,汪曾祺談到:“明季作家意識到語言的自然美,三袁張岱,是其代表。”可以說,汪曾祺的語言正是傳承了晚明文學講究的本真自然之美,多口語化的表達方式。在《談散文》一文中,他說,“文學語言總得要把文言和口語糅合起來,濃淡適度,不留痕跡,才有嚼頭,不‘水’”。如“上了井岡山,更麻煩了:井岡山說的是客家話。我們聽一位隊長介紹情況,他說這里沒有人肯當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對,說是‘辣子毛補,兩頭秀腐’──‘什么什么?’我又得給他翻譯:‘辣椒沒有營養,吃下去兩頭受苦’。”(《口味·耳音·興趣》)
1989年版的《蒲橋集》封面上有一條廣告:“齊白石自稱詩第一,字第二,畫第三。有人說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說好,雖非定論,卻有道理。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日后汪曾祺老實“招供”,廣告是應出版社之邀,此“廣告”是汪曾祺對自己“散文觀”最明確、簡練的表述。
總之,汪曾祺傳承了晚明思潮的人文主義思想,努力描繪人性的健康自然之美,創作內容貼近民生民情,感情真摯,注重趣味,章法自由,擅用口語,使他的作品很好地實現了對晚明小品文創作精神的傳承。